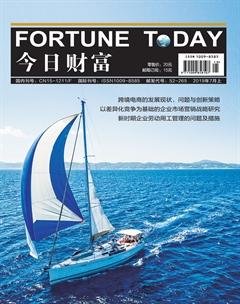從兩種“勞動生產率”管理看“996工作制”爭議
張毅來


我們需要注意到,通過加班增加工作時間創造價值,并不符合全球經濟發展的基本潮流,也不符合技術進步驅動型的未來經濟發展模式。在當今世界先進國家的學界和輿論已經熱衷于探討新一代技術進步驅動的經濟發展可能帶給人類社會的“全民無條件基本收入”前景的時代背景下,我們的“996工作制”爭論顯得那么的與時代發展脫節。從經濟成長理論中著名的經濟增長核算方程來講:產出增長率=技術進步率+(勞動收入份額×勞動投入增長率)+(資本收入份額×資本投入增長率)。這個方程式闡述了一個基本經濟規律,那就是:經濟發展的動力主要來源于三個驅動力量:技術進步,勞動投入的增加,資本投入的增加。但其中由于加大勞動(包括勞動者數量和勞動時間)與資本投入驅動的產出增加,遵循的是邊際報酬遞減規律,因此只有技術進步才被認為是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動力,所謂“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就是這個規律的高度概括。對此理念,應該說我國各界早已經達成高度共識,在此背景下也提出了“創新型社會”的重要國家發展戰略。但隨著“996工作制”爭論的發酵所體現出來的一些現象表明,即便是理念達成共識,但在具體操作和實現細節上其實尚存在很多問題,有時候甚至出現與理念背道而馳的情況。因此如何落實先進理念,對我們經濟和企業管理者是一個重大課題。
如何落實技術進步驅動的發展?千種萬種方法,其中就有一個重要方法,就是圍繞如何提高“勞動生產率”來進行管理目標和評價體系的構建,這也是包括我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大力推動的企業,乃至經濟管理的重要方法之一。一般而言,上述的“技術進步率”在學術上用“全要素生產率(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加以描述,它是一種廣義的技術進步的衡量指標,通常包含了工程意義上的技術革新,經營管理方法上的革新,人力資本意義上的技能提高等因素引發的技術進步的經濟結果。無論是國民經濟促發展,還是企業促發展,圍繞這個中心進行管理體系的構建已經越來越成為管理的核心內容之一。而提高“勞動生產率”就是“全要素生產率”管理的重要內容。但是,簡單說的“勞動生產率”,其實存在兩種計算方法,它們所體現和反映出的“全要素生產率”管理的程度存在很大差距,我們采取哪種“勞動生產率”進行管理可能導致的結果可能存在很大不同,從一定意義上講,“996工作制”之所以產生,可能就與此有關,這是我們需要注意的重大問題。
“勞動生產率”的直接計算公式非常簡單,勞動生產率=產出/投入。其中產出的部分可代入變量,一般包括名義產值或實際產值,以代入實際產值更為多見,也更科學。但特別重要的是投入部分的計算方式有兩種,這會導致出現上述兩種“勞動生產率”。具體來說,如果投入部分代入的是單純的勞動者數量,我們就稱之為“人均勞動生產率”;而不單考慮勞動者數量,還考慮人均工作時間的,計算上體現為:勞動者數量×人均勞動時間,那么我們就稱之為“人均單位時間勞動生產率”。也就是說,“人均勞動生產率”=產出/勞動者數量;“人均單位時間勞動生產率”=產出/(勞動者數量×人均工作時間)。
從公式可以很容易看出,“人均勞動生產率”在勞動者數量一定的情況下,可以通過延長人均工作時間,多加班來實現分子產出的增加,這樣就可以使“人均勞動生產率”提高。但問題是,通過增加人均工作時間,其遵循的恰恰是邊際報酬遞減規律,根本不是技術進步驅動的產出增加和生產效率提高模式,這并不符合采用 “勞動生產率”進行管理的初衷和目的。因此,即便社會已經普遍達成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管理共識,但如果采用的是“人均勞動生產率”評價體系,那么其實就已經偏離了這種管理指導思想的初衷了。它的弊端的一種表現就是試圖通過延長工作時間,多加班來提高“人均勞動生產率”,“996工作制”的出現就不奇怪了。
另一方面,從“人均單位時間勞動生產率”的計算公式可以看出,如果采用這個標準體系,那么就完全剔除了依靠延長工作時間,容忍邊際報酬遞減的低效率生產方式來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可能。“人均單位時間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就意味著只能從如何提高人均單位時間內的產出角度去考慮,這就只能依靠不斷引進更高生產效率的新的生產技術,新的經營管理方法,不斷提高與新技術新方法相匹配的知識和能力結構的人力資本,這些才能真正體現“全要素生產率”管理的主要內容。因此,企業只有提高對“人均單位時間勞動生產率”的重視,才能更強化促進其圍繞技術進步導向的發展構建其管理和經營體系,才能更容易引導企業圍繞創新,集中各種生產和管理資源,這不但能給企業帶來更大的附加價值,而且最終也能形成員工個人收入的增加,福祉的改善。當然,如果這種以如何提高“人均單位時間勞動生產率”為指導方向的生產管理體系能夠在一個社會中成為主流,那么這個社會最終將更容易實現“創新型社會”,實現長期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因此,對“勞動生產率”提高的追求,應該落腳于對“人均單位時間勞動生產率”提高的追求,這才是從企業層面推動落實“創新型社會”,創新驅動的經濟發展模式的基本抓手。
既然“人均單位時間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如此重要,那么我國目前的這個指標是多少?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又處于一個什么位置呢?對此,日本的“公益財團法人日本生產性本部”每年都會依據OECD(經合組織)公布的36個加盟國的相關數據,以及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機構公布的相關數據,進行測算并發表《勞動生產率的國際比較》報告,最新一期是2018年12月19日發表的2017年度數據的報告。我們可以通過這個報告的結果來看看上述基本情況。但由于這個報告并沒有直接提供中國、韓國的“人均單位時間勞動生產率”數據,因此,筆者根據該報告提供的中韓兩國的人均購買力平價(2000年基準)GDP、以及兩國的法定工作日數、OECD提供的兩國人均日工作時間加以計算得出中韓兩國的這項數據,以供參考比較。
從上表一目了然,目前我國“人均單位時間勞動生產率”確實存在很大提升空間。2017年的數據顯示,我國只有美國的18.8%左右,日本的28.4%左右。即便我們與同位于東亞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的韓國相比,也僅占其35%左右。如果韓國也歸為工業國家,那么上述8個世界主要的工業國家的平均“人均單位時間勞動生產率”是57.3美元,而《勞動生產率的國際比較 2018》所提供的所有36個OECD國家的平均“人均單位時間勞動生產率”是53.5美元。由于這36個OECD國家基本可以代表工業國家整體水平,這意味著我國人均單位時間創造的價值目前尚遠遠低于世界的工業化國家平均水平。如果工業化程度越高就意味著其高附加價值的生產能力越強,那么這個狀態可能也反映出我國整體工業化水平,尚處于初步發展階段,而高附加價值生產能力尚不足的現狀。
接下來,我們可以再看一下2017年各國“人均勞動生產率”的比較,兩種算法的勞動生產率相比較就能看出一些微妙差異。首先,表2的勞動生產率所反映出的問題,粗看基本與表1所反映的問題大致相同。也就是說,中國的“勞動生產率”相比主要工業化國家差距是較大的,比如是美國的24.4%左右,是日本的40%左右,是韓國的42.1%左右。但細看可以發現,盡管其差距仍然較大,但相對于“人均單位時間勞動生產率”其差距已經從數值上小了不少。比如:相對美國,表1的占比是18.8%,表2的占比則是24.4%;相對日本,表1的占比是28.4%,表2則成了40%,等。而不計入單位時間的“人均勞動生產率”之所以大幅優于“人均單位時間的勞動生產率”的根本原因,就是前者計量的人均產值可能是建立在勞動者加班延時工作的基礎之上,這樣的產值增加并不是通過全要素技術進步實現的,其遵循的規律仍然是邊際報酬遞減,因此它當然不能更好地實現生產效率的提高。再比如,表1中僅次于美國的高效率工業國家-德國,一旦不計入單位時間,那么德國的“勞動生產率”一下就跌至表2所列國家中的第4位,如果單看表2,還以為德國的生產效率不如法國和意大利,但通過表1,我們可以很容易發現,真實情況根本不是這樣,德國的生產效率其實是高于法國和意大利的。
可見,如果我們的企業,乃至社會更偏向于采用不計入單位時間的“人均勞動生產率”作為經營管理的導向的話,那產生類似靠鼓勵員工加班延長工作時間-“996工作制”來提高人均產值,進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傾向也就不奇怪了。但這樣的結果其實是抑制了企業和社會的更高效率生產的潛在提升空間,容忍和縱容了低效率的生產方式,因此是有較大缺陷和弊端的。正因為如此,我們的企業和社會更應該樹立圍繞如何提高“人均單位時間的勞動生產率”的經營管理理念,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挖掘企業和社會的創新潛力,真正實現以技術進步為主要驅動力的企業和經濟的高效率發展,更好地落實“創新型社會”所要求的增長模式。(作者單位: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
注釋:
[1]“807”是指每天上午8點開始工作,凌晨0點下班,1周7天工作。“716”是指每天7點出門上班,凌晨1點回家,1周只休息1天。
[2]“單位時間”是指1個小時。
——關注自然資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