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耐藥鮑曼不動桿菌感染64例病原學特點、耐藥情況及危險因素分析
方映雪,夏修三,張鳳琴,張愛蓮
鮑曼不動桿菌(以下簡稱AB)近年來已經成為多重耐藥菌感染防控的重點病原菌之一。由于廣譜抗菌藥物的大量使用及侵入性醫療操作的廣泛開展,該菌引起的耐藥性感染病例逐年上升,并呈多重耐藥(以下簡稱MDR-AB)、廣泛耐藥趨勢,給臨床抗感染治療帶來極大困難[1-2]。本研究對64例MDR-AB和70例一般AB病人的病原學特點、耐藥性及危險因素進行分析,旨在為基層醫院關注重點人群、采取防控措施、治療AB引起的MDR感染和防止感染傳播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2016年6月至2018年7月廬江縣人民醫院微生物標本檢出的64例MDR-AB和70例一般AB感染的住院病人臨床資料。病人或其近親屬知情同意,本研究符合《世界醫學協會赫爾辛基宣言》相關要求。
1.2 方法
1.2.1 標本來源及鑒定、藥敏試驗 按照《臨床微生物標本規范化采集和送檢》采集和送檢病人的病原學標本;分離培養基為法國生物梅里埃公司生產的相關培養瓊脂;細菌鑒定采用法國生物梅里埃公司生產的VITEK 2 compact全自動微生物鑒定及藥敏分析系統;鑒定、藥敏板條為全自動細菌鑒定藥敏分析系統的配套產品;藥敏結果按照CLSI相關標準判斷。質控菌株為:銅綠假單胞菌ATCC27853、大腸埃希菌ATCC25922、金黃色葡萄球菌ATCC25923。MDR-AB的篩選:分離的AB至少對β-內酰胺類、碳青霉烯類、氨基糖苷類、氟喹諾酮類中三類藥物同時耐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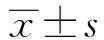
2 結果
2.1 病人的一般情況 64例MDR-AB病人年齡(66.13±12.82)歲、最小24歲、最大91歲;男女性別比為1.37∶1。70例一般AB病人年齡(68.44±13.11)歲、最小33歲、最大94歲;男女性別比為1.41∶1。兩組資料總體年齡(t=1.033、P>0.05)、各年齡段及性別,經χ2檢驗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

表1 多重耐藥鮑曼不動桿菌(MDR-AB)感染64例和一般鮑曼不動桿菌(一般AB)70例感染病人的一般資料比較/例
2.2 病人的住院醫療情況 64例MDR-AB感染者主要是顱腦損傷/手術、老年多種慢性疾患并發呼吸系統感染,惡性腫瘤也占一定比例;病人來源科室按百分比由高到低排列依次為ICU、神經外科、呼吸內科;標本來源主要是痰液;感染部位主要是下呼吸道;大部分屬于醫院感染、社區感染相對較少。而70例一般AB感染者主要是老年多種慢性疾患并發呼吸系統感染,其次是惡性腫瘤;病人來源科室主要是內科系統;標本來源仍然是痰液;感染部位也是下呼吸道;大部分屬于社區感染、醫院感染相對少些。詳見表2。

表2 多重耐藥鮑曼不動桿菌(MDR-AB)感染64例和一般鮑曼不動桿菌(一般AB)70例感染病人的醫療情況分布
2.3 耐藥性分析 64例MDR-AB感染者耐藥性結果分析:AB對頭孢哌酮/舒巴坦耐藥率最低(47.37%)、其次為阿米卡星(64.71%),其余抗生素耐藥率均大于77.19%,頭孢類抗生素及喹諾酮類耐藥率幾乎達100%。而70例一般AB耐藥率最高是左旋氧氟沙星(4.41%)、其次是頭孢吡肟(4.35%),對碳青霉烯類、氨基糖苷類及內酰胺抑制劑類100%敏感。詳見表3。
2.4 AB感染的危險因素分析 對64例MDR-AB和70例一般AB感染的危險因素進行卡方分析,發現其中顱腦損傷及手術/呼吸系統慢性感染、格拉斯哥昏迷評分(GCS評分)≤8分、有侵入性操作(氣管切開/插管+機械通氣+吸痰)及使用廣譜抗菌藥物治療是MDR-AB感染發生的危險因素。詳見表4。
3 討論
3.1 MDR-AB感染特點分析 本研究的64例MDR-AB病人中50歲以上59人、70例一般AB病人中50歲以上63人,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與這年齡階段人群易罹患心腦血管、呼吸系統、高血壓、糖尿病、惡性腫瘤等疾病有關[3];感染部位多主要是下呼吸道,其次為創口。主要見于呼吸機相關性肺炎(VAP)、創口(腦出血術后傷口、高位截癱并發壓瘡感染),是我院多重耐藥菌監測中最常見的病原菌之一。有研究顯示:MDR-AB已逐漸成為ICU及免疫力低下人群呼吸道檢出的主要病原菌之一[4],間歇聲門下吸引可有效預防氣囊上滯留物,從而降低VAP的發生概率[5]。這與本研究分析結果一致,原因可能與ICU和神經外科的病人發病急、病情重、GCS評分低、病情復雜、侵入性治療操作頻繁和病人患病時間長有關。此外,呼吸內科較高的MDR-AB檢出者大部分為老年高齡病人,呼吸系統慢性疾患破壞了病人自身防御屏障、免疫力下降、病程長、多種疾病并存、反復發作及抗感染治療,甚至進行機械通氣。腫瘤晚期病人往往出現全身衰竭,進食返流、嗆咳、氣道受壓、食道氣管瘺等致下呼吸道慢性感染,經治療后好轉,表現為MDR-AB感染與定值交替出現。以上是醫院獲得性感染的重點人群。因此,在分級診療實施過程中,基層醫務人員針對此類人群,應積極治療病人基礎疾病、控制病情發展;降低MDR-AB感染的風險。

表3 多重耐藥鮑曼不動桿菌(MDR-AB)感染64例和一般鮑曼不動桿菌(一般AB)70例耐藥情況比較

表4 多重耐藥鮑曼不動桿菌(MDR-AB)感染64例和一般鮑曼不動桿菌(一般AB)70例感染的危險因素/例
3.2 MDR-AB耐藥性分析 MDR-AB對各類藥物的耐藥性≥47.37%,有的甚至完全耐藥,遠高于相關文獻報道[6],多粘菌素、萬古霉素成為MDR-AB感染治療最后的藥物選擇,伴有腎衰的危重癥病人連最后的抗菌藥物也失去選擇。本研究分析結果顯示:一般AB耐藥率很低(≤4.41%)、對碳青霉烯類、氨基糖苷類及內酰胺抑制劑類100%敏感。MDR-AB對頭孢哌酮/舒巴坦耐藥率最低(47.37%)、對阿米卡星的耐藥率較低(64.71%),對其他各類抗生素則表現出更高耐藥(耐藥率≥77.19%)。研究顯示AB耐藥分子生物學機制:如產生多種β-內酰胺酶(ESBLs或AmpC酶)、藥物的作用靶點改變或受到保護、外膜通透屏障降低、誘導藥物主動外排系統的表達[7-9]。對指導臨床合理用藥具有重要意義。
3.3 MDR-AB感染的危險因素分析 對連續取樣的64例樣本分析表明:昏迷(GCS評分≤8分)、氣道開放時間≥3 d、有侵入性操作及廣譜抗菌藥物治療是MDR-AB感染的主要危險因素[10]。其中氣管插管/切開、機械通氣是院內肺部感染的最重要危險因素。機械通氣時破壞了呼吸道生理屏障、降低了其防御(過濾、加溫、加濕)功能,高氣道內壓力,纖毛失去協調、有節奏擺動,呼吸道分泌物不能及時被清除,AB極易與分泌物一起進入下呼吸道;吸痰操作在清理呼吸道分泌物的同時也破壞了氣道黏膜完整性,上機前已使用抗生素,為耐藥菌的產生、逆向移動提供了便利條件[11]。有報道連續機械通氣病人發生醫院內肺部感染的危險性比未用機械通氣病人高6~12倍[12]。GCS≤8分病人病情相對嚴重,病人長期臥床、自理缺陷,被動接受口腔和皮膚護理、翻身和叩背、肺部淤血、纖毛運動減弱、肺內巨噬細胞功能減退,降低了呼吸系統的自我防御功能。營養支持方式改變、久而久之出現營養不良、低蛋白血癥,機體抵抗力下降。廣譜抗菌藥物大量使用,在治療原發病的同時由于細菌的選擇性壓力作用,也增加了AB感染、耐藥的機會,并可引起體內呼吸道及消化道微生態菌種失衡[13]。雖然預防性、治療性抗菌藥物在臨床上使用極為普遍,但若使用的原則掌握不夠,抗菌藥物種類聯合過多、用藥時間過長不但沒有減少感染的發生反而成為MDR-AB產生的危險因素。
綜上所述,MDR-AB已成為基層醫院危重癥病人治療面臨的一項重大挑戰[14],該菌屬G-非發酵菌,易在醫院環境中長期存活,可在人體與外界相通的腔道如呼吸道、皮膚、胃腸道和傷口等部位定植[15],具有強大的獲得耐藥性能力以及克隆傳播能力,可通過多種途徑傳播。MDR-AB多見于伴嚴重基礎疾病的病人,感染后治療效果差,病死率高,因此針對MDR-AB感染的各易感因素,應采取綜合防控措施[16]。嚴格遵守感染控制規范以及無菌技術操作,強化手衛生,加強環境的清潔與消毒,按需進行MDR-AB篩查,實施接觸隔離,以阻斷MDR-AB傳播途徑。加強抗菌藥物管理,避免抗菌藥物濫用,對于Buccoliro等[17]報道的混合感染者需結合臨床兼顧其他細菌綜合考慮。感染管理部門加大監管力度,對預防和控制MDR-AB的產生和傳播都具有重要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