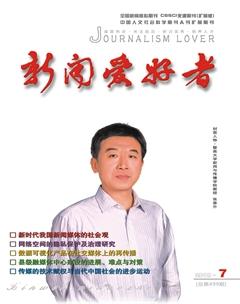導向性:新聞報道的靈魂
孫少山
【摘要】導向性是新聞的本質特征,也是歷史和現實發展的必然;在當今網絡時代,科技促動新聞傳播理念和傳播形式發生變化,新聞的導向性成為新的研究課題;掌握新聞宣傳工作中的“時、度、效”,做好新聞輿論導向,是新時代的一項重要任務。
【關鍵詞】新聞報道;導向性;輿論引導;中國國情
一
真實性是新聞報道的生命,導向性則是新聞報道的靈魂。
輿論導向,“又稱輿論引導,運用輿論操縱人們的意識,引導人們的意向,從而控制人們的行為,使他們按照社會管理者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從事社會活動的傳播行為”[1]。新聞輿論導向,就是運用大眾傳播媒介的新聞報道和其他形式完成這一引導任務。所謂新聞報道的導向性,就是新聞報道具有這種輿論引導功能。
新聞報道具有導向性,不是由人們的意志決定的,而是由我國近、當代社會各個層面的因素決定的。
一是由中華文化的性質決定的。中華文化以儒家學說為內核,而儒家學說是以“入世”為特征的,中國習儒學、考科舉的讀書人,都把寫文章當作是“治國”“濟世”“平天下”的大事,著書是為了“立說”。顯然,在中華文化的視域中,寫文章是“千古事”,寫文章不是毫無意義的文人自我表述。中國人從來不做悠閑文章。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不是悠閑文章,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也不是悠閑文章。同時,中國是以農業文明起家的,國家較為封閉、落后,原來讀書識字是有錢有勢人的事。這些“有錢有勢”的社會“精英”們讀書寫文章就是為了說理,就是為了讓被統治的“不識字”的人明白事理,變得遵紀守法、文明起來。這樣,文章的社會教化功能自然成了文章的主要特征。而新聞報道作為廣義的文章,自然要體現出強烈的“教化功能”來。
此外,我們對文章主題總是作“好”和“壞”兩極判斷。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兩極判斷呢?我想這也與我國文化有關。美國德克·布德教授說:“中國人不以宗教觀念和宗教活動為生活中最重要、最迷人的部分。……中國文化的精神基礎是倫理(特別是儒家倫理)不是宗教(至少不是正規的、有組織的那一類宗教),這一切自然標志出中國文化與其他主要文化的大多數,有根本的重要的不同。”我國著名學者馮友蘭教授認為,德克·布德教授的這一說法在一定意義上是正確的。他認為,中國文化的精神基礎是倫理,不是宗教。這意味著中國人對于高于道德價值層面的價值,不太關注。所謂高于道德價值的價值,也可叫“超道德”價值。愛人,是道德價值;愛上帝,是超道德價值。[2]將新聞文本解讀中的“二元價值判斷”現象納入這個文化大背景中考察,就能一下抓住這一現象的深層原因:因為我們只是關注以儒家思想為支撐的道德價值,因為道德價值的東西是實用的、功利的,存在著兩極性的“好”和“壞”之分,并且著重經營的也是這個“好”和“壞”的兩頭;所以,我們的文本解釋學總是以主流價值觀為準則來評判對象,并作出“好”和“壞”之分。新聞報道的價值也就在于對“好”的傳頌和對“壞”的批評。
二是由我國的國情決定的。自1840年后,我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衰落、國家貧窮,中華民族的救亡圖存問題成為時代的主要矛盾。
保羅貝羅克《1750—1980:國際工業化水平》中的一組數據就描述了中國近200年的衰落[3]:
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國GDP占世界的32%,居世界之首;印度(包括今巴基斯坦)為24%;英、法、德、俄、意占17%。
1830年(道光十年):中國29%;印度17%;英、法等五國29%;美國2.4%。
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中國6%;印度1.7%;英、法等五國54.5%(英18.5%、法6.8%、德17.9%、俄8.8%、意2.5%);美國23.6%;日本2.4%。
1945年:中國4%;美國56%。
近200年中,中國由清“康乾盛世”時的世界首富而成為落后貧窮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
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一批仁人志士辦報辦刊,發表言論,宣揚主張,振臂高呼,喚醒民眾起來,共同拯救中華民族。由于這個特殊的歷史背景,我國新聞媒體走出了一條自己特有的生存之道。在近代史上,中國人自己辦的報紙,不是以傳播信息為主,而是以宣傳主張為要。如王韜1874年創辦的《循環日報》,以“強中以攘外,諏遠以師長,變法以資強”為宗旨,極力鼓吹變法自強。這是一份以政論為靈魂的報紙。王韜也是這份報紙的主筆。從1874年至1884年這十年間,他撰寫了以《變法》《變法自強》《重民》等為題的大量政論文章,系統地宣傳了自己的政治改良主張。之后的資產階級改良人物康有為、梁啟超都是以辦報來宣傳自己的改良主張的。尤其是梁啟超倡導的“報章文體”,其“縱筆所至,略不檢束”“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條理明晰,筆峰常帶感情”。這其實是一些時政評論。王韜的政論文和梁啟超的“報章文體”,基本上可算是中國近代報刊上的正宗的“新聞文體”。中國近代的媒體,不是資本家和實業家辦的,而是仁人志士和政治家辦的。中國近代報刊是以刊載時政論文為主的政治輿論工具。
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建設得到飛速發展。2017年,中國GDP排世界第二,為13.2萬億美元,美國19.5萬億美元,日本為4.3萬億美元。雖然我國經濟總體上去了,但還有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等問題,有待進一步改革發展,提升實力。
在黨的十九大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在21世紀中葉要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復興中華民族依然是時代的重大母題。因而,我們的媒體必須將這一重大母題置于新聞宣傳的首位,在黨的領導下,引導人民群眾朝著宏偉目標奮斗。一個人要想做一件大事,必須集中精力;一個國家要想做一件大事,必須團結一致,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這就是歷史和現實的發展邏輯。
三是由我國新聞媒體的性質決定的。由于中華文化的特質和近當代中國的國情,決定了我國新聞媒體特有的性質。在近代史上,中國新聞事業從一開始就被政治家當成宣傳工具。在當代社會,我國媒體依然是作為黨和人民的“喉舌”而存在。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指出:“改革開放之后,雖然我國新聞媒體實行了市場化和商業化運作,但這只是一種求存的手段,媒體依然還是輿論機關,而不是市場主體。既然媒體還是作為輿論機關而存在,其承載的主要內容新聞報道不能不體現這一特性。”習近平強調,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堅持黨性原則,最根本的是堅持黨對新聞輿論工作的領導。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宣傳陣地,必須姓黨。尤其是2016年2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強調,新聞輿論工作各個方面、各個環節都要堅持正確輿論導向。各級黨報黨刊、電臺電視臺要講導向,都市類報刊、新媒體也要講導向;新聞報道要講導向,副刊、專題節目、廣告宣傳也要講導向;時政新聞要講導向,娛樂類、社會類新聞也要講導向;國內新聞報道要講導向,國際新聞報道也要講導向。要牢牢堅持正確輿論導向。[4]
自有新聞以來,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的媒體不講新聞的導向性。有些西方國家自標新聞報道客觀、自由,不帶傾向性,這是一個偽命題。世界上每時每刻都發生無數個事實,媒體無法將世界上發生的所有事實都作報道,媒體選擇報道哪個事實、不報道哪個事實,就帶有傾向性;每個事實有無數個報道角度,媒體選取報道這個角度而不選取那個角度,就帶有傾向性;每個新聞事實的發生都與無數個背景原因有關系,媒體將新聞事實與不同的背景相互聯系,就帶有傾向性。傾向性就是一種價值選擇,沒有媒體會做沒有價值或不符合自己價值觀的事。
二
長期的新聞實踐證明,只有那些導向正確、題材生動的新聞報道,才能得到受眾的歡迎,達到理想的傳播效果,顯現出強大的生命力。抗日戰爭時期,我黨的媒體號召和引導全國人民團結一致,積極抗日,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新中國成立初期,媒體在黨的領導下,引導人民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和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改革開放新時期,媒體更是做好黨的輿論機關,引導人民撥亂反正,勇于開拓,我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在各個時期,我黨的媒體都及時地“為時代提供有深度的思想,擔負起引導時代的重任”[5]。
我們黨在新聞輿論引導工作中,最為成功的范例是通過新聞典型報道,樹立新聞典型,引導人們的人生觀、價值觀。典型報道是對具有普遍意義和鮮明個性的人物、單位事跡組織進行的強化報道,目的是通過樹立典型,對社會中一個時代存在的一些普遍性問題進行引導和疏通。
新中國成立之初,經歷了經濟建設和抗美援朝戰爭,涌現出一大批英雄和模范人物。尤其是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我們的媒體采寫了《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黃繼光》《偉大戰士邱少云》《不朽的國際主義戰士羅盛教》等典型報道,推出了黃繼光、邱少云、羅盛教等中國人民志愿軍戰士——“最可愛的人”。黃繼光等志愿軍戰士,是新中國媒體樹立的較早的一批典型形象。這批典型形象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他們成為老百姓心中的英雄,極大地鼓舞了共和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熱情。同時,抗美援朝志愿軍典型英雄群像,也向世界表明,中國人民志愿軍是最英勇最可愛的人民子弟兵,是偉大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國防大學教授戴旭說:在朝鮮戰場上,中國人民志愿軍“那些在冰天雪地里像原木移動的人,以謎一樣的東方精神,讓中國軍隊重新在國門外找回失落百年的自信。這場戰爭,又不僅是戰爭。這是整個民族的熱血凝聚和精神迸發!”無疑,黃繼光等英雄形象的出現,極大地提升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品格,引導著當時世界對新中國的輿論態勢。
20世紀60年代初,在國家經濟最艱難的時候,媒體又推出了兩個最為經典的新聞人物——雷鋒和焦裕祿。
雷鋒的品質具備三種精神:一是忠誠精神,對黨、對革命、對人民無限忠誠;二是服務精神,時時處處為人著想,助人為樂;三是釘子精神,對工作刻苦鉆研,精益求精。新中國需要這三種精神。焦裕祿身上體現出的品質和精神是:不怕困難、艱苦奮斗、為民無私奉獻。這又是那個時代最為寶貴的。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經過自然災害和“大躍進”等人為災禍,經濟不景氣,人心不安。黨和政府的權威一時受到懷疑。針對這一特殊局面,新聞界勇敢地站了出來,推出了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這一典型形象。焦裕祿形象的推出,讓老百姓看到了新的希望:黨和政府有能力帶領人民渡過難關,我們的生活會好起來的。在焦裕祿的這個典型形象中,凝聚著黨的意志和老百姓的期盼。
在新聞典型宣傳中,除了發掘出黃繼光、雷鋒、焦裕祿等新聞典型形象外,還有鐵人王進喜、人民的公仆孔繁森、身殘志堅的張海迪、孫氏信義兄弟等一批批英雄楷模。這些英模群像,倡導了一代代的新風尚,成為時代的精神標桿。他們如一顆顆燦爛明星,永遠在共和國歷史天空中閃光。英模們的精神引領著時代的視聽,影響著一代代的中國人。
還應該看到,在新聞宣傳工作中,也有因為導向不妥而出現的社會問題。在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中,新聞界脫離實際,宣傳了一些不切實際的典型,誤導了社會,使我國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受到嚴重影響。十年“文化大革命”,媒體又一次出現導向問題,促使社會陷入混亂的狀態。實踐證明,輿論引導是新聞報道和宣傳工作的靈魂所在。
進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新聞輿論引導更為重要。由于社會文明的進步和傳播科技的發展,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興媒體,已經成為這個時代新聞信息競爭的主戰場,更是黨的新聞宣傳和輿論引導工作的重要陣地。互聯網使社會各個層面各個角落的各種信息、意見登上媒體,這無疑是一大進步。網絡時代人人都可能是信息的生產者和傳播者,新聞輿論環境將更加寬松。于是,有一種觀點認為,網絡世界,應該是一個沒有交通警察的高速公路,網民的個性和言論在上面可以自由馳騁,想怎么說就怎么說,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世界上,任何游戲都有規則,沒有規則就沒有游戲。人類肯定需要新聞和輿論自由的環境,而且隨著社會文明和傳播科技的發展,這個環境會越來越寬松。網絡的出現,其實就使人類輿論環境向前發展了一大步。但我們應該看到,我國當前的網絡內部環境比較混亂,有待進一步加強管理。
較之于傳統媒體,網絡等新媒體新聞信息發布門檻較低,有時出現零關卡,致使一些錯誤的觀點和輿論在網絡和新媒體空間生成,并形成社會動員力,誤導視聽,激化社會矛盾。目前我國網絡上的輿論存在以下問題:
一是負面性。有些網民在現實中遇到了問題,而一時又得不到解決,于是就在網上提意見。這些意見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合理的,情緒宣泄多,理性思考少。其中,也有少數人是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故意制造亂子的。對網絡上多數人的意見,要及時梳理引導和處理;對少數人別有用心的言論,必須予以批判。
二是從眾性。網上有時出現一則信息或一種言論,很多網民不明就里,人云亦云,跟著起哄。這就使輿情四處擴散,形成滾雪球效應。對此,必須及時發現引導,以免造成社會危害。
三是無聊性。網絡是個豐富的信息海洋,卻也是個無聊的世界。網民常常在上面八卦,制造許多垃圾信息,污染環境。演員王寶強離婚事件的后續報道鋪天蓋地,其時,第三十一屆里約奧運會正在進行。奧運會是人類的體育盛會,會上也有我國健兒在奮力拼搏,為國爭光。其具有極高的娛樂性,也處處充滿著正能量。而讓人不可思議的是,我國網民對王寶強的離婚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在網絡空間里,王寶強離婚事件一時沸沸揚揚,其輿論熱度不比奧運會低。2015年10月初,我國學者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獎,同時也是某影視明星結婚期間。網民在注視著參加影視明星婚禮的一個個大腕兒,卻不知道屠呦呦是什么人。就新聞信息的價值而言,奧運健兒的拼搏、科學家屠呦呦獲諾貝爾醫學獎,遠遠高于演員的離婚、結婚,但網絡社會的注意力和興奮點為什么在后者呢?可能主要是新聞信息的欣賞價值觀和消費價值觀問題。這就讓我們必須思考一個問題:網絡作為社會的重要媒體,將如何引導網民的新聞信息欣賞價值觀和消費價值觀?演員、明星結婚、離婚,有一定的娛樂價值,但缺乏引人積極向上的價值。如果一個社會陶醉在這狹隘而嘻哈的娛樂圈里,是沒有前途的。
網絡媒體是一個張揚個性的平臺。但當個體的自由成為為所欲為甚至嚴重擾亂了社會公共秩序的時候,這種自由是某個個體的所謂自由,不是全社會和全體公民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建立在社會文明、和諧、發展基礎之上的,是社會中的正能量盡可能得到激發并促進社會進步發展的。同時,自由也包含社會個體的優秀品質得到充分展示而獲得的身心愉悅。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應該是人民利益的一種法制化的體現,而不是某一個階層、某些人的隨意性,也不是滿足任何一些人、任何一個階層提出的任何一個要求。加強互聯網內容建設,建立網絡綜合治理體系,營造清朗的網絡空間,刻不容緩。
三
新聞輿論引導是一種藝術。要做好新聞輿論引導工作,必須積極推進理念創新、手段創新和基層工作創新,特別要把握好“時、度、效”。
“時、度、效”是習近平同志對新聞輿論引導工作精髓的高度概括,是新時代做好新聞輿論引導工作的法寶。這里的“時”,為時機、周期和節奏。引導輿論時機的把握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主動釋放、正面闡述,時機選擇的主動權在我;另一類是被動回應、釋疑解惑,時機是個窗口期,稍縱即逝。這兩類又可能互相轉化,主動發布給“料”足、做得好,負面輿情出現的概率就小;負面輿情應對及時、有效,往往又能給正面發布創造機遇、提供條件。“度”,為力度、掌控度和接受度。力度不夠,引不起足夠關注,難以形成持續熱點;用力過猛則過猶不及,很可能會引起公眾的抵觸。新聞輿論關鍵是要讓人接受,要做到隨時對輿情心中有數,對受眾的變化有準確評估,根據這些情況對工作進行靈活調整。“效”,為傳播效果。要用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方式,使我們的內容更接地氣、更聚人氣,“入腦、入心”,對受眾形成實實在在的影響。[6]
在實踐操作中,我們應該從三個層面把握它們的關系。一是“時、度、效”三者的互動關系。“時”是對輿論引導工作時間層面的考量,“度”是對輿論引導工作力度的考量,“效”則是對前兩項工作社會效果的綜合考量。它們之間是一種關涉多個層面多個角度的互動關系。二是“時、度”與“效”的互動關系。“時、度”,是手段,是輿論引導者獨立操作控制的;“效”,是結果,是輿論引導者經過“時、度”方面的操控而達到的社會實際效果。顯然,“效”是不受輿論引導者直接操控的。三是“時、度、效”既是三個獨立的考量單項,同時它們又是一個運行的整體。只有認真做好“時、度”兩個環節的工作,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時、度”重點是輿論引導者在審時度勢后的運作,它們是內在的、相對封閉的。“效”則打破了這種封閉性,使“時、度”的運作呈現一種開放的態勢,與社會現實緊密聯系起來。因而,“時、度、效”相輔相成,構成了把握新聞宣傳輿論引導工作的渾然一體。
意識形態屬性是新聞的本質。新聞報道失去了輿論引導功能,就失去了意義。在新聞實踐中,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傳播手段建設和創新,提高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
參考文獻:
[1]甘惜分.新聞學大辭典[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41.
[2]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3-4.
[3]保羅·貝羅克.1750—1980:國際工業化水平[J].歐洲經濟史雜志,1982(秋季號):269-334.
[4]習近平.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EB/OL].http://china.chinadaily.com.cn/xxjhjs/2016-02/21/content_23660917.htm.
[5]丁柏銓.新理念、新實踐、新追求:論新時代黨報改革再出發[J].新聞愛好者,2018(7).
[6]趙辰昕.把握時度效 講好發展改革故事[EB/OL].http://www.scio.gov.cn/zhzc/10/Document/1515394/1515394.htm.
(作者為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博士生)
編校:董方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