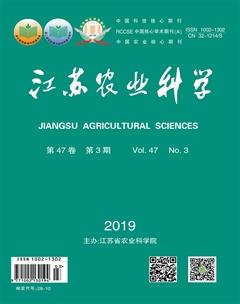“互聯網+精準扶貧”聯動機制:理論邏輯與案例實證
白福臣 肖書興 汪維清
摘要:黨的十九大提出要打贏脫貧攻堅戰,而“互聯網+”是鄉村發展農戶幫扶脫貧的新動力。當前我國“互聯 網+ 精準扶貧”面臨政府政策大力扶持、貧困地區的電商行業得到初步發展及其基礎設施日漸健全的發展機遇。運用“互聯網+”的新思路新技術,以“輸入—整合—實施—反饋”的流程建立富含金融跨界融合、創新驅動、開放生態等特色集精準識別、聯動幫扶、動態管理及精準考核于一體的促進政府、社會、市場、社區和個人等多元主體協同的“互聯網+精準扶貧”的聯動機制。以廣東揭陽軍埔村為例,探索其筑建多元扶貧主體格局、構建扶貧信息綜合平臺和打造“一鎮一品”品牌工程等做法,給我國扶貧提供新型創業主體培育、多元幫扶格局形成、動態管理機制施行等“互聯網+精準扶貧”實施路徑。
關鍵詞:互聯網+;精準扶貧;聯動機制;機遇;實施路徑;創新
中圖分類號: F323.8?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002-1302(2019)03-0278-05
信息技術與經濟社會的互動融合為互聯網技術的普及與創新提供了良好的發展機遇,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是助推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增加社會財富的新源泉。在治理貧困的過程中,尤其是在“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關鍵時期,更需要高效整合扶貧開發的各項資源,利用互聯網技術,改造粗放型、撒胡椒面式的傳統扶貧模式。“十三五”期間,中央提出要加大扶貧的投入,結合我國制度優勢,實施精準扶貧戰略,同時出臺了大量的扶貧優惠政策,保證到2020年我國832個貧困縣及7 000多萬貧困人如期脫貧摘帽。習近平總書記上任后對我國河北、甘肅、湖南等地視察,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調研考察時提出,“實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準扶貧,切忌喊口號”[1]。2014年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建議,實施精準扶貧、扶貧攻堅,建立準確的工作機制[2]。習近平總書記在《擺脫貧困》中的“勤富、智富、共富”的扶貧理念又與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實施“互聯網+”計劃和黨的十九大提出要打贏脫貧攻堅戰實現鄉村振興的措施相契合。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使“互聯網+精準扶貧”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并存,作為探索貧困治理的創新模式,如何將“互聯網+”及相關資源、技術與精準扶貧相契合,以解決當前扶貧進程中存在的問題,并對精準扶貧機制進行創新,帶動貧困地區的人順利脫貧,是研究的重要要義。
1 文獻綜述
“貧困”,源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學者朗特里的研究中,即當家庭的總收入無法滿足日常人口生存所需以致總收入跟不上總支出,這可能源于經濟社會轉型發展中的“惡性循環”存在[3],也可能由于人口過快增長以致經濟發展的紅利無法為所有人所分享[4]。為擺脫貧困,重在針對特定貧困人口實施最低工資保障、推進保險計劃施行和建立公共投資扶持機制等入手[5-6]。如果只是粗放式扶貧,沒有針對性地明確扶貧范圍和明晰扶貧目標及計量相關扶貧工作的成本效用,結果只會適得其反。扶貧,貴在精準識別貧困片區貧困對象,還須結合當地貧困片區的風俗習慣與貧困對象的能力和知識[7]。
自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湘西調研時提出要“因地制宜,精準扶貧”到黨的十九大提出要將精準扶貧成為打贏扶貧開發攻堅戰的重大戰略決策,“精準扶貧”成為近年來理論界研究的熱點問題。精準扶貧“貴在精準,重在精準,成敗也在于精準”,盡管鄧維杰等提出采用“二元檢索”與“指標打分”去精準把控[8],羅江月等提出采用個體需求評估、自我瞄準和社區瞄準等方法去精準識別[9],但因我國的貧困村太多而導致缺乏準確科學客觀的方法去瞄準貧困對象和管理貧困片區,建立瞄準機制并完善相關的制度體系不可或缺[10]。
在精準扶貧實施過程中,重在精準識別、精準督查、精準施策和精準流程,同時推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化轉移,加強扶貧機構間的親切聯動以施行產業扶貧[11-12]。趙秀蘭認為,精準扶貧要針對貧困片區農民予以財政金融、農業生產技能培訓和產業扶貧績效考核機制理順來瞄準扶貧[13]。
“2015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提出“互聯網+扶貧”,萬寶瑞提出要發揮“互聯網+”的云計算、大數據和虛擬計算等技術的優勢,分工深化農業經營[14]。汪向東等指出,要高度重視“互聯網+”在扶貧開發中的超常規舉措,推進信息化扶貧[15]。“互聯網+扶貧”成為當前我國開發式扶貧到扶貧開發與生活保障中的引領石,也是新歷史時期內取代傳統扶貧路徑的新思路,更成為貧困片區發展后發趕超的重要抓手[16]。王軍等認為,從“互聯網+金融”“互聯網+企業”“互聯網+創業”和“互聯網+旅游”等推進精準扶貧,發揮精準扶貧的加倍乘數效應[17]。
自秦巴山區甘肅省隴南市首創“互聯網+電商”推進精準扶貧[18],“互聯網+精準扶貧”重心在于其信息化優勢降低個體必要勞動時間,突破空間限制打通貧困片區精準扶貧的“最后一公里”。“互聯網+”最大的優勢在于以聚焦更多的網絡節點促進網絡規模來提高網絡價值進而降低個體交易成本,提高市場交易主體的靈活性,進而以“互聯網+”思維注入電商基因,賦予農民的電商產權,盤活農業農村潛在生產要素培育,推進農產品市場化,實現貧困片區發展后超“彎道超車”。同春芬等認為,要融“互聯網+企業”、“互聯網+農戶”等方式推進“企業+農戶+合作社”的農業經營,實現“互聯網+精準扶貧”[19]。王盈盈等以廣東五華縣為例指出“互聯網+”推進電商進村,激發片區勞動力回流創業,改變了傳統片區的生產經營模式、重塑鄉村關系網絡、重構片區貧困農戶“想脫貧”的鄉村想象和幫扶集中連片貧困農戶脫貧的鄉村意義[20]。
現有文獻對如何解決精準扶貧所面臨的困境缺乏新思路、新措施,存在2個有待深化的研究方向或領域。一是精準扶貧模式研究須要進入創新模式變革研究的階段。現有文獻主要集中于將精準扶貧看作是傳統扶貧的一種升級,基于這種預設框架通過案例分析探索精準扶貧的具體發展形態,這類研究傾向于歷史性總結性的研究而不是在國家大力弘揚五大發展理念的變革時代所需的變革性研究。二是精準扶貧的研究還須進入理論重構、模型建構的階段。現有文獻對精準扶貧的研究多集中在具象化的描述,依賴于具體案例的描述,抽象化的理論重構、模型建構研究不足,并未形成精準扶貧理論結構模型。若要有效地解決精準扶貧實踐中的困境須要結合時代特征,充分發揮精準扶貧中各參與主體的能動性及“互聯網+”技術平臺的優越性,對“互聯網+精準扶貧”模式的研究將成為新的熱點。
2 我國“互聯網+精準扶貧”發展的機遇
2.1 政府政策發揮引領扶持作用
2015年,全國“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互聯網+”行動計劃這一概念。“十三五”規劃提出,互聯網技術與社會經濟的融合發展要大力實施“互聯網+”行動計劃,促進共享經濟的發展。在該政策的積極引導下,我國的互聯網發展進程進入跨境整合和變革的關鍵時期。隨著我國減貧與發展論壇再次對這一概念進行闡述,“互聯網+扶貧”新型脫貧扶貧方式開始逐步取代傳統的扶貧方式。2016年出臺的《網絡扶貧行動計劃》和黨的十九大提出要打贏脫貧攻堅戰,將互聯網技術與精準扶貧融合,是我國取得“精準扶貧”新勝利的特色方案,要以充分認識并發揮互聯網的創新與引領作用,帶動全社會各個參與者,讓13億的人共享發展成果,并且當前我國處于經濟發展的新時期,發展“互聯網+精準扶貧”有助于我國經濟的平穩發展,所以,精準扶貧的實踐發展對于各個參與精準扶貧主體來說都既是機遇又是挑戰。
2.2 貧困地區的電商行業得到初步發展
在電子商務方面,一方面我國貧困地區的創業者、企業等主體利用互聯網技術平臺、結合當地特色,生產并出售特色產品達到增收創富的目的。另一方面,貧困戶還可通過網上購物,來滿足生活生產的需要,節約消費支出。根據商務部統計,截至2017年8月底,在我國農村地區有1 311個淘寶村,比2016年增長68%。2017年全國貧困縣中電商包裹超過百萬件的有445個,其中淘寶村整年網絡零售額要求最少達到1 000萬元,部分淘寶村的網絡零售額甚至超過10億元。淘寶村平均每增加1個網店,便可提供約2.8個就業機會。按此計算,對淘寶村網店的開發可以直接提供84萬多個就業崗位(表1)。在普惠金融方面,普惠金融的發展為我國扶貧提供了一個堅實的經濟基礎。尤其是金融企業為我國貧困地區提供的具有普惠性、多元性、特色性的網上貸款、電子支付及網絡保險等金融服務,彌補了當地創新創業脫貧資金不足的缺陷。截至2017年12月底,螞蟻支付服務提供信貸金融服務,為我國的3 514萬農民通過網上銀行貸款金額達4 062億元;為13億戶農民提供網絡保障服務,累計參保數達4763億筆;向16億戶農村用戶提供互聯網支付、繳費、轉賬、充值等便民繳費服務。
2.3 貧困地區的基建日益完善
在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中,截至2017年,我國的互聯網用戶已經達到71億人;城市網絡基礎設施建設不斷推進,當今我國光纖寬帶普及率已達到60%,3G和4G用戶不斷增加。阿里新農村研究中心的專家分析預測,2019年我國農村地區將有24億的互聯網用戶。但“寬帶中國”地圖顯示,目前我國大多數省份和城市寬帶普及率只有31%~46%。除網絡建設外,對互聯網商戶而言,同樣重要的還包括公路及物流的建設。阿里研究院通過對4萬戶家庭、637個村莊的調查顯示,2016年我國有超過50%的村莊最多有1條道路,2條道路的村莊占29.8%,3~5條道路的村莊占 10.1%,5條以上的村莊僅為3.6%。在同等家庭條件下,鋪設多條道路可使每戶家庭增加家庭財富收入11.93萬元。因此,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交通運輸和物流道路建設,對于幫助貧困人口擺脫貧困具有重要意義。在互聯網技術方面,互聯網技術不僅解決了貧困地區的信息不對稱問題,而且為邊遠貧困山區的人們提供了先進的技術和前沿的視角,隨著電子商務平臺實現農產品和工業產品進入農村市場,各利益相關方共同參與,營造一個多元、開放的生態系統,以眾籌、眾創等共享經濟模式實現創新創業,推動“互聯網+旅游”“互聯 網+ 醫療”“互聯網+金融”“互聯網+創業”等新型精準扶貧方式,使精準扶貧取得加倍的乘數效應。
3 “互聯網+精準扶貧”聯動機制的理論結構模型
3.1 “互聯網+精準扶貧”的創新內涵
2015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云南調研時提出要打好扶貧開發攻堅戰,實施精準扶貧;同年3月李克強總理在全國十二大三次會議上提出要制定“互聯網+”行動計劃,將其納入國家重要發展戰略的頂層設計,至此,學術界開始對“互聯網+”如何與精準扶貧有機融合、更好地助推精準扶貧的發展進行探討。“互聯網+”是基于信息和通信技術的使用,與傳統產業的融合再造并進行生態創新與發展的新型工具及范式。“互聯網+”是新時代下的社會先進生產力的具體表現形式,或是實施社會知識創新的生產資料,是知識創新2.0實現的驅動力,也是新常態新業態下發展共享經濟的本質內涵。“互聯網+精準扶貧”是在扶貧工作中運用互聯網思維、技術等新型生產力,根據貧困人群的脫貧愿望及需求,運用現代信息技術來對扶貧工作方式進行根本性轉變的新的工作模式。利用諸如大數據等新技術使扶貧方式多元化、扶貧工作高效化,整合社會資源力量推進扶貧工作扎實開展,實現扶貧工作在新的社會背景下的發展與變革[19]。
3.2 “互聯網+精準扶貧”的主要特征
3.2.1 跨界融合 “互聯網+精準扶貧”是運用創新思維引導先進技術與扶貧方式的跨界、融匯。跨界讓技術創新擁有堅固的基礎,融合讓大眾智能在新領域發揮最大的優勢。將“互聯網+”融入到精準扶貧工作中,結合新興行業發揮萬眾創新創業的智慧,以更開放的態度、更多元的角度推動精準扶貧事業的革新與重塑。融合、碰撞、創新使得扶貧工作更加高效、準確。
3.2.2 創新驅動 創新驅動的信息技術創新推動我國互聯網產業的發展,電子商務、遠程醫療、新經濟和新產業共享模式的不斷涌現,已成為創新驅動發展的主導力量。互聯網在充分利用整合社會資源方面具有共享、開放的優勢,繼續推進“互聯網+”數字戰略和創新服務模式,將幫助農民擴大農產品銷售渠道,提高農民收入水平,為達到“兩個確保”和貧困人口“兩不愁、三保障”的脫貧目標作出貢獻。
3.2.3 開放生態 開放生態是指與外部環境進行物質和能量的交換的生態系統。一個開放的生態系統是“互聯網+精準扶貧”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征,通過對過去傳統發展模式的溶解與創新,形成一個連接一切并且開放的生態系統,將開放、共享、平等的思想融入到扶貧的實踐中來,激勵政府、企業、個人、公益組織等多元主體協同參與扶貧,體現參與主體多元化、生態扶貧開放化、扶貧效果普惠性的特征。
3.3 “互聯網+精準扶貧”聯動機制模型
所謂聯動,是指多個相互關聯的事物中當其中1個發生變化時,其他的也隨之變化的互動過程。為了清晰地描述復雜元素的交互過程,人們通常采用聯動模型來研究。從系統論的觀點把精準扶貧看成一個系統并構建我國“互聯網+精準扶貧”聯動機制(圖1)。為了更清晰直觀地描述“互聯網+精準扶貧”聯動機制,采用構建模型的方法研究此機制的有效性和長效性。“互聯網+精準扶貧”聯動模型將精準扶貧中的各個主體抽象化,使其組織結構更加直觀,有助于更加清晰地了解其相互關系及相互作用。實際上,“互聯網+精準扶貧”聯動機制是指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指導下,運用互聯網思維,立足先進的“互聯網+”技術平臺,根據本地實際精確識別貧困群體及其需求,政府、社會、市場、社區及個人等多元主體依據當地優勢資源發展多樣化精準扶貧模式,實現我國精準扶貧工作的發展與轉變,以一種全面、持續、均衡、互動的方式開展精準識別、聯動幫扶、動態管理及精準考核等活動,為貧困家庭提供精準幫扶,解決其脫貧的主要制約因素。
3.3.1 “互聯網+精準扶貧”聯動機制模型的運行結構 “互聯網+精準扶貧”作為一個組織形態,該系統或組織既包括內部的運行結構,也包括外部系統的輸入。通過建立動態機制來加快內外部因素的互動與轉化。“互聯網+精準扶貧”的動力系統有內外部之分。其中,內部系統的內生動力是核心,如建立科學合理的貧困識別機制、精準幫扶機制、精準管理機制、精準考核機制,定期、不定期地評估各類扶貧單位工作,及時發現問題,督促各扶貧單位不斷提高能力,全面履行精準扶貧工作,及時履行扶貧主體的職責,既能保證扶貧資源的最大化利用,又能在無形中緩解社會矛盾。相比而言,外源動力的驅動效應則較弱。由于我國歷史文化的影響,貧困、平等、獨立的自主脫貧意識薄弱,更愿意寄希望于上級單位,使得內部制度力量匱乏,從而讓內外部系統互動不足,技術采取激勵措施調動貧困群體脫貧的積極性,當然,內部制度須要依靠外部制度力量推動扶貧方式創新。這種動態機制可以保證精準扶貧的長效機制,也須要保證有序聯動機制的高效,避免系統各環節之間的摩擦(圖1)。
3.3.2 “互聯網+精準扶貧”聯動機制模型的鑲嵌結構 精準扶貧的發展與實踐每一環節都鑲嵌于一個特定的環境中,在特定的環境中鑲嵌著內、外部系統兩部分(圖1)。實線部分即外部系統,即輸入、輸出、反饋。外部系統不斷輸入貧困群體的脫貧需求,并通過現代信息技術平臺將反饋信息進行整合,為公共產品的制定與實施提供理論參考與現實依據,及時解決貧困戶的整體需求,并以發揮政策出口效用的外部系統為輿論反饋及監督的主要部分。以此形成“輸入—整合—實施—反饋”的有序聯動過程。虛線內即內部系統,主要是指精準扶貧的各個主體及相關配套機制,“互聯網+精準扶貧”聯動模型有效運轉的關鍵在于主體的職責明確以及有效分工,避免責任缺位或錯位,影響扶貧工作的具體落實。政府、社會、市場、社區及個人作為多元扶貧主體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同時須建立以云計算和大數據為技術應用支撐的智慧精準扶貧機制平臺,將精準扶貧戰略與“互聯網+”有機結合,實現精準識別信息化、精準幫扶多元化、精確管理動態化、精準考核透明化。
4 基于案例的現實運用——以廣東省揭陽市軍埔村為例
在我國扶貧脫貧進入攻堅拔寨的關鍵期,打贏扶貧開發攻堅戰必須運用“互聯網+”思維及技術,切實讓“精準”在扶貧中落到實處,因此,構建“互聯網+精準扶貧”聯動機制模型并合理運用在現實案例中,目的在于實現精準扶貧與互聯網技術的緊密結合,更全面地發動各個參與主體,建立信息化、多元化、動態化、透明化的扶貧機制,提高扶貧效率、解決扶貧困境。本研究以廣東省揭陽市軍埔村的脫貧實踐為例,剖析軍埔電商村利用互聯網技術實踐精準扶貧的發展歷程、總結軍埔村“互聯網+精準扶貧”的運行機制對開展我國“互聯網+精準扶貧”工程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4.1 案例背景介紹
“淘寶村”是以網商聚集的村落為主體,以淘寶或天貓等電商平臺為主要交易載體,基于線上交易模式形成規模效應與協同關系的網商群聚現象。“淘寶村”能夠有效地拓寬地方產業銷售渠道,提升本地優勢產業競爭力。據統計,2016年廣東省已有超過262座“淘寶村”,每年創造就業機會超過15萬個。以全國聞名的揭陽市揭東區錫場鎮軍埔村為例,軍埔村本屬于食品專業村,數十年前由于本地食品加工廠的倒閉直接導致村民生存艱難,造成大量勞動力流失。隨著電子平臺的出現,開始有村民回鄉創辦淘寶店,在發展初期,軍埔村主要以線上零售為主,在政府的牽引下,軍埔村大力發展網絡覆蓋工程、道路物流基礎設施建設,培養電商人才,探索出“互聯網+農業”“互聯網+旅游”和“互聯網+金融”等新型扶貧模式。短短1年的時間,軍埔村就發展成為擁有近千家網店的“淘寶村”,交易額翻了數番,2016年“雙十一”購物節過后軍埔村甚至創造了超過1億元的銷售紀錄。如今,軍埔村已經形成了一個多主體良性共生互補的“互聯網+精準扶貧”系統。
4.2 軍埔村“互聯網+精準扶貧”的運行機制
4.2.1 多元扶貧主體格局形成 個人及社區層面,自2012年軍埔村12名創業青年經營淘寶店的成功經驗傳播以來,當地越來越多的新生代農民工、受過高等教育的畢業生紛紛回村創業開起淘寶店。當前全村已有350多戶1 600多人從事電商銷售,開設了2 300多家網店,月交易量約80萬筆,月成交金額超1.2億元;社會及市場層面,我國各大通信運營商、快遞公司陸續進入軍埔村設置自助服務終端,新建基站,設立服務辦事處等。榕城鞋業、普寧國際服裝、云梯電商、邦想電商等企業紛紛在軍埔村建立電商服務平臺;政府層面,軍埔村政府通過推動成立電子商務服務中心,為符合資格的電商戶提供借貸補貼和減免優惠。同時,鼓勵民間投資,設立揭陽職業技術學院電商培訓中心,邀請專家為當地居民提供免費培訓。隨著近年來政府對淘寶村的扶持力度不斷加大,淘寶村已從野蠻生長逐漸步入“草根創業+多元主體支持+平臺賦能+大數據管理”相結合階段,當前軍埔村淘寶村已呈現多元化扶貧發展態勢,逐漸衍生出以政府、社會、市場、社區及個人為扶貧主體的格局[20]。
4.2.2 構建扶貧信息綜合平臺 在“互聯網+”的背景下,揭陽市通過整合互聯網信息技術和扶貧政策,建立創業服務中心,將“互聯網+”和精準扶貧戰略有機結合,構建扶貧綜合信息平臺。在精準識別、管理與考核上,依托于網絡技術對貧困地區農戶建檔立卡,建立貧困戶信息數據庫,以便于群體特征的分類與分析,提升扶貧政策的精準性,同時保證貧困戶脫貧后按時退出,便于考核。在精準幫扶上,軍埔村實施“互聯網+電商”扶貧,服務中心通過電商平臺嫁接上游的原產地農產品生產基地及下游企業批發商,縮短銷售路徑把特色產品推廣到全國甚至全世界;推廣“互聯網+金融”扶貧模式,2013年揭陽市當地政府頒布實行企業貸款風險補償、貸款貼息等優惠補貼政策,政府及當地普惠金融服務中心結合當地發展實際為創業者們營造一個良好的創業發展環境;同時軍埔村針對當地專業技術人才不足的困境,分層次、分人群對當地人進行免費的專業技術培訓。
4.2.3 打造“一鎮一品”品牌工程 近年來,揭陽市各地按照政府規劃文件和工作要求,構建“互聯網+農業”新型產銷體系,依托當地的優勢產業,實現原產地特色產品與當地及周邊產業對接,把“一鎮一品”工程的產前、產中、產后有效結合起來,同時啟動建設“一鎮一品”電子商務示范園,成立“一鎮一品”電商運營中心,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不僅提高村民的收入,帶動當地農產品和特色產業的發展,同時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2016年全市30個農業“一鎮一品”示范鎮中的示范企業通過與網絡平臺的合作全年交易額達上億元。
5 我國“互聯網+精準扶貧”模式的實施路徑
5.1 完善網絡交通工程,培育新型創業人才
首先,要加快網絡覆蓋工程的建設。基礎設施建設是推進“互聯網+精準扶貧”工作的基礎,應加快扶貧重點縣鎮光纖基站的建設,盡快落實貧困地區的網絡全覆蓋,讓其搭上“互聯網+”的快車;推進智能產品普及、加大家電下鄉優惠政策的優惠力度,引導貧困戶主觀意愿提升農戶購買智能產品的積極性,為“互聯網+”入駐農村發展電商扶貧提供基礎設施保障。其次,完善農村交通物流體系。利用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技術,規劃建設現代農業物流基地、物流園區、配送中心等物流系統,完善網絡交通工程,實現高效節約化運作和智能透明化管理。最后,加大人才的培養引進力度。配合基礎設施建設落實對于基層干部、部分農戶的技術培訓,著重應用性教育,同時鼓勵農村青壯年創新創業,培養扎根貧困地區的大眾創業人才。
5.2 轉變精準扶貧理念,構建多元主體扶貧格局
精準扶貧的各個參與主體作為多元扶貧主體的組成部分,在規劃上應將各個扶貧主體統一起來,大力動員并整合社會各類主體形成聯動效應,形成攻堅扶貧的合力。要有效動員政府、市場、社會、社區及貧困主體等力量參與扶貧。“互聯網+精準扶貧”的有效實踐需要政府在五大發展理念的指導下制定“互聯網+精準扶貧”優惠政策,促進互聯網企業與各領域扶貧深度融合,通過各種多媒體手段宣傳“互聯網+精準扶貧”,強化農民運用互聯網脫貧致富的意識,培育現代化農民,推廣典型、總結教訓,打造因地制宜的品牌建設。對于具體貧困人口的精準扶貧的掌握,由于村委或社區距離扶貧對象最近,掌握信息最靈敏,所以由村委或社區來提供精確貧困人口的信息是最好的途徑,而政府須要從宏觀上保障基本公平,市場應發揮創新驅動作用,社會組織及志愿者系統須要在精準幫扶中發揮其靈活性、專業性特點。構建“一對一”、“一對多”和“多對多”聯動機制,逐步形成多種形式社會扶貧新格局。
5.3 打造智慧扶貧網絡平臺,實施動態管理機制
首先,搭建智慧精準扶貧網絡平臺和高端載體,建立縣(市、區)、鄉(鎮、村)信息互建互聯機制,使精準識別信息化、精準幫扶多元化、精準管理動態化及精準考核透明化。其次,動態管理機制的實施,可積極調整社會貧困的內部結構,有效整合政府合作銜接、扶貧資金和立項目的,扶貧培訓意識和責任參與。在精準識別方面,運用互聯網技術,為貧困戶建檔立卡,通過遙感技術(remote sensing,簡稱RS)和地理信息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簡稱GIS)等工具,分析貧困戶的分布特征。同時,利用大數據技術建立多維貧困的測定標準。在精準管理與考核方面,依托智慧精準扶貧網絡平臺,建立動態追蹤機制,及時記錄并幫扶農戶脫貧。同時依據互聯網的相關實時監測數據,推進監督考核透明化,實現多元扶貧主體及資源的無縫連接。在精準幫扶方面,依托互聯網信息化技術,通過“互聯網+金融”“互聯網+營銷”和“互聯網+醫療”等專業化、精細化、現代化手段幫助貧困戶脫貧。
參考文獻:
[1]習近平赴湘西調研扶貧攻堅[EB/OL]. (2013-11-03)[2017-06-08].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03/c_117984236_8.htm.
[2]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R/OL]. (2014-03-05)[2017-06-08].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305/c49150-24536558.html.
[3]Carney D. Implementing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J].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1998(12):1474-1479.
[4]Keating M. The invention of regions political restructuring and territorial government in West Europe[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1997(3):383-398.
[5]Ravallion M,Walle D V D,Datt G . Quantifying absolute povert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J].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1991,37(4):345-361.
[6]Park A,Wan S,Wu G B. Regional poverty targeting in China[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2(86):123-153.
[7]Copestake J,Dawson P,Fanning J P,et al. Monitoring the diversity of the poverty outreach and impact of microfinance:a comparison of methods Uusing data from peru[J].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2010,23(6):703-723.
[8]鄧維杰. 貧困村分類與針對性扶貧開發[J]. 農村經濟,2013(5):42-44.
[9]羅江月,唐麗霞. 扶貧瞄準方法與反思的國際研究成果[J]. 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31(4):10-17.
[10]張笑蕓,唐 燕. 創新扶貧方式,實現精準扶貧[J]. 資源開發與市場,2014,30(9):1118-1119,1081.
[11]張玉強,李 祥. 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的精準扶貧模式[J]. 重慶社會科學,2016(8):64-70.
[12]陳亞琦. 互聯網時代電子商務發展規律及其路徑探析——基于時空分析視角[J]. 河北學刊,2015,35(5):219-222.
[13]趙秀蘭. “互聯網+”精準扶貧模式:主要內容與政策建議[J]. 農村經濟,2017(8):57-61.
[14]萬寶瑞. 我國農村又將面臨一次重大變革——“互聯網+三農”調研與思考[J]. 農業經濟問題,2015,36(8):4-7.
[15]汪向東,王昕天. 電子商務與信息扶貧:互聯網時代扶貧工作的新特點[J].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15(4):98-104.
[16]魏嘉文,田秀娟. 互聯網2.0時代社交網站企業的估值研究[J]. 企業經濟,2015(8):105-108.
[17]王 軍,吳海燕. “互聯網+”背景下精準扶貧新方式研究[J]. 改革與戰略,2016,32(12):111-114.
[18]鄭瑞強,王 英. 精準扶貧政策初探[J]. 財政研究,2016(2):17-24.
[19]同春芬,張 浩. “互聯網+”精準扶貧:貧困治理的新模式[J]. 世界農業,2016(8):50-56.
[20]王盈盈,謝 漪,王 敏. 精準扶貧背景下農村電商關系網絡與地方營造研究——以廣東省五華縣為例[J]. 世界地理研究,2017,26(6):119-130.周曙東,張 冬. 基于DEA-Tobit模型的花生種植戶生產效率及其影響因素分析[J]. 江蘇農業科學,2019,47(3):283-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