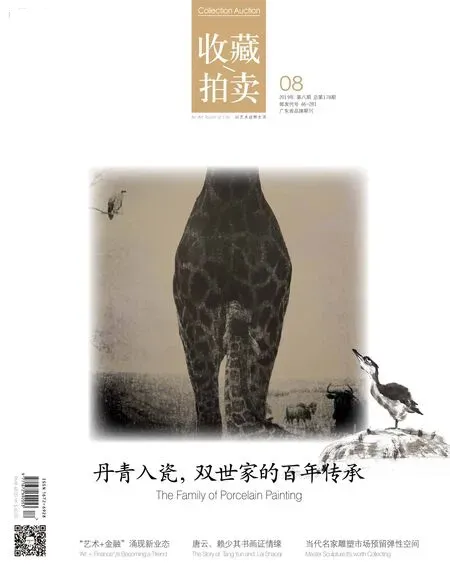觀畫,也觀一場(chǎng)歷史演義
文:木子 圖:受訪者提供
采訪江哲讓人產(chǎn)生一種錯(cuò)覺,好像來到了百家講壇的歷史大講堂。近現(xiàn)代的歷史年代、事件、背景、人物在他口中侃侃而來、如數(shù)家珍。他就像一個(gè)布道者,用他的畫面作為契機(jī),引發(fā)觀者的疑問和思考。如果說學(xué)術(shù)的跨學(xué)科研究已經(jīng)成為一種發(fā)展趨勢(shì),那江哲的作品無疑是走在前列的那一個(gè)。

《孝順竹》 60cm×60cm 布面油畫
江哲的采訪時(shí)間不大好約,與一些喜歡偏居一隅的藝術(shù)家不同,他的日程安排總是滿滿的,經(jīng)常要到處跑來跑去。好奇于一個(gè)畢業(yè)不久的職業(yè)畫家何以如此忙碌時(shí),他解釋說,要與策展人交流;外出考察、學(xué)習(xí);還要對(duì)各大學(xué)術(shù)前沿發(fā)展趨勢(shì)有所了解,以找出自己的發(fā)展方向與空間。
也許正是緣于這樣的積累與沉淀,才產(chǎn)生了不同于其他的作品表達(dá)。
歷史演義的傳達(dá)
看江哲的作品不難發(fā)現(xiàn)其與歷史事件的聯(lián)系貫穿其中,看他的畫就像一個(gè)個(gè)歷史小劇場(chǎng)鋪陳在眼前。在作品中能看到許多清末民初的人物——看書的文人、私塾里的孩子、剪辮子的人等等。這些人物形態(tài)各異,但是每一個(gè)的面孔都模糊不清,似是藝術(shù)家有意為之,讓來自百年前的人物模糊個(gè)性,從而彰顯他們所代表的群體特征。
從小喜歡歷史的江哲,在大學(xué)后,開始對(duì)清末民初的歷史有了新的認(rèn)識(shí)。他發(fā)現(xiàn)這段時(shí)間有著很多不同于以往認(rèn)知的一面,有很多的模糊性,值得探討發(fā)人深思的東西。于是這段歷史也成為了他的創(chuàng)作重點(diǎn)。在江哲看來,“大的歷史時(shí)勢(shì)造就了一大批在中國(guó)歷史上留下璀璨星光的人物,這些人物的不凡人生經(jīng)歷構(gòu)成了這段豐富的歷史。而這里更不乏有很多有爭(zhēng)議的人物,而對(duì)有爭(zhēng)議的人物及其相關(guān)事件進(jìn)行重新探討就構(gòu)成一個(gè)可供我們描繪和表達(dá)的空間”。
但他的作品又不同于寫實(shí)性的歷史畫,江哲定義其為“歷史的演義性”,即是不用根據(jù)客觀的歷史細(xì)節(jié)進(jìn)行某個(gè)場(chǎng)面的再現(xiàn),它的畫面不需要大量的歷史細(xì)節(jié)作為支撐。但同樣需要閱讀大量一手材料,并對(duì)歷史事件有一個(gè)比較立體的了解,然后再根據(jù)自己的觀點(diǎn),重新安排人物、地點(diǎn)、細(xì)節(jié)等構(gòu)建一個(gè)演義性的歷史場(chǎng)景。

《辛亥.剝落 》 90 cm×120 cm 布面油畫

《利瑪竇與〈山海經(jīng)〉》 171cm×150cm 布面油畫
象征意象的運(yùn)用
江哲的作品中經(jīng)常會(huì)出現(xiàn)石獅子、仙鶴、竹子等這些具有象征意義的中國(guó)傳統(tǒng)物件,通過這些傳統(tǒng)符號(hào)來表達(dá)自己對(duì)于歷史的理解。例如仙鶴通常在畫面中充當(dāng)情緒和氛圍的營(yíng)造元素;竹則是傳統(tǒng)耕讀文化的表征;石獅子則是王權(quán)的象征。
老照片的參與
中國(guó)19世紀(jì)末的照片大部分為外國(guó)人所拍攝,拍攝者以一個(gè)獵奇者的心態(tài)進(jìn)行拍攝,拍攝對(duì)象多為神秘的景觀、異國(guó)風(fēng)俗、殘酷的刑罰等。而正是這些圖像構(gòu)成了我們對(duì)中國(guó)19世紀(jì)末至20世紀(jì)初的最初印象與認(rèn)識(shí)。它既是當(dāng)時(shí)的客觀存在,又具有很強(qiáng)的片段性和主觀性,運(yùn)用老照片進(jìn)行重合組裝再加上一些象征性的符號(hào),能產(chǎn)生另外一些有趣又具備思考性的圖像。

《庚子年》 160 cm×120 cm 布面油畫
歷史事件的重述
在對(duì)鄭和的闡釋中,江哲強(qiáng)調(diào)的不是簡(jiǎn)單的盛世繁華,更不是代表國(guó)家形象的鄭和,而是文官集團(tuán)和下西洋這個(gè)事件的關(guān)系。這種關(guān)系正是作者試圖用畫面去理解的東西。
袁世凱在近代歷史上是個(gè)備受爭(zhēng)議的人,而導(dǎo)致這種爭(zhēng)議的最大原因是他的稱帝事件。江哲把他的人生分成幾個(gè)階段進(jìn)行討論,《閑云野鶴》便是其中的一段。 由此便會(huì)發(fā)現(xiàn)他人生的好多階段都是具備改良視野的。但多少有雄才偉略之人就因人生最后的錯(cuò)位移步而輸了生前身后名,讓后人感慨不已。

《鄭和下西洋之麒麟來朝》 176cm×103cm 布面油畫

《閑云野鶴》 50cm×60cm 布面油畫
江哲把自己的創(chuàng)作融入歷史的維度中,給了觀者另一種觀看、思量歷史的角度。 在他看來,自己的作品并不抽象,而是很真實(shí)的,連通著過往、現(xiàn)在和未來。“最好作品是能引領(lǐng)人進(jìn)入思考狀態(tài)的”,這也需要有大量的知識(shí)結(jié)構(gòu)、人生閱歷等作為支持的。
江哲坦言在這樣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過程中,自己是幸運(yùn)的。“研究生最重要的是提出問題,建立系統(tǒng)。”江哲在不斷提出問題中,逐漸建立起自己的風(fēng)格。
對(duì)當(dāng)今社會(huì)的觀照
“現(xiàn)在不同于10年前,那時(shí)候你可以慢慢畫,慢慢學(xué),現(xiàn)在如果你再縮在家里閉門造車,那就是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一種逃避,也無法跟上時(shí)代發(fā)展的步伐,也就無法反映社會(huì),承擔(dān)起相應(yīng)的社會(huì)責(zé)任。”江哲說。
極少從一個(gè)90后的藝術(shù)家口中聽到社會(huì)責(zé)任感這個(gè)詞,很是意外。回頭一想,跟他的作品聯(lián)系起來就覺得情理之中了。作為一名熱愛歷史、熟悉歷史,又在用作品去表達(dá)自己獨(dú)有的歷史觀的青年畫家,必然會(huì)對(duì)這個(gè)社會(huì)產(chǎn)生很多思考。
在江哲的創(chuàng)作中,有一部分是配合政府部門的主題性命題創(chuàng)作。江哲說:“事實(shí)上,這種主題性創(chuàng)作是屬于公共藝術(shù)的范疇,跟社會(huì)上極大部分人的記憶、文化、知識(shí)結(jié)構(gòu)是息息相關(guān)的,也是一種時(shí)代氣息的表達(dá)。就像廣美的李勁堃院長(zhǎng)說的‘你關(guān)注社會(huì),社會(huì)就會(huì)關(guān)注你’。目前,在學(xué)院體系里做這種主題創(chuàng)作的已經(jīng)很少了,近些年大家都在強(qiáng)調(diào)繪畫本體、個(gè)人風(fēng)格、創(chuàng)新等。但如果你的創(chuàng)作無法與社會(huì)發(fā)生關(guān)系,只專注于個(gè)人層面的表達(dá),很容易掉入虛空、消極的情緒之中,就無法肩負(fù)起社會(huì)擔(dān)當(dāng),去傳達(dá)正面、積極的信息。”
這也許就是一位中大歷史系研究生在看到江哲的畫后,馬上將其引為知己的緣故吧,他的畫已經(jīng)遠(yuǎn)超出單純的藝術(shù)范疇了。
未來的作品將不限于架上
在采訪過程中,江哲對(duì)于作品中運(yùn)用的技藝和技法很少談及,在江哲看來技法應(yīng)是為藝術(shù)品的內(nèi)涵服務(wù)的。就像他的同門師兄許健所指出的:在他的作品中,技術(shù)在內(nèi)涵面前被完全弱化了。僅有技法好的作品會(huì)變成工藝品,只有內(nèi)涵才可以讓其成為藝術(shù)品。
在江哲對(duì)作品的規(guī)劃中,未來肯定要做非架上的作品。“我做作品要輸出的是思想和觀念,架上媒介和材料只能滿足一部分的需求,肯定有一些想表達(dá)的平面上滿足不了。所以以后一定會(huì)借助一些非架上的其他媒介的東西。”
“作為輸出觀念型的作品,無論是架上作品還是裝置作品,你可以銷售的不僅是作品本身了,還可以出售草圖、小畫、甚至其衍生品。消費(fèi)者會(huì)覺得不僅是買了一幅裝飾性的作品,而是買了一種文化。目前比較藝術(shù)市場(chǎng)比較前端的上海已經(jīng)在一些展覽或畫廊銷售中采用這樣的模式了。”
所以一幅有文化內(nèi)涵的作品,其市場(chǎng)前景才是巨大的。

《魏源與〈海國(guó)圖志〉》 352cm×103cm 布面油畫
符號(hào)性的隱喻
在江哲的作品中,小人物的生計(jì)、大人物的起伏;牛車、枯木、綠柳等等這些圖像和符號(hào),構(gòu)成了一個(gè)當(dāng)下人對(duì)兩種文明碰撞后產(chǎn)生的矛盾心理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