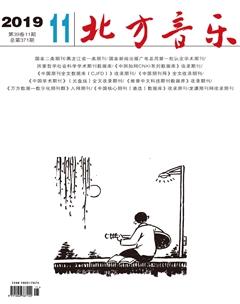靈響于藝術殿堂的寺廟聲
牛志遠
【摘要】對于世界上的大多數民族,音樂是民族文化的重要體現途徑與載體之一是廣泛被世界各族人民及學術界所認同的。隨著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的現代化快速進程,縱觀世界民族音樂文化的歷時發展態勢,不難發現其發展過程的復雜化與內容形式的多樣化。受世界音樂組織形式的多元化與構成元素多樣化之影響,各民族小眾且單一的傳統音樂元素生存境地受到極大的威脅。那么,以何種的創作思維與技術形式在堅持民族本位的情況下去順應時代大勢,使民族傳統音樂元素在世界音樂文化發展洪流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時使得民族文化得以全新形式的體現,是每一個民族音樂學研究者應予以高度重視的話題,也是每一個音樂學者和人類學家為之努力的重要原由之一。蒙古族著名的青年作曲家額·那日蘇的經典代表作品馬頭琴狂想曲《一百零八轉經筒》比較完美的詮釋了此問題。此文筆者將以這首作品以及這場展演為例來闡釋蒙古族音樂學者對于保護傳統音樂元素與民族文化的理論與實踐中的獨特思考。
【關鍵詞】《一百零八轉經筒》;傳統音樂;民族文化
【中圖分類號】J60 【文獻標識碼】A
引言
國家藝術基金2018年度舞臺創作資助項目《一百零八轉經筒》暨額·那日蘇民族音樂作品展演于2018年12月15日在內蒙古藝術學院演藝廳舉行,次日《一百零八轉經筒》作品研討會在內蒙古藝術學院召開,此次展演與研討會的召開無疑是蒙古族音樂創作史上的又一里程碑。根據國家藝術基金2018年度資助項目立項名單可以看出,國家立足弘揚與發展中華民族傳統優秀文化,堅定不移貫徹黨的民族路線,在文化藝術層面,大力支持少數民族音樂藝術文化的創新與發展。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其中包含文化、信仰、宗教、藝術元素等等,那么民族的怎樣才能成為世界的,以何種形式與時代同流,這些問題是催促每一個民族藝術學者創新意識快速轉型的不竭動力,“一些作家已經尋求描述非西方音樂傳統的價值和情緒,并不把自己的限制在他們的結構和形式中”。
額·那日蘇是一位蒙古族青年作曲家,能夠無形中將民族學、社會學、人文學、宗教學的因素體現在作品中,在學術界及其相關領域的不同組成要素快速發展的勢頭下,學者身份的組成方面更加的需要多樣化,不在單一于某一特定研究領域的局限,以音樂學為例,其中有專門研究形態學的、有專門研究音樂美學的等等,在以往這些學科研究方向范疇中,總是潛移默化的體現出一種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學術態度,在當今這個趨于中性化的時代,人們的思維也在發生著重大的改變,更加的多元,如今更加要求人們要扎實立足研究本源且要涉獵廣泛的研究姿態。額·那日蘇則無疑是一位立足民族音樂創作本源且涉獵多領域的作曲家。
《一百零八轉經筒》這首作品的題材來自于藏傳佛教文化,蒙古佛教是以西藏佛教為典范的,大部分的蒙古佛典皆譯自思藏佛典。轉經筒又稱“嘛呢”經桶,它是藏傳佛教的宗教標志,與佛教的八字真言與六字真言有關,六字真言即“嗡嘛呢叭咩吽”,藏傳佛教認為持誦真言越多,越加表明對佛的虔誠,可以減輕人間痛苦,包括心理與身體之苦,轉經筒則是人們除口誦外的另一種形式,即將六字真言裝于經筒內,經筒外也刻有六字真言,信徒以及一般人們可以用手轉動,每轉動一次就相當于念誦經文一次。因佛教文化的深奧性,以及出于作者此文的初衷,在此就做簡單敘述。通過作者本人的敘述,他的創作靈感來自于一次寺廟旅途,這些靈感承載著他深厚的音樂修養與民族情懷在他后期的創作中呈現出沖破傳統的獨到創作思維方式與手法,將本民族的民族文化與民族音樂相結合,將歷時文化的演變做了深刻的的總結。他的現代化與傳統結合的創作思維不僅是學者們一般認為的技術上的中西結合,比如音樂創作配器上的中西結合,調式的結合,更為寶貴的是將這種結合進行了全新的解讀,沖破了人們所局限認為的一般意義上的現代與傳統,西方與中國的結合,這在他的這場展演中體現了出來,無論是獨奏曲還是協奏曲都體現出這種思維的價值所在。在研討會上各路民族音樂學前輩對他的創作給予了高度評價與改進建議。下文則對額·那日蘇的獨特思維的體現與學界對他創作的評價以不同角度進行解釋與評析。
一、沖破傳統創作的思維
傳統音樂是特定社會成員情感意愿的表現。蒙古族現代傳統文化形式與內涵深受自古以來蒙古族游牧生活生產方式使蒙古族產生了特有的民族文化與民族文化認同情感以及隨之產生的民族代表性文化載體,在音樂藝術方面,則出現了比如極具代表性民歌體裁“長調”、極具民族代表性的樂器“馬頭琴”、以及極具自然風格特征的歌唱形式“呼麥”這些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隨著時代的發展與社會對文化藝術的需求變化,蒙古人民在文化藝術方面的發展也呈現出與時俱進的特征,我們經常習慣于用現代話語為過去的事物下定義,比如為區分與現代民族傳統創作的區別,稱過去的傳統藝術為原生態,這無疑是具有歷史色彩的陳述話語。往往不知情的局外人將原生態音樂與傳統音樂相淆,認為原生態就是傳統,原生態是指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無刻意的生活藝術形式,傳統是隨著原生態的發展而來,而當下人們所聽到的原生態則是建立在傳統之上的,這是兩個概念,這可能有些讓人不容易理解,比如在游牧民族時期,長調是由于蒙古人民自然的生活方式與地理所形成的一種游牧唱法,更多的是為生活而服務的,這可謂是現代話語中的原生態,隨著時間對原生態環境的洗滌,城鎮化的突飛猛進,人們精神需求的提升,原生態逐漸褪色,現在的長調則是受到正規專業院校專業技術手段的浸染,唱法以及處理手段都發生了改變,稱之為傳統,是藝術化的舞臺藝術,也可稱之為現代話語體系下的原生態。
額·那日蘇的創作思維突破了傳統的束縛,20年代至60年代,多數蒙古族藝術創作都局限于單一的民族藝術的元素,比如長調獨唱,馬頭琴獨奏等等,隨著社會普遍審美要求的提升,在70年代以后,蒙古族創作呈現出多元的苗頭,出現了大量的合奏,重奏等,這可以說是一個藝術上的里程碑,額·那日蘇正是這個里程碑之后不久的作曲家,他走在世界音樂變遷的時代,全球政治、經濟、文化趨于從西方化——后西方化——中性化的道路上,他豐富的學習經歷加之他先天的民族傳統血液,使他創作出了《一百零八轉經筒》這種突破傳統思維束縛的新民族藝術作品。
《一百零八轉經筒》是一首馬頭琴狂想曲,馬頭琴是蒙古族傳統樂器,狂想曲一詞來源于古希臘,是西方創作中以民歌曲調為主題而發展起來的器樂幻想曲,由此可見作曲家的創作心境,將西方民族的藝術話語嫁接到蒙古族傳統音樂上,使其形成中西交融,這種交融與以往的交融不可相提并論,以往的創作之中西結合都是用傳統樂器為西方意識所服務,這首作品則打破了這種傳統創作 方式的思維,讓西方的意識為我們的民族音樂服務,這無疑是一個現代蒙古族音樂藝術創作的里程碑。傳統的馬頭琴曲目都是用純四度定弦,這首作品別出心裁的利用增四度定弦,不僅體現了佛教文化的特殊音響,還將民族文化以西方作曲技法得以全新展示,使馬頭琴演奏技巧突破傳統演奏模式,將以往傳統所做不到的以特殊方式得以拆解重組,使全曲達到一個傳統之外的新高度。
二、立足民族文化本體,放眼多元藝術載體
中國傳統音樂的生成和狀況直接與其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政治以及整體文化發展狀況影響。在中國,五四運動以后,中國在軍事、經濟、文化上大量吸收西方經驗,以西學為主要發展趨向,提出“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等一系列上層建筑標簽,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以及時代的進步,越來越多的傳統文藝工作者以及學者受西方思維的約束,這不僅僅體現在現代文藝創作、學術研究、客觀實踐中,還深深的倒過來影響著傳統的方方面面,比如在進行傳統藝術批評時,人們時刻在用西方的話語與思維來作為批評標準。比如在音樂作品創作時,哪怕是民族音樂作品,首先置于頭腦的是怎樣將傳統與西方因素相結合,往往以此創作出的作品引以為傲,不可否認,這樣的創作是現代化的產物,但是在近30年左右,甚至更早,中西結合的藝術形式已經層出不窮,已經不在是一個新穎的話題,當一個事態從新穎發展到大眾甚至到疲憊的時候,這背后所蘊含的人文態度其實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當一個事物發展到一定的零界點,也就代表著事態的轉型以及重塑。近年來發生在藝術界的一個重要的現象是學者們從研究西方民族的視域慢慢的轉向了自己的民族,這無疑是后西方化的結果,以批評西方化為主的意識形態,可以說中國的學者在一定程度上的視域回歸也是受到西方化的影響。當然這是歷史的選擇,但是怎樣在歷史的必然選擇中不迷失自己的方向以及進行自身的選擇是值得深思的話題。在以往的民族藝術創作中,創作者大量使用西方創作手法,甚至將傳統藝術因素改變的面目全非,這無疑是現代化學院西化的影響,出生在80年代以后的文藝工作者已經悄然無聲的進入到這個影響范圍內,文化自信、民族自信不是口頭語,他背后需要的是局內人與局外人由內而外的共同認同,這種認同包括審美角度、文化感知角度、人文角度等等,那么在后西方化的過程中,怎樣將傳統文化置于世界人民認同層面,突破西方化的控制,絕地求生。
每一首作品背后都有著一種事件的支撐,為了情感而作,為了事件而作,額·那日蘇的《一百零八轉經筒》則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場上,不是單一的為了取悅人們的審美,而是用西方的音樂話語元素將蒙古族佛教文化以襯托的方式予以呈現,為什么以這首作品來解讀和以往的中西結合的藝術作品之不同,從文化感性角度,可以從這首作品中體悟到,他打破了以往的用中西結合的方式為西方意識服務的格局,它正是以中西結合的方式用西方元素為中國民族傳統文化所服務,增四度雖然是西方的音樂技術理論話語,它有它的特性,以及抒發情感的音響類型效果,增四度是不和諧音程,馬頭琴打破傳統定弦方式改為增四度,這對于演奏員更是一個極大的挑戰,佛教是中華民族的主要 教派之一,他有著虔誠、行善的教性,善惡分明,對信徒的價值觀起到積極的作用,是正面且高貴的教派,在寺廟中經常聽到誦經的聲音,它是一種并不協和的音響,那么他為什么不和諧,還有待考證,但是經過幾千年的過渡,人們的意識中已經下意識的對這種音響產生敬畏,只要一響起,人們則獲得了一種特定的似乎不成文的信號,那就是敬仰,這首樂曲馬頭琴運用增四度 定弦就是為了起到傳遞這種信號的作用,也是佛教象征性的宗教音樂特質,全曲運用樂團協奏曲的西方化創作手法,在音響上突破了單一的民族音樂風格元素的限制,使民族文化借用西方的手法達到一定的高度,可謂是站到巨人的將肩膀上。額·那日蘇的這種立足于民族文化本體,尋求音樂上的多元載體形式為民族音樂服務的眼界與獨特的思考無疑將引領蒙古族民族音樂更上一層樓。
三、“場”遷移過程中的審美認同差異
不同的國家和民族都有屬于自己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是一個隱形于不同社會的群體意識形態,約束著人們的行為,主持著價值觀念,當人們想要將這種文化顯性的為世界所知,一定需要一定的傳播載體,音樂無疑是活生生的例子,在西方,基督教以教堂為圣地,由此產生了教會音樂,作為人們對于此宗教文化的認同以及遵從,也是基督教的標簽。包括還有許許多多的宗教文化都有著屬于自己的宗教音樂。然而宗教隨著社會的發展,內部的結構也在發生著不同程度的改變,其宗教音樂的功能也隨之改變,起初從西方來看,格里高利一世為統治教會而創生出了格里高利圣詠,基督教為統一教會而創生出圣經以及基督教歌曲,許多的音樂家也都是從傳教士而來,他們的創作也都是為教會服務,隨著時間的發展,教會音樂的功能也在向多元的形式發展,不在局限于統治的功能,比如還有審美功能,最容易理解的就是聽到某一種音樂就能很快的辨別它的歸屬,這就是一種審美認同,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當人們的精神需求提升時,對待事物就不是單一的某方面的需求,現在的很多的宗教歌曲被拿上舞臺,不在局限在特定的教堂或者廟宇,但是在這種場遷移的過程中避免不了使人們的審美認同發生改變,比如為了展示特殊的宗教意義,要求演奏者的身心投入后產生奇怪的動作以及神情,導致觀眾由此發笑或者是不理解,其實換句話說就是一種認同缺失,但是在許多的寺廟或者教堂,即使主持教會儀式或者佛法儀式的人為達到儀式所要表達的意義出現某種怪聲或者動作,人們也會肅然起敬,這是為什么。筆者也曾因田野多次參加過類似的活動以及儀式,仔細觀察,首先就是人們在特定的儀式氛圍中,其個人的心里被特定場域氛圍所牽引,不自覺的形成心里認同,第二,人們將自身已經身緣其中,這是一種場的認同,所以當人們在音樂廳以音樂的形式去感受佛教文化的時候,就出現對該文化所屬傳統場域的聯想,以至于產生感受的落差
《一百零八轉經筒》的創作恰恰將這樣的認同差異最小化,別具想法的配器以及旋律,雖然是在音樂廳,但是將人們的審美緊緊地與在傳統場域的審美相連接,使人們一樣肅然起敬,使人們脫離了場域對審美觀念的束縛,將音樂與文化完美的結合。
四、結語
在研討會上,各路學者專家對《一百零八轉經筒》給予了高度評價以及建議,內蒙古藝術學院音樂學院院長楊玉成教授對于此次研討會的整體結構以及全方位視角做出整體概述,蒙古國國立文化藝術大學的額爾敦其美格教授,對馬頭琴狂想曲《一百零八轉經筒》這首作品的調性、音階、節拍以及文化內涵等方面做了全方面的分析與解讀。內蒙古自治區著名作曲家色·恩克巴雅爾、內蒙古藝術學院音樂學院副教授哈斯巴特爾、中國音樂學院教授、著名作曲家劉順、內蒙古民族大學音樂學院院長、著名作曲家溫澤、中央民族大學著名作曲家斯琴朝克圖、中國-東盟音樂周藝術總監、廣西藝術學院教授鐘峻程、著名作曲家、內蒙古藝術學院教授崔逢春、蒙古國國立文化藝術大學教授那森巴特、內蒙古師范大學教授民族音樂學家松波、著名作曲家、內蒙古藝術學院教授好必斯、內蒙古自治區著名作曲家原內蒙古藝術研究所副所長段澤興、中央電視臺著名導演朱智忠都分別從不同的及誦讀對此作品進行了詮釋與建議。《一百零八轉經筒》是從民族文化本體出發,探索多元傳播形式,展現蒙古族文化精髓,這是一種時代的思想,也是民族文化的發展要求,而這首作品以及研討會將會是蒙古族現代音樂發展的里程碑。
參考文獻
[1]博特樂圖.蒙古族傳統音樂概論[M].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15.
[2]李吉提.中國音樂結構[D].北京:中央音樂學院,2004.
[3]安東尼·西格爾[美].蘇亞人為什么歌唱[M].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2.
[4]周海宏.音樂與其表現的世界[M].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04.
[5]尤瓦爾·赫拉利[以色列].人類簡史[M].北京:出版集團·北京,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