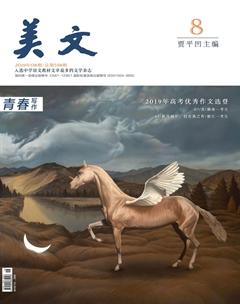《史記》獨韻亙古不絕
靳超

《史記》作為中國古代二十四部正史中獨具魅力的史書,曾被魯迅先生評價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先生之所謂“絕唱”即為中國古典詩文的無上高度、至美境界;而其所謂“無韻”便是司馬遷以“敘”和“筆”的“非文”方式描繪出了一部宏大而絢麗的文學(xué)世界。故而,《史記》既有其他二十三部正史歷史性的本質(zhì)特征,又有其他二十三史沒有的文學(xué)境界,而這種雙重性質(zhì)也是《史記》突顯于歷代史書的重要因素。
一、體例高妙——與《易》渾融
作為一部韻味獨具的史書,《史記》所開創(chuàng)的體例為歷代史書所延續(xù)。作為形式層面的體例,其實就是著作的編寫格式。而這種編著格式,并非以單向的時間、歸類為主要線索,而是融宇宙中盡含的“天、地、人、事、理、情”為一爐的渾融結(jié)構(gòu)。正如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指出的著述目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說,《史記》的體例是經(jīng)過嚴(yán)密思慮而構(gòu)筑的圓融世界,而這種圓融世界的核心思想即來源于《周易》中“殊途同歸”的“歸一”精神。圍繞著歷代王朝盛衰規(guī)律的“歸一”核心,《史記》發(fā)散出12條主射線,即“十二本紀(jì)”,他們記載的是黃帝以來歷代王朝興衰的歷史,以及各個帝王的事跡和社會的重大變化;存在于每條主線中的關(guān)鍵節(jié)點,以王侯外戚、個別具有突出貢獻(xiàn)的人為載體,構(gòu)成“三十世家”;而在這些基本框架之外,包含著許許多多、形形色色的事件、人物、道理、情感,這便是“七十列傳”。因此,七十篇列傳構(gòu)成了《史記》最具姿彩、最為鮮活的部分。此外的“十表”“八書”為更外圍層面的補充。
雖然是外在的形式,《史記》的體例中包含著司馬遷特有的思想傾向,而這種思想傾向從根源上來看,即源自于《周易》的“歸一”精神。《周易》代表了中國古典哲學(xué)的最高成就,其核心布構(gòu)實為“究天道、明人事”兩個方面。由乾卦、坤卦直至習(xí)坎卦、離卦組成的“上經(jīng)”為“究天道”;而從咸卦、恒卦直至既濟卦、未濟卦組成的“下經(jīng)”為“明人事”。由于《周易》在本質(zhì)上是一部哲學(xué)著作,因此其中所討論的多為以卦象、卦辭而推演的“天道”“人事”的思想與道理。《史記》作為一部紀(jì)傳體通史,其是以人物傳記為載體而表達(dá)其中所蘊含的“天、地、人、事、理、情”。例如《史記·貨殖列傳》,司馬遷將記載“地物”列在前面,將敘述民俗勞作放在后面,因為前者是古代帝王所“因天勢而利導(dǎo)”,后者是“因人事而制宜”。文章的先后順序正表示了作者對自然、人事之間的主從領(lǐng)屬關(guān)系。也就是說,《史記》“究天人之際”的核心宗旨是《周易》的“究天道”“明人事”思想的推演與發(fā)揮。由此可見,《史記》體例的高妙之處在于將《周易》無形地渾融、內(nèi)化于己身。
二、審美性與情感性——《史記》鮮明的文學(xué)韻味
從具體來看,《史記》的文學(xué)性表現(xiàn)在多種方面,譬如運用多種細(xì)節(jié)描寫、語言描寫等文學(xué)手段、塑造人物形象,又如多姿多彩的文章風(fēng)格、紛呈百態(tài)的謀篇布局等。但從文學(xué)的本質(zhì)上來講,《史記》的審美性與情感性則散發(fā)著其自身獨有的文學(xué)韻味。
自建安文學(xué)開始,文學(xué)自覺的標(biāo)志便是文人審美意識的覺醒。而此前的司馬遷已經(jīng)具有了審美自覺,并且這種自覺是一種“進(jìn)步的審美”。在《史記》列傳中,司馬遷尤為熱情地歌頌了那些推動社會改革、進(jìn)步的人物:他們既有為國家富強做出過卓越貢獻(xiàn)的政治家,如管仲、晏子、商鞅、子產(chǎn)等;又有在軍事上具有杰出建樹的軍事家,如吳起、孫武、孫臏、樂毅、司馬穰苴等。除此之外,《史記》審美的進(jìn)步性還體現(xiàn)在贊揚那些被置于上層社會之下的社會底層的小人物,弘揚他們的優(yōu)良品德。在當(dāng)時的古代社會中,愛好交游、行俠仗義的游俠是一直被上層社會所鄙視的人物。而在《史記》中,司馬遷舍棄了那些虛美、隱惡的士大夫,而專門為游俠作傳,熱情歌頌他們樂于助人、豪邁真誠的精神與人格。載入史書的意義尤為重大,因為它不僅意味著名留青史,更意味著一種精神的亙古長存。不得不說,這種進(jìn)步的審美眼光為《史記》帶來豐富且鮮活的文學(xué)精神。
除了審美性,《史記》的情感性貫穿于著作的方方面面。司馬遷將自己的價值觀與人生態(tài)度賦予其中,而每一篇都蘊含著司馬遷的用意。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上至本紀(jì)、下至列傳,都清楚地記敘著自身的寫作意圖。如“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司馬遷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為屈原立傳的史學(xué)家與文學(xué)家,他以深沉的情緒唱出了一曲悲涼的挽歌。在他看來,無論是屈原的離騷,還是賈誼的騷體賦,都是憂憤抒情的重要方式。這也與司馬遷“發(fā)奮著書”的寫作現(xiàn)實相共鳴。又如“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nèi)可以治身,外可以應(yīng)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司馬遷娓娓動聽地講述了一個悲壯的故事,顯示對吳起的崇敬之情,認(rèn)為作為軍事家“信廉仁勇,與道同符”是應(yīng)有的高貴品質(zhì)。無論是嫉惡如仇的悲憤,還是扼腕長嘆的惋惜,抑或無計憤慨的無奈,都隨著司馬遷的情緒灌注在《史記》的字里行間。
三、《史記》余響亙古不絕
如果說中國古代歷史是一條汪洋恣肆的萬古長河,那么《史記》便足以稱得上是掉落其中的一顆充滿神奇的隕石,激起了千層巨浪,萬股波瀾。《史記》不僅以它強大的包容氣質(zhì)囊括了大量珍貴的上古史料,更在文學(xué)上展示出了對后世巨大的影響力。上古傳說中的五帝時期是中華民族的鴻蒙之源,年代久遠(yuǎn)而史料匱乏。司馬遷憑借自己的游歷之體驗,搜集、整理了大量的僅存文獻(xiàn)記載與民間傳說,描繪出了自黃帝伊始的一個具有血緣繼承關(guān)系的帝統(tǒng)譜系。這種觀念對中華民族的凝聚具有深遠(yuǎn)的意義——直到現(xiàn)在,人們依舊以炎黃子孫而自居,依然以作為炎黃子孫而驕傲。可以說,《史記》的歷史余音,如同一首浩氣長歌,綿遠(yuǎn)悠長,亙古不絕。
作為《史記》的另一個鏡面,其文學(xué)精神在歷代的接受中更突顯了精髓和特征。從審美的角度來看,《史記》的散文中散發(fā)著一股剛健而不瘦硬,溫情而不柔靡的獨有韻味。這種散文風(fēng)格也為歷代古文家所標(biāo)榜。唐代中期,以韓愈、柳宗元為主導(dǎo)進(jìn)行了一次反對駢儷文風(fēng)的“古文運動”,他們明確提出“志在古道”的理論主張,并提倡以班、馬之散文為審美高度,去文之浮靡空洞而返歸質(zhì)實真切,以“寧為流俗所非,也絕不改弦易轍”的膽力和氣魄創(chuàng)作了大量飽含政治激情、具有針對性和感召力的古文杰作。明代中期前后七子以“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為口號掀起了一場巨大的文章改革浪潮,其所謂“必”秦漢之文便主要意指班固、司馬遷的散文風(fēng)格。除了唐代的韓、柳,宋代的歐陽修、蘇軾,明代的前后七子,清代的桐城派在文章觀念上也是不遺余力地以《史記》為審美號召。
從題材來看,由于具有廣泛的史料包容性,《史記》成為元明清戲曲、小說的一個重要的題材來源。例如《史記》中經(jīng)典的《澠池會》《霸王別姬》《文君當(dāng)廬》等事件在歷經(jīng)歷史的洗禮后,不斷以各種風(fēng)貌重現(xiàn)在各類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包括戲曲、小說。在歷代傳唱的過程中,故事情節(jié)逐漸被加工、潤造,形成了現(xiàn)如今耳熟能詳?shù)慕?jīng)典故事,而如若追本溯源,這些經(jīng)典故事的題材來源多為《史記》中的史料記載。據(jù)記載,明代著名傳奇集《六十種曲》中,便有十余種戲曲的題材源自于《史記》。
瑰麗不足以道盡,言語不足以盡情。《史記》在歷史的星空中閃耀著獨有魅力,亦吟唱著亙古不絕的余響之聲。作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寶庫,《史記》的光芒理應(yīng)在當(dāng)代為更多人所發(fā)掘,更理應(yīng)延續(xù)著它本身獨有的魅力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