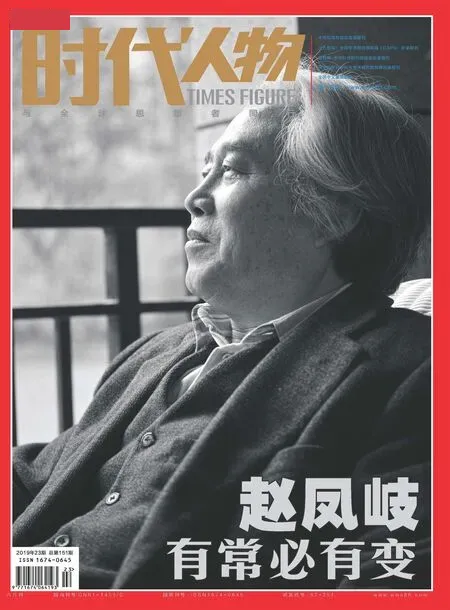從《論法律》一文談對法官職業(yè)修養(yǎng)的認(rèn)識
□文|周飛宇
培根的《論法律》一文論證了司法與訴訟、律師、警吏以及君主和國家之間的關(guān)系,幾乎論證的每一部分都提出了對法官職業(yè)的要求,這種要求既包括對法官職業(yè)道德的要求,也包括對法官職業(yè)行為的要求。培根提出的要求正是對法官這類特殊職業(yè)修養(yǎng)的要求,對我們現(xiàn)階段加強(qiáng)司法職業(yè)倫理建設(shè)很有啟發(fā)。司法改革的順利推進(jìn),也正需要作為法律實(shí)施者的法官的努力。因而,有必要探討法官職業(yè)修養(yǎng)的內(nèi)容,從法律思維、法官能力、法官道德、法官責(zé)任四個方面出發(fā)探索法官職業(yè)修養(yǎng)的建設(shè)途徑。
法官職業(yè)修養(yǎng)的內(nèi)涵
職業(yè)修養(yǎng),根據(jù)中國知網(wǎng)的詞條解釋,即指人們培養(yǎng)自己的職業(yè)才干和在所從事的職業(yè)中取得成就的能力和水平,主要包括掌握適合時代需要的良好的職業(yè)技能、職業(yè)才干、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fēng)。如果再對職業(yè)修養(yǎng)的內(nèi)容進(jìn)一步劃分,就是指兩部分內(nèi)容:職業(yè)能力和職業(yè)道德。
對于任何一種團(tuán)體來說,為了實(shí)現(xiàn)使這個團(tuán)體都能夠有效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的目的,都需要一種具體化的規(guī)范來約束全體成員。同樣,法官也不例外,法官是從事需要特殊專業(yè)技能的特殊工作的一類特殊群體,他們掌握著司法審判的權(quán)力,做出的每一份判決都影響著相關(guān)當(dāng)事人的切身利益,也承載著人民對于公平公正價值追求的寄托。因而,對于這一類特殊群體,需要在總結(jié)職業(yè)特點(diǎn)和功能的基礎(chǔ)上,用特殊的規(guī)范來樹立和約束法官的職業(yè)修養(yǎng),正如同《論法律》一文開頭開門見山的一句話,“法官應(yīng)當(dāng)具有很高的修養(yǎng)”。
法官職業(yè)修養(yǎng)的要求
公正是法官必備之品質(zhì),也是法官職業(yè)修養(yǎng)的核心。在此,不免要提到文中被廣為引用的一句話,“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因?yàn)榉缸镫m是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培根用這個深刻形象的比喻說明了法官違背公正原則將帶來的嚴(yán)重后果,會使民眾喪失對法的尊重,破環(huán)司法的權(quán)威性。
審判技能是法官入職的基本要求,法官的專業(yè)能力是法官職業(yè)化的重要內(nèi)容。培根在《論法律》一文中,還有一句話非常有名,那就是“知識就是力量”,我們知道法律體現(xiàn)著正義,但也要人能正確地運(yùn)用它。法官作為法律的適用者,正確地解釋和實(shí)施法律是他們的天職,他們也就必須要具備解釋和實(shí)施法律的能力,能夠在分析案件后準(zhǔn)確地適用法律、做出判決。當(dāng)然,實(shí)施法律不是指機(jī)械式地實(shí)施,而是要將法律應(yīng)用到具體案件中去,充分說理,使產(chǎn)生糾紛的雙方能夠信服。
具有司法為民的情懷,“使人民幸福就是最高的法律”。這句話與現(xiàn)階段我國弘揚(yáng)的一句話出發(fā)點(diǎn)相一致,“讓人民群眾從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法官在庭審中與當(dāng)事人保持距離,并不意味著法官需要對當(dāng)事人冷漠。司法貼近群眾是我國司法制度的一大優(yōu)勢所在,法官不是高高在上的職業(yè),他們也是有感情的,要維護(hù)善良的每一位公民的權(quán)益。
自身廉潔的日常作風(fēng),如前文所言,法官是公平正義的守門人,承載著社會民眾對于公平正義的寄托,我們希望看到的情景是,當(dāng)人民見到法官時,都會發(fā)自內(nèi)心地肅然起敬。因而,法官除工作任務(wù)外,不應(yīng)出現(xiàn)在紅紅綠綠的娛樂場合,不應(yīng)儀態(tài)不整、無視紀(jì)律,不應(yīng)隨意發(fā)表對某一案件的看法,更不應(yīng)當(dāng)與當(dāng)事人或者律師稱兄道弟,以一身正氣捍衛(wèi)頭頂?shù)膰铡?/p>
法官職業(yè)修養(yǎng)的培育
“之所以人們看到公正逐漸失去信譽(yù),更多地不是由于公正的脆弱性,而是由于以主持公正為職業(yè)的那些人中的某些人的行為”。以司法腐敗為例,政法隊(duì)伍中上到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下到基層法院普通干警,無視法律紀(jì)律,知法犯法、貪污受賄、徇私枉法,致使金錢案、權(quán)力案、人情案頻發(fā),民眾對司法判決公正的信心嚴(yán)重缺失,足以說明我國法官職業(yè)修養(yǎng)需要建構(gòu)和鞏固。
規(guī)范法官的職業(yè)行為。法律即使制定得再完美無瑕,但最終還是要靠法官做出具體的判定,法官的職業(yè)行為便顯得非常重要,即法官主體行為的合理性。《論法律》中提到了法官在審判中應(yīng)當(dāng)做的四件事:(1)調(diào)查證據(jù);(2)主持庭審時的發(fā)言,制止與審判無關(guān)的廢話;(3)審核通過法庭發(fā)言所陳示的證據(jù);(4)根據(jù)法律宣示審判的標(biāo)準(zhǔn)。
培根希望法官除四件事之外,不要再去做其他額外的工作。這對我們很有啟發(fā),從“應(yīng)為”的角度出發(fā)列舉法官的行為準(zhǔn)則。當(dāng)然,我國《法官法》已對法官履職的義務(wù)做了規(guī)定,是原則性的要求,內(nèi)容相對比較寬泛。我想,一部分法官走上違法犯罪道路不是由于他們不懂法,法官行為標(biāo)準(zhǔn)的模糊性使他們心理放松逐漸突破紅線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培養(yǎng)法官的專業(yè)能力。英國大法官愛德華曾言:法律是一門藝術(shù),它需要長期的學(xué)習(xí)和實(shí)踐才能掌握,在未達(dá)到這一水平之前,任何人都不能從事案件的審判。法官能力的培養(yǎng)是一個過程,需要在學(xué)習(xí)和庭審實(shí)踐中不斷得以鍛煉成長,我們在藝術(shù)作品中看到的優(yōu)秀法官往往是滿頭銀發(fā)、面容慈善的樣子,當(dāng)然并不是說法官都是靠一點(diǎn)點(diǎn)熬年齡熬出來的,是為了說明豐富的審判經(jīng)驗(yàn)對法官的修養(yǎng)有很大的作用。
培養(yǎng)也需要運(yùn)用激勵的手段,提升法官的地位,保障法官的經(jīng)濟(jì)收入,使法官對崗位充滿預(yù)期,增強(qiáng)職業(yè)的穩(wěn)定性。記得看過一篇新聞報道,某縣城為創(chuàng)建文明城市,要求法官去街道清理衛(wèi)生,進(jìn)行義務(wù)勞動,使人大跌眼鏡。如此擴(kuò)充法官的業(yè)務(wù)范圍,又怎能使法官們有職業(yè)尊嚴(yán)感呢?也常見法官跳槽出去當(dāng)律師,這與外國優(yōu)秀的法律人才都盼望著當(dāng)法官的現(xiàn)象相反,其中的原因需要我們?nèi)ニ伎肌M瑫r建議將法官的招錄工作由法院單獨(dú)負(fù)責(zé),現(xiàn)在我國的法官還是歸于公務(wù)員,屬于人事部門管理。法官既然是一門特殊職業(yè),在入職前就需要體現(xiàn)出特殊的要求,不然由行政人事部門掌握錄用權(quán),會產(chǎn)生法院受制的感覺。
完善法官的問責(zé)制度。任何權(quán)力的背后都有責(zé)任對其約束,不然權(quán)力就會太任性,當(dāng)法官出現(xiàn)違反職業(yè)規(guī)范的行為時對其問責(zé)是權(quán)責(zé)統(tǒng)一原則在司法權(quán)運(yùn)行領(lǐng)域的要求,也是防范錯案出現(xiàn)的一種手段。這些年來,一些冤假錯案的出現(xiàn),破壞了民眾對司法公信力的感情,世間無數(shù)的苦難之中,最大的苦難莫過于含冤受罪。我國古代自西周時便有“五過”之規(guī)定,若法官不依法辦案、徇私舞弊,則要被處以同法官審判之罪相同的刑罰,國外也有法官懲戒和彈劾制度,盡管制度規(guī)定不同,但目的都是一致的。
我國的司法改革也關(guān)注到這一點(diǎn),其司法責(zé)任制的出臺正是應(yīng)對上述的需要。問責(zé)制度應(yīng)當(dāng)把法官行為作為判斷標(biāo)準(zhǔn),堅(jiān)持主觀過錯與客觀行為相統(tǒng)一的原則,使責(zé)任追究與責(zé)任豁免結(jié)合起來。法官也不必一提到司法責(zé)任就過于緊張,因?yàn)榉ü儇?zé)任追究的條件和程序都必須是法律明文規(guī)定的,問責(zé)并不意味著不需要保障法官的權(quán)益,相反,也許正因?yàn)閱栘?zé)的法定性,才會使法官不會被任意處理。
培根的《論法律》一文盡管只有一千六百多字,但其中的思想很深刻,語言的質(zhì)樸使理解上也更為容易。法官是司法殿堂的守護(hù)者,他們的工作是人們尋求救濟(jì)的最后一扇門,對他們的職業(yè)修養(yǎng)要求也是人們對于法治的期盼,當(dāng)法官得到社會公眾普遍的尊重時,法治乾坤的那一天才會真正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