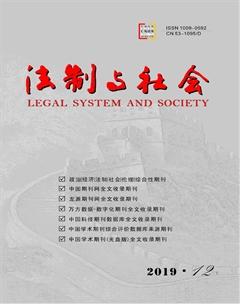《監察法》基本原則研究
金雪花
基金項目:2019年度江蘇省社科應用研究精品工程課題《紀檢監察體制改革背景下黨紀黨規與法律法規的關系問題研究》前期成果,項目號19SYC--193。
中圖分類號:D922.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12.246
2018年兩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以下簡稱《監察法》)在第一章總則部分,明確規定了基本原則,包括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原則,維護憲法和法律尊嚴原則,獨立行使監察權原則,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原則、協助原則、以事實為根據? 以法律為準繩原則、平等原則、保障權益原則、權責對等原則、監督與教育相結合原則、寬嚴相濟原則等,這些原則是協調的、統一的、互相聯系的。
所謂法律原則,指為法律規則提供某種基礎或本源的綜合性的、指導性的原理或價值準則的一種法律規范。 “法律原則是整個法律體系的原點,就是一種根本規范或基礎規范,其在一國法律體系或法律部門中居于基礎性地位,體現了法律的總體精神和根本價值,是具體法律規則的出處和源頭。”
法律原則的作用,在民法領域,在沒有法律條文規則依據的情形下,法官可以依據原則裁量,即“民法基本原則具有擴張機能和拾遺補缺的作用”;而在“法治國家的刑事法,實行規則中心主義” ,即刑事法律原則,不可以成為法官的自由裁量依據,法官只能依據刑法的罪狀條文定罪處罰。
因此,監察法律原則是整個監察法律體系的原點,在監察法中居于基礎地位,體現了監察法律體系的總體精神和根本價值,是具體監察法律制度的源頭,具體監察法律制度不得違背、并不得與監察法律原則相沖突。而監察法律原則是否可以作為監察官調查案件的直接依據,應分別而論:在遇到沒有具體法律規則時,向法律原則尋求依據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如果涉及對監察對象職務犯罪行為及犯罪證據進行調查認定,則不得以原則為依據,因為我國刑法明文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即只有依據具體刑事規則才可以。
一、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原則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無產階級自己的政黨組織——共產黨,是實現社會主義的政治保證。世界社會主義演進歷史也證明,社會主義事業需要共產黨提供政治、組織和思想保證。 新中國70年的發展史也證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2018年憲法修正案第一條明文規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因此,以法律原則明確黨對監察工作的領導,既落實了黨的執政意志,也體現了憲法的要求。
2016年11月7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開展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方案》,部署在3省市進行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開啟了我國監察體制改革的進程。在此之前,我國對職務違紀、違法犯罪監督體制是一個多元格局:對黨員領導干部的違反黨紀行為,由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監督;對政府及其職能部門公務員的違紀、違法行為由行政監察機關監督;對公職人員的職務犯罪,由檢察院的反貪污賄賂局、反瀆職侵權局負責偵查。舊有的監督格局,缺陷是顯而易見的,分別為:監督力量分散,導致監督無力;監督權力分配在多個機關,容易出現監督的真空地帶;黨紀和違法犯罪的處理程序出現沖突,導致帶著“黨籍蹲監獄” 的怪現象等。從嚴治黨的成績 也證明,改革前的監督體制無法發揮有效性。因此,監察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特色,就是整合分散的監督力量,將強大的監督權力賦予一個國家機關——監察委員會行使,從而對職務行為增強威懾力度、提高打擊力度,以求達到較好的治理效果。在改革前的監督體制下,如果說黨對紀律檢查委員會的領導是直接的、近距離的;那么黨對隸屬于行政機關的監察機關、和對隸屬于司法體制的反貪污賄賂局、反瀆職侵權局的領導則是間接的、遠距離的,因為黨的領導中間隔著它們的直接上級領導機關。而改革后黨對紀律檢查委員會、監察委員會的領導,是直接領導,沒有中間領導機關相隔。其監督力度無疑大大增強。
需要注意的是,黨對監察機關的領導,是政治領導、思想領導、組織領導,應遵循不越位不缺位的要求,因為依據法律行使監察權,具有嚴格的法定程序要求,在調查職務違法犯罪、查證取證過程中,須遵循嚴格的制度規定,這些法律明文授權的監察權力,都應當由監察委員會獨立行使,一旦進入法定程序,監察權行使不受任何機關和個人的干涉。
二、維護憲法和法律尊嚴原則
《監察法》是現行法律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在這個體系中,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此監察體制改革這一重大的組織創新和制度創新,必須有憲法依據。2018年兩會伊始,就頒布了《憲法修正案》,共21條,其中11條涉及監察法律制度,從而為我國的監察體制改革提供了憲法正當性依據。同時也意味著,監察權的行使,應當尊重憲法,須不得與憲法原則與規定相抵觸,如果有抵觸,則因違憲而無效。
根據《監察法》規定,監察委員會的監察職責包括監督、調查和處置三項職責。由于改革后紀律檢查委員會與監察委員會合署辦公,一套人馬,兩塊牌子,因此監察委員會行使權力的依據有黨內法規和法律兩套規則。在對監察對象違紀、輕微違法行為履行監察職責時,可以依據黨內法規和法律;但是如果對監察對象職務犯罪行為進行查處時,只能依據法律,這是現代法治文明的要求,也回應了法治反腐的精神,也是國際通行規則,同時也維護了法律的尊嚴。
我國《刑法》第三條明文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即“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作為具有執法職能機關的監察委員會,沒有任何理由不遵守刑法的規定,增加法律之間的沖突與張力;更何況“罪刑法定原則”體現了對公民權利的保護,與設立監察法律制度,啟動法治反腐進程的法治價值追求不謀而合。因此,遵守“罪刑法定原則”,是監察委員會不言自明的職責。《刑法》第五條規定了“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即“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根據此條規定,監察委員會在對職務犯罪行為查處的時候,應嚴格依據查處的證據進行處置,不得隨意增加或減輕對監察對象的擅自處置,更不得越俎代庖,將應當提交司法機關公訴審判的犯罪嫌疑人提前處置,雖然這種處置可能更多的是出于人道主義考慮,給予了輕罰,但違背了前述“罪刑法定原則”;如此做更可怕的后果是,這種不經法定程序擅自處置的行為同時也增加了“輕犯重罰”的風險,即增加了制造冤假錯案的風險,因此應加以杜絕,以維護法律的尊嚴。
三、獨立行使監察權原則
根據《監察法》第四條規定:監察委員會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監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這種獨立原則是相對獨立原則,前提是堅持黨的領導。在此前提下,這種獨立的內涵首先是監察機關獨立于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和社會團體;但是這種獨立又不是權力分立,根據《監察法》規定,與“審判機關、檢察機關、執法機關”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關系。其次,這種獨立是行使監察權的獨立,在黨領導前提下,只服從法律,不受任何機關和個人的干涉,調查取證、認定證據,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任何機關和個人,對于監察委員會依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證據等,不得隨意篡改,尊重并維護這種獨立性,確保監察權公正客觀行使。
為了更好維護這種獨立,應完善相關法律制度,盡快出臺《監察官法》,明確監察官的職責、權利義務、就職條件、任免、回避、福利待遇、職級晉升條件、培訓、獎勵、辭退等,一來保證監察隊伍的業務素質不下降,二來可以保護監察官行使權力的正確性和積極性。由于改革歷程時間較短,因此監察法律制度存在宏觀難以操作的特征,與其他機關和法律制度的銜接,雖然《監察法》第四十七條規定了移送起訴的銜接制度,但在取證、非法證據排除等方面還存在制度真空,因此,必須及時對《監察法》作出修訂,使監察委員會有法可依,保證監察權獨立行使的制度依據。
四、保障權益原則
設立監察法律制度,根本是為了保護人民的權益。但是,在行使監察權的過程中,應保護監察法律關系主體的權益,包括監察官的權益和監察對象的權益。對監察對象的權益保護,是法治國家應有的義務。
為此,監察法已經設立的出示證件、重要取證錄音錄像等程序制度、留置措施的通知程序和醫療等生活保障規定,都體現了對監察對象的權益保護。然而,對于監察對象救濟制度規定卻略顯薄弱。目前只有《監察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的復審復查制度;第六十條規定的申訴、復查制度,即針對《監察法》第六十條規定的違法采取查封、扣押、凍結、留置等監察權限時,監察對象及相關人有權申訴、申請復查。顯而易見,這種在原來的監察機關復審、申訴制度,如此設計,是存在一定的可商榷性的,首先違背了人之常情。試想,一個機關自己調查的案件,然后讓它承認自己錯誤并承擔責任,何等之難。其次違背了程序正當性原則。根據程序正當性原則,“自己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 ,因此,可以考慮設立特別的制度,完善監察對象的救濟制度,具體可以作如下設計:
1.將救濟職能授予檢察院,即監察對象覺得自己被錯誤監察,可以向檢察院求助。這么設計的理由是,檢察院具有法定的監督權和監督司法的經歷。但是缺陷在于,在檢察院與監察委員會的關系上,雙方是彼此平等的國家機關,因此監督權力不夠強大,加之曾經的檢察監督職能并沒有很好行使,因此,這一構想有效性可能不太理想。
2.將救濟職能授予全國人大憲法與法律委員會。因為該委員會具有違憲審查權,因此依據憲法對監察委員會的職權進行審查,理所當然,這么設計的優勢很明顯,首先節約成本,因為不用另設立機構也不用另聘用人員。其次具有可行性,阻力較小。需要說明的是,人大行使救濟權,缺乏強制執行權,因此其監督效果難以達到預期。
3.設計專門的監督機關,監督監察權行使,這一建構是設立專門機關,置于全國人大委員會之下,單獨聘用人員,然后制定配套的法律制度,內容主要包括機構的監督權、行使監督權的條件、行使監督權的程序、監督的對象和范圍、如何啟動國家賠償、如何敦促監察機關糾正錯誤等。如此設計,缺陷是運營成本較高。監察官的權益同樣需要保護。為了防范監察對象及相關人對監察官的財產及人身侵害,還應設立具體的制度,保護監察官。
五、監督與教育相結合制度
根據規定,監察委員會的第一個職責就是監督職責,即監督公職人員遵守職業道德的情形。對公職人員的職業道德進行法律層面的監督,在發達國家,早已有之,如美國最早為了解決“政黨分贓制”帶來的公務員道德問題,于1883年出臺了《彭德爾頓法》。而1978年美國制定《聯邦政府道德法》,則是因為“水門事件”的發生。依據該法,美國還于1978年設立了“聯邦政府道德署”,并于1989年將該機構“升格為具有獨立性的政府機構,其主任也由總統提名并經國會批準,直接向總統、國會、國務院負責。任期與總統任期不同步。” 因此該機構在履行監督職責時,具有高度獨立性;另外,行政系統每個機關都有一名道德官管理本單位道德事項。此后,美國1989年還頒布了《道德改革法》。可見,美國對公務員道德行為的監督有豐富的法律制度和完善的機構設置。此外,韓國1981年頒布了《韓國公職人員道德法》,日本《國家公務員倫理法》2000年實施。
我國《監察法》第十一條第一款將監督原則具體化,進一步明確了監察委員會的首要職責是監督。監督范圍從理論上說,除了公職人員的道德行為,還包括違法犯罪行為;如果說對道德行為監督為狹義監督職責,那么對其他職務行為監督則為廣義監督。顯然狹義監督的力度遠遠小于調查和處置職責。狹義監督職能的發揮,可以結合黨內法規和法律兩套規則行使,但對職務犯罪的監督則不可依據黨內法規。
需要說明的是,監察監督不同于檢察院的法律監督職能。首先從監督對象說,監察監督有權監督公務員和行使國家公權力的非公務員,不包括機關法人;而檢察監督主要監督公安司法機關及人員是否依法行使司法權。其次從目的上說,根據《監察法》第一條,監察監督的直接目的是預防腐敗,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而檢察監督的目的是保障司法權的合法正確行使。但兩種監督權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即約束公權力。
在行使監察監督權的過程中,對監察對象進行教育,及時糾正其思想上存在的錯誤認識,降低違法犯罪的幾率,是監察法律制度的又一功能。這種教育首先指對監察對象的直接教育,其次指對其他人員的間接教育,即通過對職務行為違法犯罪的處置及宣傳,對其他人員具有示范和警示作用。
六、監察公開原則
我國監察法沒有規定監察公開原則,但是理論和實際證明,確立公開原則具有重要意義。
公開原則在我國現代行政學和法學領域,已經廣泛設立。如我國有政府信息公開制度、行政處罰公開原則、行政許可公開原則等,還有黨務公開等都有明確規定。不僅如此,公開原則在國外同樣應用廣泛。如美國行政法領域,關于行政公開的立法有1966年制定的《情報自由法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保障公眾知情權;1976年制定的《陽光下的聯邦政府法(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 the Sunshine Act)》,要求行政機關會議公開;1972年制定的《聯邦咨詢委員會法 (The Federal Advisory Committee Act) 》,要求政府咨詢活動要公開;1974年制定的《聯邦隱私權法(The Federal Privacy Act) 》,保護公民的隱私權。 這些法律在美國形成一個完整的行政公開法律制度體系。此外, 法國于1976年制定了《行政行為說明理由和改善行政機關和公民關系法》, 1978 年公布了《行政文書公開法》, 1991年 日本政府發布《行政信息公開標準》, 1993年頒布《行政程序法》 《信息公開法案》 1999年通過。1950年奧地利制定了《行政程序法》, 1955 年意大利制定了《行政程序法草案》, 1976年德國制定了《行政程序法》, 1977 年愛爾蘭通過了《信息自由法》,? 1980年荷蘭開始施行《政府信息條例》, 1983年芬蘭通過了《官方文件公開條例》等。
中外立法實踐表明,公開制度已經成為法學領域的常態原則與制度,之所以如此,首先在于它蘊涵的法律價值,所謂法律價值,指“以法與人的關系為基礎的,法對于人所具有的意義,是法對于人的需要的滿足,是人關于法的絕對超越指向。” ,公開的法律價值在于它能促進公正,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和參與度。“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通過公開監察調查等監察過程,讓利害關系人參與或及時知悉監察權的運行情景,既可以防止違法濫用監察權,約束監督監察權,又維護和尊重了當事人和利害關系人及公眾的知情權;其次鑒于我國監察體制改革實踐,監察執法工作人員60萬左右,監察對象為全國9000萬黨員,涉及人數眾多,且影響重大,因此公開可以更好保障監察主體的權益,減少冤假錯案發生的幾率;最后,公開可以更好樹立國家監察權威。因為只有一個透明、公正、體現法治文明與進步的制度才會得到公眾的尊重和自覺遵守。
我國《監察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監察機關應當依法公開監察工作信息,接受民主監督、社會監督、輿論監督。”但是沒有具體規定哪些屬于可以公開的信息,哪些屬于不可公開的信息。從理論上說,在調查過程中涉及的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應屬于不可公開的范圍;而公開的范圍因內容不同應具有相應的公開范圍,如對于調查過程中如何取證,可以向舉報人公開,但不可對監察對象公開,防止翻供、串供;而查封、扣押等涉及財產的監察權的行使,可以對財產所有人及利害關系人公開;一些影響重大的案件,其監察進程則應當在行政管轄區域內乃至全國范圍內公開。
注釋:
[德]阿列克西著,法律論證理論[M].舒國瀅,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頁.
劉風景.法律原則的結構與功能———基于窗戶隱喻的闡釋[J].江漢論壇,2015(4),第114-121頁.
甄占民.黨的領導制度是我國的根本制度[EB/OL].中國社會科學網,http://www.cssn.cn/zk/zk_zz/201911/t20191121_5046559_1.shtml,2019年11月25號訪問。
深化監察體制改革? 推進試點工作之二:根本目的在加強黨的領導[EB/OL].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網,http://www.ccdi.gov.cn/special/xsjw/series27/201801/t20180102_160 889.html,2019年11月25日訪問.
形成反腐敗斗爭壓倒性態勢——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成就綜述[EB/OL].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fanfu.people.com.cn/n1/2017/0817/c64371-29476247.html,2019年11月25日訪問.
王名揚.英國行政法[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頁.
左秋明.20世紀美國公務員道德立法研究:經驗與啟示[J].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16(6),第104+114+128頁.
石富覃.從立法看美國的行政公開制度及其對我國的啟示[J].蘭州學刊,2006年(10),第117-120頁.
郎佩娟.西方國家公開行政立法研究[J].行政法學研究,2001(2),第81-89頁.
卓澤淵.法的價值總論[M].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