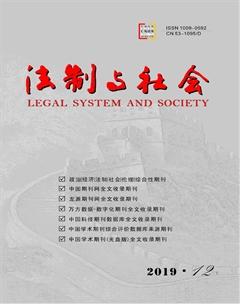淺析法醫鑒定在醫療糾紛中的應用問題
龔煒琪
中圖分類號:D91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12.342
與死亡有關的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件,確定死亡原因、明確損害后果為醫療損害案件的核心及基礎,在此基礎之上才能進行醫療過錯行為、因果關系及參與度的分析。[1]因此,本文將探討法醫鑒定在醫療損害糾紛中的應用現狀,具體分析現行制度下其適用存在的相關問題,并針對如何防范相關風險,得出一份公正、客觀的鑒定結果而提供具體對策選擇。
一、法醫鑒定在醫療糾紛中的適用現狀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公民法律維權意識的提高,醫患關系反而日趨緊張。早在2007年,中華醫院管理學會對全國326所醫院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被調查醫院醫療糾紛發生率竟高達98.4%。而當前,有關因醫療參與引發死亡而產生醫患糾紛而尋求法醫鑒定的事件逐年上升。
一般而言,當醫療糾紛中出現患者死亡的情形,醫院和患者家屬一般有以下三種處理辦法:(1)自行協商。根據我國醫療糾紛賠償的相關規定,當醫療糾紛賠付額度在一萬元以下的,醫院可以和患者家屬私下協商賠償事宜;(2)采取醫療事故的技術鑒定。當醫患雙方對于是否存在醫療過錯以及對患者死因存在分歧時,可以通過申請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將此鑒定結果作為證據,向法院提起訴訟;(3)直接起訴。直接就本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件向法院提起訴訟,由法院提請醫療過錯司法鑒定,再根據法醫鑒定結果進行裁決亦或是組織當事人雙方進行調解。但無論是何種原因,一旦出現患者死亡的情形,首先需查明患者死因,只有經過法醫學死因鑒定明確患者的死因,才能明確各方主體責任,以更合理科學、公平公正的處理醫療糾紛。
筆者通過Alpha案例庫查閱可知,醫療損害糾紛的相關案例數量自2012年開始呈現爆炸式增長態勢,2018年已一躍高達23098件,比2017年的22758件略有上升。其中,案由為醫療過錯責任糾紛12766件。在檢索的法律文書中,判決書結案的共有11326件,裁定書結案的共有6763件,調解結案的數量為3833件,較2017年的4055件有一定的下跌趨勢。由此可見,在醫療損害糾紛中,當事人更傾向于通過訴訟的方式解決爭議,整體而言,和解并不是滿足其利益需要的最優選擇。
二、法醫鑒定在醫療糾紛適用中存在的問題分析
雖然隨著近年來醫療改革的深入發展及人們維權意識的提高,法醫鑒定在醫療糾紛中適用的情形越來越多,但是在實務中法醫鑒定仍遭受許多阻礙,難以較好適用于醫療糾紛事件中:
(一)患者家屬委托法醫鑒定意愿較低
首先,受中國傳統儒家觀念的影響,國人對于尸體處理仍較為保守,認為死留全尸才是對死者最大的尊重,而一旦進行法醫鑒定,必然要進行尸體解剖,這無疑是很多人所不能接受的;其次,法醫鑒定費用相對高昂。當前,各地法醫鑒定費用少則幾千,多則上萬元,且患者死亡原因越是復雜、難以鑒定,相關的鑒定費用則越高。再者,即使家屬支付了法醫鑒定費用,由于鑒定技術、鑒定人員知識水平等因素限制,有時需要進行多次鑒定,高昂的法醫鑒定費用也并不是每個家庭都能支付的,與此同時,心理壓力之大更是很多家屬難以承受的。
(二)醫院對于醫療糾紛中的法醫鑒定接受度低
據資料顯示,近50年來,盡管各種臨床檢驗方法及診斷手段日新月異,但國內資料表明,臨床生前診斷與尸檢診斷不一致率仍在20%以上,說明臨床診斷技術的發展和進步并沒有明顯改善診斷正確率。[2]對于直接涉及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件的醫生而言,一旦提起法醫鑒定,該鑒定結論很大程度上確認患者死亡原因是否由于醫生誤診造成的,一旦最終構成醫療事故,醫生將會承擔不可預估的風險。而對于院方來說,醫院一旦確定存在醫療過錯,甚至造成醫療事故,不僅要對患者家屬承擔直接賠償責任,還要接受衛生行政部門的嚴厲處罰,且因此降低醫院社會評價、影響醫院的正常經營所帶來的不利后果不是院方所愿意面對的。
(三)鑒定機構及鑒定人員水平不一,鑒定結果難保準確性
隨著醫療技術的不斷提高,涉及患者死亡的醫療損害糾紛案件所爭議的事實所需鑒定人醫學知識更加高度專業化,對鑒定意見的真實性、客觀性、關聯性也有著更嚴格標準。雖然我國有關機構已制定鑒定機構的準入標準,并對鑒定人員的資質有明確要求。但在法醫鑒定實務中,鑒定機構和鑒定人員進出機制體現為“寬進寬出”,即準入門檻較低,懲戒、退出機制并未實際嚴格落實與執行,由此引發一系列問題。而鑒定機構和鑒定人員素質參次不齊,亂象層出,最直接的影響就是鑒定結果難保準確性。不少鑒定結論因忽略或者未能察覺有關患者死亡的真正原因等客觀因素而出現鑒定結果瑕疵或者鑒定結果明顯與客觀事實不符而使得鑒定意見難以使人信服。如此前山東一患兒因接種水痘疫苗而死亡,家屬花費一萬元給有資質的鑒定機構進行死因鑒定,歷經53天得到的鑒定結果卻連患兒接種是右臂卻都寫錯為左臂,顯然,這有可能不僅未緩和醫患矛盾,還極大損害鑒定意見的社會信任度。
(四)重復鑒定情形多,司法采信度低
法醫鑒定結果是司法鑒定意見中的一種,是法定的八大種類證據之一,鑒定程序及結果的科學性、客觀性決定了其是否被法院最終采納。我國法律規定,法醫鑒定人員及機構不得與糾紛存在利害關系。但當前鑒定機構存在一定市場化的態勢,即為獲得更多案源,做出的鑒定意見可能對委托鑒定人有一定的利益傾向,而喪失鑒定結果的公正性。與此同時,不同的鑒定機構,不同的鑒定人所做出的鑒定結果有可能存在極大分歧,即使是同一個鑒定機構,亦有可能出具兩份截然相反的鑒定結論,孰真孰假,難以辨別,使得重復鑒定成為醫患雙方常態。患者的死因是爭議之所在,而互相矛盾的鑒定意見彼此間并不具備明顯證據優勢,因此,在司法實踐中,法院難以憑借其中任何一份鑒定意見處理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件。這不僅增加訴訟成本,浪費司法資源,而且嚴重損害了法醫鑒定的可信度及法院判決的公信力。
三、法醫鑒定在醫療糾紛中的優化適用及出路探索
(一)加強尸體病理檢驗重要性的宣講
實踐中,醫患雙方積極主動申請死因鑒定的案例很少,但醫患雙方的矛盾并沒有因此解決。死者家屬認為醫院違反有關醫療操作規范,而導致患者死亡,而院方則認為是患者自身疾病原因致死。且隨著互聯網的普及,有醫療因素參與的死亡案件更是容易在網絡發酵,輿論一邊倒的情形常見,更是使得醫患關系更加緊繃。此時,死因鑒定則是解決兩者關系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故在當前,應當加強早期病理尸檢重要性的宣講,通過互聯網等新媒體等媒介,將法醫病理的基礎知識及重要性普及給人民大眾,這樣才能有力的保障各方合法的權益,促進醫療事業往更好的方向發展。
(二)統一涉及死亡的醫療損害司法鑒定的適用
由于在法律層面,我國只是籠統規定鑒定人只需滿足鑒定條件并具備相應的鑒定能力即可,并未對鑒定人的身份進行限制。因此,無論是醫學會里的行業專家,還是司法鑒定機構的醫療鑒定專家,只要符合相應條件都可以成為涉及死亡原因的醫療損害責任糾紛的鑒定人。但有醫療因素參與的死亡案件與一般司法鑒定案件不同,其后期產生醫療損害責任糾紛的風險更高。且患者的死因越是復雜,對于法醫鑒定人的技術水平要求更高。為此,需要破除醫療過錯司法鑒定與醫療事故技術鑒定的“雙規”并行制。通過建立一個統一具備具體法醫學科知識的醫療損害鑒定機構及人員名單庫,為涉及死亡的醫療糾紛案件鑒定的具體選擇適用提供參考。
(三)提高醫療糾紛法醫鑒定的專業性
法醫鑒定的結論是解決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件的核心問題。當前,我國司法鑒定機構的數量如雨后春筍般快速增加,鑒定機構的專業化水平參次不齊。與此同時,鑒定人員的資質審查并不規范,相關的職業能力有所欠缺,容易使鑒定結果失真。為此提高醫療糾紛法醫鑒定的專業性很有必要:首先需要對鑒定機構和鑒定人員進行資質審查和考核,審查結果不通過的鑒定機構及鑒定人視情節輕重采取懲戒、退出等處理辦法;其次加強對法醫鑒定人員全面系統的職業培訓,強化其業務實操的規范化與標準化程度,確保鑒定結果的準確性,以為醫療糾紛的進一步處理提供指導。
(四)明確重新鑒定的客觀標準,解決鑒定亂象問題
重新鑒定遍地開花的重要原因是重新鑒定程序的啟動的客觀標準不明確,為此重新鑒定的考慮因素應限為:原鑒定人的鑒定水平有限,未充分對患者死因進行鑒定;鑒定技術方法和檢驗設備使用不當;發現新的鑒定材料會導致鑒定結果與原鑒定意見不一致;鑒定人與醫院雙方與利害關系而未回避等可能會影響原鑒定結果準確性的。同時規范重新鑒定的申請次數。當醫患雙方對于法醫鑒定意見存疑時,可以向相關鑒定委員會提出申請,經過審查符合條件后,可自行委托或者法院指定相關的鑒定機構進行重新鑒定,對于重新鑒定依舊出現分歧的,由鑒定委員會指定法醫鑒定或者派員進行法醫鑒定,鑒定結果為最終適用標準。
(五)提高審理涉及死亡的醫療糾紛案件法院的專業化
首先,需要培養一支具備相關醫學知識的綜合型法官以審理相關醫療糾紛案件。當前,涉及有醫療因素參與的死亡案件量多,且由于醫療糾紛案件具有高度專業性和復雜性,法官若不具備相應的學科背景,則有可能出現原本因經法官審查才能采信的法醫鑒定意見,最后卻直接確定為案件的唯一證據而被適用于案件,則無疑不利于案件的公正審理;其次,完善醫療損害糾紛中法醫鑒定的審查和質證。先審查鑒定機構及鑒定人員的鑒定資格,隨后法院對于患者的死因鑒定進一步審查核實,對于不具備證明力,不符合證明標準的鑒定意見不作為案件審理的依據。同時對于鑒定材料的補交進行嚴格的審查,對于可能會影響原本鑒定結果準確性的補充證據,要求法醫重新鑒定。最后,細化鑒定人的法律地位、權利義務、質證程序以及不出庭作證的法律責任,以提高此類案件的審結效率。
參考文獻:
[1]王代鑫,朱英芝,周小偉,等.法醫病理學鑒定與醫療損害責任糾紛鑒定[J].中國司法鑒定,2018(5):38-44.
[2]馬佳,仁壽.中國醫院為何冷遇尸檢? [N].北京科技報,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