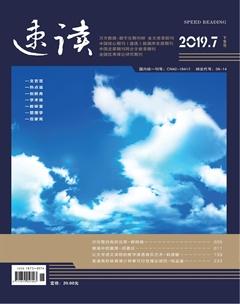戶外觀察中激發的幼兒自主學習
王琳超
親愛的80后伙伴們,還記得小時候在草叢里捉螞蚱的情景嗎?那光著腳丫專注在草叢里翻來尋去的時刻,想來就是童年最難忘的光景。如今我也從事著幼教工作,今年正好回歸小班隊伍。從開學以來孩子們的注意力和傾聽能力一直就是我最惆悵的問題。于是,我們不停的強調上課的坐姿,集體活動的紀律,對孩子們的要求越來越多,可孩子們依舊是容易走神,不專注。這讓我們真的不知如何是好,幾天的陰雨夾著我們的苦惱綿延不絕的下著。這一天,天空終于放晴,幼兒園的后花園里綻開了一朵朵恬靜的小白花,淘氣的小螞蚱從小草的一頭跳到另一頭,銀杏樹搖擺著黃燦燦的小扇子,遠遠望去,十分美麗。我腦海里突然閃過一個想法:趁著秋高氣爽,去戶外上課吧!說走就走,帶領著一群萌寶,敬園的后花園里各種尋寶。
妮艷:“老師老師,我們今天去哪里呢?”
我:“去找一找草叢里的寶貝。”
定可:“會有什么寶貝呢?”
我:“草叢里的寶貝可多啦!仔細看仔細找,你一定會發現。”
欣然:“哇!快看快看,白色的小花好泡亮~”
我:“真的很漂亮。”
銘玥:“有蝴蝶,噓~不要吵到它。”
之閑:“老師,這朵蘭花的顏色好美,像我媽媽的連衣裙一樣美。”
書然:“花里面有黃點點,我最喜歡黃色。”
子喬:“有蟲子,綠綠的。哈哈,它會跳。它是蝗蟲嗎?”
錦城:“不是不是,它和我們養的蝗蟲長得不一樣。”
海峰:“你看,它有三只腿。”
妮艷:“不對不對,我這還有三條腿呢。”
冰冰:“快躲開,有怪物,它有兩把大鏟子,快走,它的頭在看你。”
睿哲:“是只綠色的怪獸蟲。”
子喬:“它會攻擊嗎?”
海峰:“我們圍住它,它就被我們困住了。”
“哇,你們找到寶貝啦?”我靜悄悄的走進他們。
“老師快讓開,它會攻擊你的。”“老師它是什么蟲子呢?”孩子們七嘴八舌的說著,我拿出準備好的昆蟲觀察盒,小心翼翼的把它裝進盒子里。“給它起個名字吧!”我提議。“它的身體是綠色的,個子挺大,就叫大綠綠吧!”
問題來了,大綠綠到底是什么呢?我將這個問題拋向孩子。孩子們拿來我們之前找到的蝗蟲,大家圍坐著一起觀察。“它們一樣嗎?”我問,“不一樣的。”孩子們都觀察出來了,有的說:“它們一個大,一個小。”有的說:“它們的腿上都有尖尖的小刺。”“大綠綠有脖子,蝗蟲沒有脖子。”“大綠綠身上只有綠色,蝗蟲身上還有黃色呢。”孩子們的回答太精彩了。趁熱打鐵,我提出了第二個問題“大綠綠和和蝗蟲會是好朋友嗎?”“可能是吧。”“應該不是”孩子們的答案出現了分歧。“他們可以住在一起嗎?”一個孩子問著,所有孩子都覺得好奇。我將它們收養到一個盒子里面,讓孩子們有時間就去看看它們。
第二天一早,欣然急匆匆的過來拉我“不好了,王老師你快去看看,大綠綠把蝗蟲給咬死了。”借此機會,我給孩子們組織了一個科學活動《莊稼的小衛士——螳螂》。這一次的活動孩子們非常安靜,乖的讓我覺得驚訝。短短一天半的時間,他們專注的探索,為意見的不統一而拌嘴,為求證而協作。相比在教室里連五分鐘都專注不了的狀態,這一次的活動真讓我對他們刮目相看。
通過與大自然實物的接觸,孩子們的觀察力變得敏銳,平衡能力、靈巧度、身體協調性、交際能力和表達能力都有所提升,同時也觸發了孩子們主動學習的契機,與之前在教室里的狀態截然不同。這也引導著我反思,學齡前階段的孩子,其大腦以及身體的各個器官和組織的發育還不完善,決定了他們還不能像小學生那樣坐下來正規的學習。強制的要求他們達到我們理想的標準是否小學化了呢?如果非要像對待小學生一樣要求他們,這種違背規律的做法對孩子的危害可想而知。孩子在這種教育過程中,得不到快樂,而得到的常常是消極的情緒體驗,自然就會認為學習就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于是,對學習產生恐懼和厭惡的心理,結果使孩子還未正式開始學習的過程,就已產生了厭學的情緒,這是最糟糕的事。
教育學家蒙特梭利提到大自然對幼兒教育的重要性,她認為人,尤其在兒童時期就屬于自然界的一分子,他們必須在自然中取得身體與心靈成長所需的各種原動力。我也由此思考著:幼兒的成長是否更應該順應自然,回歸自然,讓每一個孩子投入大自然的懷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