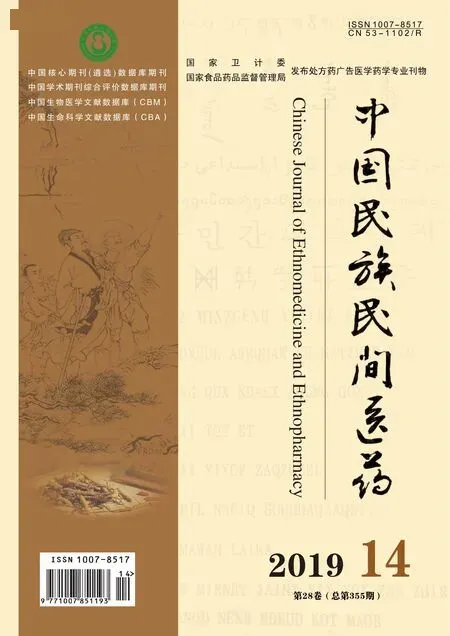基于《王仲奇醫案》探析王仲奇辨治泄瀉的處方用藥規律
1.安徽中醫藥大學,安徽 合肥 230038;2.廣州中醫藥大學,廣東 廣州 510405
“新安王氏醫學”作為新安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學淵源有自來,學風嚴謹,宗經典而取眾家之長,廣采博納而自成一家。王仲奇(1881-1945年),諱金杰,晚年自號懶翁老人,安徽歙縣人,出生于中醫世家,為新安王氏內科第四代傳人,15歲時隨父親學醫,22歲掛牌應診,以治療濕溫病和鼓脹等大疾而名噪鄉里。《王仲奇醫案》共40門,輯709案,是其子樾亭,女蕙娛、燕娛和侄任之隨伺先生學醫時所抄門診處方以及部分弟子所提供的處方手跡整理而來,反映了王氏豐富的臨床經驗和學術思想[1]。陰陽五行,參伍錯綜,迭相為用;氣有偏勝,故理有扶抑;其間輕重疾徐,酌其盈,濟其虛,補其偏,救其弊,審察乎毫厘之際,批導乎隙之中,這是王仲奇學術思想的基本觀點[2]。文章基于office 2010與SPSS 22.0進行藥物及其性味歸經頻數統計、聚類分析,對《王仲奇醫案·泄瀉》所載78則處方治療泄瀉的用藥特點和臨床思路進行分析。
1 資料和方法
1.1 資料來源 選用《新安醫籍叢刊》醫案醫話類(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95年)所載《王仲奇醫案·泄瀉》為研究資料,其中所錄醫案30例,處方78則,涉及中藥128味。
1.2 數據整理
1.2.1 數據錄入 將《王仲奇醫案》所載病案錄入 Microsoft access 2010,建立王仲奇醫案數據庫。所選醫案療效確切,記述詳實,并單純采用中醫藥治療;所選醫案要求完整、可靠,如醫案不僅要有臨床癥狀,還要有診斷、分型和治法方藥。在《王仲奇醫案·泄瀉》中篩選有效方劑,整理錄入。
1.2.2 數據規范化 本研究主要目標是挖掘《王仲奇醫案·泄瀉》處方用藥信息,在分析前對藥物進行預處理。對中藥的統一規范和功用分類以15版《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3]和《中藥學》[4]為標準,對不同藥物名稱規定如下:①對處方中相關藥物別名和俗稱統一規范為標準名,如“雞肫皮”改為“雞內金”;②中藥經炮制后功效相似者仍用標準名,但因為炮制方法不同所致的生熟異治的,如“甘草”與“炙甘草”則不予同化;③有修飾詞的性味,去除修飾詞統計,如“微溫”直接去除“微”字,按“溫”統計。
1.2.3 數據篩選處理 對數據庫中的醫案進行篩選整理。所選醫案為王仲奇治療泄瀉的有效醫案,共78首方劑,排除對癥加減用藥;排單味藥組成方劑;排除無方無藥、組方不詳及重復出現者。將有效方劑通過 Microsoft access 2010處理數據,建立數據透視表,并與中藥藥典數據庫進行匹配。得到處方中所有用藥的完整信息,進行下一步處理。
1.3 數據挖掘 應用頻數分析和聚類分析將處方中的用藥進行深刻挖掘。頻數分析反映該藥在所有方劑中的使用頻繁程度[5]。而聚類分析則通過數據處理,尋找醫家最常用的藥對配伍,探究藥對配伍的特殊作用,相對于普通經驗探索則更具有科學性[6]。
1.3.1 頻數分析 利用上述數據透視表可得病案中所有藥物的用藥頻數,每一味藥的用藥頻數除以病案總數即為該藥的用藥頻率。
1.3.2 聚類分析 使用SPSS 22.0對使用頻數較高的藥物進行聚類分析。通過系統聚類分析法,把數據中一些相似程度較大的數據歸為一類,把一些相互疏遠的歸為不同的類,并進行賦值表格制作,從而尋找出《王仲奇醫案·泄瀉》的臨床組方用藥規律。
2 結果
2.1 藥物頻數分析 對《王仲奇醫案·泄瀉》中所用藥物進行統計分析,其中使用頻次≥12的高頻藥物共23味,前5位分別茯苓、白術、佩蘭、肉豆蔻、益智仁。見表1。

表1 處方核心藥物構成(頻次≥35次)
2.2 藥性、藥味及歸經頻數分析 《王仲奇醫案·泄瀉》中治療泄瀉所使用的藥物,藥味以甘、苦、辛為主,藥性以溫、寒、平居多;歸經以脾、胃、肝、肺經為主。見表2、表3。

表2 處方藥物藥性、藥味構成

表3 處方藥物歸經構成
2.3 藥物類別頻數分析 根據《中藥學》藥物分類方法,對《王仲奇醫案·泄瀉》中的藥物進行匯總歸類,最后共分為16個大類,其中以補虛藥、收澀藥、利水滲濕藥、化濕藥、理氣藥頻率最高。見表4。

表4 處方藥物類別構成
2.4 藥物聚類分析 對《王仲奇醫案·泄瀉》中78則治療泄瀉病案所用的頻次超過12次的23味中藥進行聚類分析,聚類情況見圖1,聚類結果見表5。當聚類達到九類時,聚類結果顯示良好。將《王仲奇醫案·泄瀉》中常用藥對列表,可以清晰的看出王氏的臨床治療特色。

圖1 聚類分析

序號成員數藥物組成主要功效C12枳殼,大腹皮行氣寬中,利水消食C23防風,禹余糧,罌粟殼祛風勝濕,澀腸止瀉C32白芍,益智仁暖腎止痛,澀腸止瀉C42神曲 ,大麥健脾和胃,消食利水C52石斛,化橘紅益胃消食,清熱燥濕C65枳殼,大腹皮,陳皮,白豆蔻,半夏健脾化濕,行氣寬中C72蒲公英,雞內金清熱健脾,利尿消積C83白術,肉豆蔻,茯苓益氣健脾,澀腸止瀉C91佩蘭化濕,健脾
3 討論
聚類分析指將物理或抽象對象的集合分組為由類似的對象組成的多個類的分析過程,旨在相似的基礎上收集數據來分類。應用聚類分析統計方法研究中醫證候、辨證分型及用藥特點時,能夠有效避免主觀不合理因素,在總結研究名老中醫臨床經驗和用藥思路上有可靠價值。
泄瀉是以排便次數增多,糞質稀溏或完谷不化,甚至瀉出如水樣為主的病證。其主要致病因素為濕,以脾虛濕盛,脾失健運為主要病機,治療當應以運脾祛濕為原則[7]。王仲奇治療泄瀉藥物多屬補虛藥、收澀藥、利水滲濕藥、化濕藥、理氣藥,其次為解表藥、消食藥、化痰藥、清熱藥等。而藥物使用頻率最高者為茯苓、白術、佩蘭、肉豆蔻、益智仁、神曲、白芍、防風、大麥、禹余糧、白豆蔻、陳皮、罌粟殼、枳殼、半夏、雞內金、砂仁、木瓜、大腹皮、荷葉、石斛、蒲公英、化橘紅等,以益氣健脾、溫腎理氣、淡滲祛濕、固澀止瀉為主要功效。其中使用利水滲濕之茯苓頻率最高,共74次。如《難經》所說“濕多成五泄”。《景岳全書》亦提到,“凡泄瀉之病,多由水谷不分,故以利水為上策。”由此可推,《王仲奇醫案·泄瀉》中所載泄瀉多以肝郁脾虛、脾胃虛弱及脾腎陽虛為主證。王仲奇治療所用藥物多為甘、苦、辛味,藥性多為寒溫并重,以溫為主;歸經以脾、胃、肝、肺經為主。王仲奇受葉天士影響,治瀉不忘脾胃之本[8]。正如《景岳全書》所言,“泄瀉之本,無不由脾胃”,泄瀉病因復雜,但其基本病機屬脾胃受損,濕困脾土,腸道功能失司[9]。
藥對既是方劑配伍的精華與核心所在,也是辨證施治針對性與治療性的明確體現,其配伍簡單,易于探討配伍的效應和規律[10]。根據系統聚類分析王仲奇用藥規律和治瀉方法,結果顯示,C3藥組為治療脾腎陽虛特色藥對。益智仁,味辛,性溫,入脾、腎經。《本草備要》中記益智仁有和中益氣,補腎虛滑瀝,散寒止痛,止吐止瀉之功[11]。白芍味苦、酸,性微寒,歸肝、脾經,《醫學啟源》中記,白芍“安脾經,治腹痛,收胃氣,止瀉利,和血,固腠理,瀉肝,補脾胃。”具有平肝止痛,養血調經,斂陰止汗的功效。二藥相配,溫脾暖腎之時兼以斂陰止瀉,用于治療腎虛泄瀉療效顯著。C6藥組枳殼、大腹皮、陳皮、白豆蔻、半夏共奏健脾化濕、行氣寬中之功效。陳皮、半夏合用有二陳湯之意,有燥濕化痰、理氣和中之功。范文萃應用二陳湯加減健脾燥濕,半夏辛溫性燥,善能燥濕且又降逆和胃止嘔,陳皮苦辛而溫,功能燥濕理氣健脾。兩藥相配,共奏燥濕健脾、和胃止嘔之功,治療脾虛濕困型腹瀉[12]。王奎平應用二陳湯配伍失笑散加減化痰祛瘀、健運脾胃,治療痰瘀內阻之泄瀉[13]。二陳湯配以行氣寬中、消食開胃之枳殼、大腹皮、白豆蔻,理氣和胃之效更著。C8藥組,白術與茯苓配伍,始見于張仲景《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二書[14]。白術,味苦甘性溫,為補脾之要藥。《本草匯言》中記“白術,乃扶植脾胃,散濕除痹,消食除痞之要藥也。脾虛不健,術能補之,胃虛不納,術能助之。”茯苓,味甘淡性平,為健脾滲濕之要藥。《本草求真》更提到“茯苓專入脾、胃,味甘入脾,味淡滲濕。……諸病皆從水濕所生,服此皆能有效。”白術配茯苓,白術守中,促進脾胃運化水濕;茯苓下行,使水濕從小便而去[15]。肉豆蔻溫中行氣、澀腸止瀉,與白術、茯苓同用,共奏益氣健脾,澀腸止瀉之功效。
通過對《王仲奇醫案·泄瀉》用藥的數據分析,可以看出王仲奇在臨床診療方面頗具特色,其認為泄瀉的病位在于脾胃,病邪以濕為要,并在調理脾胃的同時暢達肺氣,處方中肯、思路明確、用藥輕靈。王氏臨床善用藥物與常用配伍,是其臨床寶貴經驗的重要積累,有著極其顯著的療效,值得臨床借鑒和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