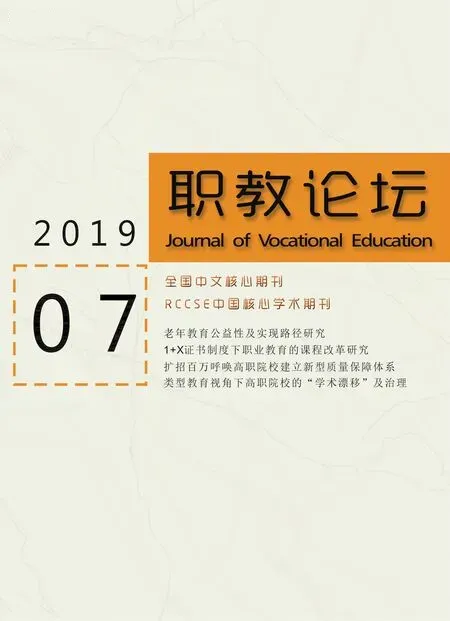百萬擴招任務的責任分解機制研究
□常 姍
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我國高等職業教育在院校規模和招生規模的量級層面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就。但是,自2014年始高職院校逐漸開始面臨生源危機,部分高職院校投檔率持續降低且錄取報到率持續低于70%[1],甚至呈現向外蔓延趨勢,如何解決生源危機成為高職院校求發展的關鍵問題。2019年新春伊始的全國“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在向全國人大代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穩定和擴大就業的重要政策取向“改革完善高職院校考試招生辦法,鼓勵更多應屆高中畢業生和退役軍人、下崗職工、農民工等報考,今年大規模擴招100萬人。”[2]“大規模擴招100 萬人” 不是小數字,與2018年高職院校實際招生規模相比增幅巨大。2018年全國高職院校招生368.83 萬人[3],100 萬比2018年招生量的1/4 還多,這對本來就存在生源危機的高職院校來說,百萬級別擴招是一個極大的現實挑戰。如何實現100 萬的擴招量,首要問題是斟酌百萬擴招的任務如何分配,以省域分配或是以人口規模分配,以行業分配或是以產業量級分配,以校級分配或是以年招生量分配等等,所以必須構建百萬擴招量的責任分解機制。
一、百萬擴招任務的責任分解困境
2019年中央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擴招100 萬人,但是百萬規模的擴招并非隨意分配,需要根據一定的影響要素綜合考慮擴招規模的分配比例。百萬量級的擴招需要百萬量級的產業需求、學生來源和辦學容量等為基礎性條件,但是面對2018年高職院校年招生量僅為368.83 萬人的體量,100 萬擴招規模量級實屬巨大。高職院校每年招生計劃量是根據市場需求、辦學能力和生源狀況等諸多要素指標提前測算而來,所以百萬擴招的任務分解應立足于不同區域的經濟社會整體格局,充分考慮不同區域產業布局、辦學資源、生源狀況等影響因素。
(一)不同區域之間產業發展及人才需求的差異
高職院校每年招生計劃數量的主要測算指標之一是區域或行業市場對相關人才的需求量,以及每個地區的產業布局差異。這兩個因素均會影響到該地區對技術人才的現實需求,即產業越發達,所需技術人才越多;產業層級越先進,所需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層級越高。高職院校是培養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的重要“孵化器”,畢業生多涌向相應產業的生產性或服務性崗位,且呈現出一定的行業粘聯性和區域內斂性。行業粘聯性和區域內斂性意味著不同區域的產業結構及人才需求決定相應區域內高職院校人才培養數量,間接影響到百萬擴招應分配的擴招份額。所以,可以抽象地使用不同省份的GDP 以及產業結構比重來分解百萬擴招的整體比例份額。
從表1中可以發現,從全國產業結構比例來看,百萬擴招的招生比例可參考產業結構比進行分配;第二產業在全國占比超過5%的省份包括廣東、江蘇、山東、浙江和河南五個省份,所以在第二產業技術人才培養中,百萬擴招份額可向這五個省份傾斜;第三產業在全國占比超過5%的包括廣東、江蘇、山東、浙江和北京五個省市,所以第三產業技術人才培養中,百萬擴招份額可向這五個省份傾斜。同時觀察全國及各省(市)三次產業結構比,第三產業占比超過50%的從高到低依次是北京、上海、天津、海南等十余個省份,在第三產業擴招份額中可以優先向這些省份傾斜;第二產業同理。

表1 全國各省份的GDP 以及產業結構比重表
(二)不同區域之間辦學資源及人才供給的差異
高職院校每年招生量的主要測算指標之二是區域內高職院校辦學資源對學生的承載量。區域內高職院校數量和辦學規模較多的地區,可招收的學生就多,對社會供給的人才就多。2019年5月,教育部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高職擴招專項工作實施方案》,明確高職院校擴招重點布局在優質高職院校[4]。所以,高職優質院校辦學規模較多的省份所容納的新生應該越多,擴招人數也越多,百萬擴招應分解的擴招比例份額就越多。
從表2全國各省份示范校、骨干校、優質校數量統計結果來看,國家示范校中數量相對較多的省份是江蘇、山東、浙江、四川及湖南;國家骨干校中數量相對較多的省份是廣東、山東、江蘇、浙江、四川、湖北、安徽;優質校建設立項相對較多的省份是四川、河北、江蘇、浙江、江西、重慶;三者合計相對較多的省份是江蘇、浙江、四川、河北、廣東、山東、江西、重慶等。從統計結果不難看出,示范校、骨干校及優質校建設排名靠前的省份皆是經濟發達省份和人口較多省份,也從側面印證了高等職業教育所能提供的“人才紅利”。
(三)不同區域之間生源現狀及擴招潛力的差異
高職院校每年招生量的主要測算指標之三是區域內生源現狀及潛在生源量。在百萬擴招之前,高考是高職院校招生的主要渠道,輔之以面向中職生的單獨招生。所以省域內的應屆高中畢業生和中職畢業生的保有量是擴招的基礎,擁有較多適齡高中或中職畢業生的省域潛在生源越多,其擴招的潛力越大,再加之百萬擴招的新增生源對象:農民工、下崗職工和退伍軍人,上述生源在省域內占比越多,應分得的擴招份額應越多。

表2 全國各省份示范校、骨干校、優質校數量統計表 (單位:所)
從高考生源數量來看(見表3),河南、廣東、山東、四川、安徽、河北、湖南等居前,與各省份人口排序基本一致。從高考招錄比來看,浙江、內蒙古、西藏、河北、江蘇等省份靠前,而總人口數量較多的省份招錄比相對較低,基本維持在全國高考招錄比線上下,同時也體現出百萬擴招的生源變化和潛在生源蘊含量。
(四)整體統籌與東西部地區存在的差異
百萬量級擴招既要考慮產業發展需求量、辦學容納量和潛在生源量等,又要考慮東西部地區所存在的差異,比如貧富差距、產業差距等。由于東西部地區經濟實力的差異,導致東西部在產業布局上存在差異,在人才需求量上也存在差異。東部地區產業越發達,則經濟實力越強,對人才培養需求力度也越大;西部地區反之。正是由于東西部地區的差異,百萬擴招任務的責任分解過程中既要考慮東部地區對人才的緊迫需求,也要考慮到西部地區剩余勞動力較多的現狀,多分配些名額到西部以使得西部適齡勞動力接受技能教育,以幫助他們擺脫貧困的制約。所以百萬擴招任務分解過程中在全國全盤考慮的基礎上,還應注重東西部的地區差異、南北方的差異,整體統籌百萬擴招的份額分配。
二、百萬擴招任務的責任分解層級
擴招100 萬人的任務下達后,如何分配這些招生指標就成了首要問題,按什么標準分解份額至關重要。部分學者建議從省域層面分解,部分學者提出從行業層面分解,還有部分學者建議從校級層面分解。教育部印發的《高職擴招專項工作實施方案》中雖然明確了中央統籌、分省確定招生計劃等宏觀層面的分配措施,但是在具體實施中還應兼顧行業和校級兩個微觀層面再次分解任務。
(一)省域層面分解
省級行政單位是我國教育實施的主體,各個行政主體按照所屬行政范圍內的情況進行教育資源分配,行政邊界劃分也就成為我國各個類型教育實施范疇的劃分界限。所以,在百萬擴招任務下達后,按照省域進行擴招任務分配是較佳標準,教育部印發的《高職擴招專項工作實施方案》也已明確中央統籌、分省確定的分配原則。對于擴招責任在省域層面的分解,田志磊(2019)認為可重點考慮高職招生數或本省高中階段畢業生數(或高考生源數量,見表3),以及每萬元GDP 高職招生人數、高職經費占總教育經費比重、高職財政性經費占高職經費比重等指標[5]。從上述指標進行綜合統籌來分解百萬擴招的任務是較為合理的辦法,但是按上述指標分配擴招指標往往太過于剛性,比如產業發達地區亟需大量高技能人才,但是按照指標進行分配所得的擴招指標又不足以支撐產業發展需求,這時就需要重新考慮分配的合理性。胡峰(2018)認為招生數量可以酌情考慮向廣東、江蘇等經濟實力比較強的省份傾斜,或重點向教育資源比較突出的江蘇、浙江等省份傾斜[6],抑或向勞動力輸出大省山東、河南、四川等省份傾斜,這樣可以把擴招生源指標盡可能地用到產業發展亟需之地、教育資源豐裕之地、潛在生源眾多之地。總之,省級地方政府可根據人才需求、辦學資源和生源供給等實際情況,探索改革百萬擴招的招生考試辦法。

表3 全國各省份人口及高考生源數量、招錄比統計表
(二)行業層面分解
區域產業發展情況以及產業結構比例決定不同類型的人才需求量,某一產業在區域經濟中占比越大,該產業所需的高技能人才越多。正是基于上述事實,部分學者提出從行業層面分解百萬擴招的任務。馬成榮(2019)提出可以根據全國產業結構按照區域占比去分解百萬擴招總任務,全國統籌從產業層面按比例分解擴招指標;然后根據各個省份的產業占比和省域產業結構比例,按照行業類別分解省域或行業總指標[7]。總之,高職院校根據可挖掘的辦學潛力和承受力,依據不同的行業背景從行業層面自主申報擴招指標,以滿足省域產業發展對技能人才的需求。
(三)校級層面分解
除上述按照省域、行業分解任務指標外,還有部分學者提出按照院校類別分解百萬擴招的任務,比如按照國家示范校、國家骨干校、國家優質校、“雙高計劃”以及其他普通高職院校進行指標分解。邵建東(2018)建議將高職院校擴招的主要情況分為三種:第一種是辦學質量高、規模大、辦學空間局限的院校,適宜采取穩定計劃控制規模的措施;第二種院校因地方對人才有大量需求,可以增加計劃適度擴張;第三種是辦學水平較為一般的院校,可以借此機會爭取計劃招足學生[8]。梁克東(2019)提出高職院校可以自主招生的形式在附屬技師學院當中選擇符合自身需求的學生,將國家級、省級技師學院納為高職院校全日制人才培養教學點,以增加高職生源擴招落實單位[9]。上述學者建議應將百萬擴招指標“重點布局在優質高職院校”,比如200 所國家示范校和骨干校,以及各省市建設的300 多所優質校。
三、百萬擴招任務的責任分解機制
面對擴招100 萬人的規模,按照省域宏觀層面和行業或校級微觀層面進行任務分解后,還需要對分解后的實施機制進行構建,形成關聯性機制、匹配性機制、飽和性機制和銜接性機制為主的整體責任分解機制。2019年5月,教育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農業農村部、退役軍人部等多部門聯合印發的《高職擴招專項工作實施方案》,給出了百萬擴招任務的責任分解機制。
(一)關聯性機制:人才培養與產業經濟相關聯
職業教育的本質性工作是為各個行業培養技能型人才,這就意味著職業教育活動與產業經濟活動息息相關,職業教育人才培養與產業經濟具有極高的關聯性。離開產業經濟談職業教育失去了目標,離開職業教育談產業經濟失去了底氣。在分析高職院校與經濟活動的關聯機制后,周森,劉云波(2019)指出百萬規模的招生擴招中可能會導致高職院校人才培養與經濟產業相關性的下降[10],所以說百萬規模擴招不是盲目地擴大招生規模這么簡單,百萬擴招必須與區域產業經濟發展相關聯,培養滿足經濟發展的高技能人才,而不是盲目地培養學歷人才。一旦高職院校在擴招中的人才培養與產業經濟活動失去關聯性,則職業教育的社會價值將會大大折扣,失去了百萬擴招的真正價值與現實意義。因此,高職院校百萬規模擴招過程中,尤其是在百萬任務的責任分解時,應時刻保持與產業經濟活動的緊密關聯性,將擴招指標分配至最需要高技能人才的產業之中。
(二)匹配性機制:專業設置與產業結構相匹配
高職院校人才培養除了要與產業經濟活動相關聯外,還要注重專業設置與產業結構相匹配。邵建東(2019)通過對職業教育與地區產業結構關系的實證研究,指出地方政府應有積極作為,細化產業發展所需要的技能人才,與高職院校一起建立與地區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相匹配的人才培養方案[11]。所以,高職院校應抓住這次百萬擴招的機會,將擴招指標盡可能多的匹配產業亟需專業的建設之上。總之,在高職院校大規模擴招的機遇中,主要從宏觀層面上優化專業設置,并實現人才培養與產業結構相匹配,在省域層面上實現高技能人才培養與產業結構相匹配的優化調整。
(三)飽和性機制:指標投放與行業需求相飽和
百萬擴招背景下的人才培養與產業經濟相關聯是前提、專業設置與產業結構相匹配是核心,但同時擴招指標投放也應指向并滿足行業需求以達到飽和狀態。所謂飽和狀態意味著百萬擴招的指標既不能投放過量導致人才培養過剩,同時也不能指標投放量過少致使人才培養不足,這就要求指標投放與行業需求相飽和。胡峰(2019)認為針對部分產業在當下或者今后一段時間里技能人才需求已趨于飽和的情況,擴招所來的百萬生源在行業需求和專業投放上應有所側重[12]。一方面將擴招指標側重于未來快速發展行業,比如家政、護理、智能制造等產業;另一方面將擴招指標盡量緩投或不投向人才供給過剩的行業,比如計算機維修、汽車維修等行業。所以,百萬擴招的指標投放應與行業需求相結合,行業亟需的專業多投放,供給過剩的專業少投放,維持供與需的均衡飽和狀態。
(四)銜接性機制:擴招方向與新興產業相銜接
高職院校實施百萬擴招計劃,擴招的主要方向一方面要與新興產業相銜接,另一方面要與緊缺專業相銜接,同時做好不同層次的職業教育相銜接。劉曉(2019)認為高職院校擴招生源應向發展前景更好的專業傾斜,諸如新興產業、康養服務產業等[13],百萬擴招的機遇可以快速推動職業院校在新興產業領域的快速介入。王家源(2019)認為高職院校改革要加快緊缺專業的人才培養,在技術技能人才緊缺領域開疆拓土[14],比如學前教育、養老護理等專業,同樣百萬擴招的指標投放應向這些專業傾斜。同時,佘穎(2019)也認為高職院校百萬規模擴招要做好不同層次之間職業教育的銜接[15],比如中職與高職的有效銜接,以保障擴招規模的順利實現。面向中職畢業生的單獨招考制度,是高職院校招生依靠高考渠道的另外一條途徑,也是最重要的渠道。所以,高質量完成百萬擴招的任務,離不開擴大中職畢業生的招生比例,近期發布的《高職擴招專項工作實施方案》也給予了明確答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