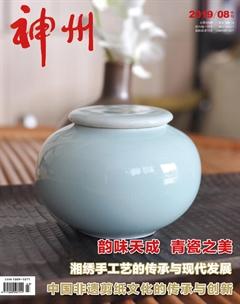從空間批評視角解讀《小小小小的火》
牛越
摘要:小說《小小小小的火》是華裔美籍女作家伍綺詩的又一新作。這是一部關于階級、種族、家庭、夢想、藝術等方面的小說。以往的作品大多從互文性、主題分析、倫理等視角對這部小說進行分析。本文試從空間批評視角對《小小小小的火》進行解讀,從而使每個在自己道路上奮力前行的人,都能過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關鍵詞:空間批評;景觀空間;社會空間;個體空間
引言
《小小小小的火》為我們描寫的是理查德森一家和新房客米婭之間發生的一系列故事,實際上是在探討不同的價值觀下有著不同的人生追求與生活方式,選擇以何種方式度過我們的一生,是這部小說最想要傳達給我們的。
一.伍綺詩與《小小小小的火》
伍綺詩(Celeste Ng),華裔美籍女作家,是香港移民第二代,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和俄亥俄州長大。她畢業于哈佛大學英文系,從事寫作多年。《小小小小的火》是伍綺詩繼《無聲告白》之后的又一經典之作。《小小小小的火》出版于2017年,一經出版就榮登各大排行榜之首,獲得2017亞馬遜年度小說的桂冠及其他27項年度圖書大獎。《紐約時報》書評稱贊此書道:“極端、劇烈、熾熱,令人心碎不已,比《無聲告白》更勝一籌”;《金融時報》稱:伍綺詩塑造出來的故事結構,會帶著木匠般的真實質感。當代小說家中很少有人能像伍綺詩這樣聰明,飽含愛心和同情心。無論我們選擇怎樣的人生,我們都要付出一定的代價。
二.空間批評
空間批評理論是近三十年來西方學界興起的重要的批評理論與批評方法,也是當前學術界的熱點話題。在傳統的文學批評研究中,評論家大都過多地關注作品中的時間問題,而忽略了空間。但在20世紀末期,西方學界經歷了一場引人注目的“空間轉向”,“空間”開始受到學者們越來越多的關注。空間批評是20世紀80年代在文化地理學和文化研究等后現代理論的基礎上逐步發展起來的文學批評方法。空間批評通過融入多種文化研究理論,強調對文學空間的社會文化解讀,更加關注現代性所造成的空間與社會和文化的融合,注重“強調文化是人與人之間、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各種關系,通過文化作為中介、平臺、生活圈等等空間隱喻,將文化研究空間化”[1]
(一)《小小小小的火》中的景觀空間
景觀是一部小說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它常常以地域、場景、建筑等形式出現在文本中。自然和地理景觀在空間批評中變成了一種象征系統,凸顯出景觀的文化屬性。[2]小說中的西克爾高地,是主人公理查德森一家的家庭住址,也是整個故事發生的大背景。西克爾高地在這部小說中代表著也象征著規則的存在。小說中有這樣的描寫,:“以房子該漆成什么顏色為例,市政部門曾經發表過一份說明,將本地房屋的建筑風格分為三大類:都鐸式、英式和法式。要求居民根據不同的建筑風格選擇適當的顏色。”[3]12 總而言之,在西克爾高地,一切且有定規。實際上,這座城市的座右銘就是“經過規劃的才是最好的”,背后的潛臺詞:任何事物都可以----也應該----被規劃,從而避免出現不恰當、不愉快甚至災難性的后果。作者之所以會把故事設置在西克爾高地這一地點,是因為在理查德森太太埃琳娜的心中,沒有哪一個小鎮能比西克爾高地更完美,更符合她心中的期望。這里的景觀就是一種隱喻,西克爾高地在這部小說中就代表著完美,同時也象征著一成不變的規則,與米婭母女那毫無規劃,隨性而富有創造力的生活方式形成鮮明的對比。
(二)《小小小小的火》中的社會空間
社會空間不僅指人們的活動場所,重要的是人物在社交場合交流中所體現的非物質空間,如人物在社會空間中的行為方式和結果等。社會空間有時會體現為一種思想同另一種思想的交鋒、一個群體階級對另一個群體的壓迫和反抗,這些都是小說中社會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2]
小說中的埃琳娜·理查德森是克利夫蘭的一家報社的一名記者,有著體面的工作,穩定的收入,很好的愛人和四個可愛的孩子。與她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新房客米婭。米婭是一個為藝術而流浪的人,她熱愛藝術,為藝術癡迷。埃琳娜與米婭之間的關系,是房東與租客的關系,是記者與流浪藝術家的關系,更是規則與自由的關系。兩人的思想在這個社會空間內發生了激烈的沖突。表面上看似毫無交集的兩個人,卻因為房東和租客的關系聯系在一起,又因為兩人象征著不同的社會意識形態因而擦出了更多的火花,產生了思想上的碰撞。理查德森太太把房子租給別人這一舉動,在她心目中她認為這是她對別人善意的一種表現,更重要的是在她的內心,她居然希望別人要從心底里感謝她的這一善意。埃琳娜從心里就抵觸和自己不是同一意識形態的人,所以在面對米婭的時候,她居高臨下,一副女主人的樣子;所以她不喜歡小女兒伊奇的特立獨行。埃琳娜所處的社會空間比較狹小,基本是在家里或者在報社。但是在故事的高潮部分埃琳娜經歷了一次空間轉換。那就是當女兒伊奇請求她幫忙調查藝術博物館陳列的“圣母子1號”照片中的人物是不是米婭時,這一請求觸動了埃琳娜的職業自尊,讓她覺得這是一件值得調查的事情。所以埃琳娜動身從西克爾驅車前往賓夕法尼亞,去拜訪米婭的父母,去查清米婭的底細。
相對于埃琳娜而言,米婭經歷過多次的空間轉換。這跟她追求的藝術相關,米婭會不定期的搬家,為自己所熱愛的藝術尋找靈感。但也并不是每次的轉換都是在為藝術獻身。在米婭多次搬家的經歷中,最為典型的一次是她從匹茲堡開車一路來到舊金山,在桑賽特定居的這一空間轉換。那段日子對于米婭來說是糟糕的,不能參加心愛弟弟的葬禮;不被自己的父母理解和接受;在孤身一人的情況下馬上就要成為一個新生生命的母親;得知疼愛器重自己的恩師病危的消息。那段日子對于身處這一時空下的米婭來說,是不友好的和殘酷的。
(三)《小小小小的火》中的個體空間
個體空間是一種表征的空間,是特定空間被賦予了個體特征的空間。小說中不同人物的的個體空間有各自的特點,無論是主人的居所,還是人物的內心獨白,都明顯給小說的空間刻上了人物的思想特征。[2]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內心世界,都有自己的秘密花園,那里存放著自己的心事,小心翼翼生怕打擾。珀爾,房客米婭的女兒,一個安靜敏感、聰明可愛的女孩。在同母親定居西克爾后,在認識新房東理查德森一家后,珀爾的內心世界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她會主動和母親米婭聊起在理查德森家都做了些什么事,看了哪些有趣的電影。她發現自己越來越能融入到理查德森一家,越來越像他家的一份子。但當珀爾得知母親會去理查德森家當臨時工時,“珀爾沒有繼續發難,但在內心深處,她并不滿意母親對“她的空間”---理查德森家---的“入侵”行為。”[3]84母親的到來使珀爾覺得她的個人空間受到了侵犯,因為母親會在理查德森家里聆聽一切、觀察一切,這會使她感到不自在,這會使她羞怯于做自己想做的事---接近她喜歡的崔普。
在米婭的內心深處也藏著一個驚人的秘密,那就是珀爾的身世。在聽到和這一話題相關的詞匯時,米婭就會不由的感到緊張。“然后她猶豫了,因為不知怎么,她隱約覺得事情并沒有那么簡單,她感覺自己就像踩在了一級搖搖欲墜的樓梯上,心中充滿了腳下的木板即將掉下去的預感。”[3]115“背對著他們的米婭看起來并無異樣,從容自若地在水龍頭下沖洗雙手,但四個孩子都看到了:在聽到珀爾說話的那個短暫的瞬間,她的身體變得有點兒僵,像被一根線突然拉緊了一樣,但隨即便放松下來。”[3]116米婭的這一反映是在孩子們質問她藝術博物館里陳列的“圣母子1號”照片中的人物是不是她時而產生的。當時的米婭極力隱藏自己的情緒,好在孩子們還小,還在珀爾及時停止了提問。可是紙是包不住火的。隱瞞過了孩子,可是沒能騙的了埃琳娜。在埃琳娜的質問下,米婭的個人空間開始瓦解,理查德森太太瞥了米婭一眼,“別試圖說謊,你是個十分高明的騙子,但我己經知道了,我對你了解得一清二楚。”[3]352頃刻間,米婭隱形的外衣被撕破,她瞪大了眼睛。
三.結語
本文從生態批評視角對《小小小小的火》這部小說進行解讀,將人物、自然,思想融入到空間中。自然景觀空間體現出了西克爾高地的全貌,介紹了生活在那里人們的生活背景;社會空間構建出了兩個不同階級等級的人物思想的碰撞與沖突;個人心理空間折射出了每個人內心深處的秘密,那一束束正在燃燒的小火苗。生活中,我們身上被賦予很多的角色與期待,有時候我們渴望摘下面具做真正的自己。就像小說中的米婭與伊奇一樣,沖破世俗的眼光,找到真正的熱愛。永遠記得,你呼吸著的每一個瞬間,都應該去過你真正想要的生活。
參考文獻:
[1]李蕾蕾.當代西方新文化地理學知識譜系引論[J].人文地理,2005 (2):79
[2]屈榮英.從空間批評視角解讀喬伊斯的《死者》[J].文學與藝術 2009 (7)
[3]伍綺詩.《小小小小的火》[M].江蘇: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