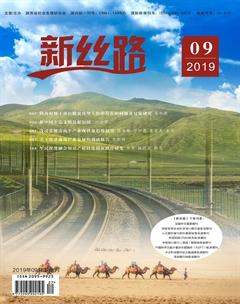傳統的力量
《京畿筆談》是亞歷山德拉·葛女士于1918年出版的關于中國的一本書。該書是英文書,藍色的封面上題著“京畿筆談”四個字。該書收錄在1918年7月的《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會刊》的書目列表中。1919年4月的《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會刊》上刊登了關于該書的一篇5頁的書評,認為該書展示出對中國人深切的同情,對中國哲學由衷地欣賞,從很多方面看都是一本有價值的書。
亞歷山德拉,1868年出生在德國,后在英國讀書,1894年4月嫁給英國人弗雷德里克·葛。二人婚后共育有四子,最為人熟知的是次子葛量洪,1947-1957年出任第22任香港總督。二人的另外三子,長子和四子分別在一戰、二戰中陣亡,三子夭折。亞歷山德拉的丈夫于1915年5月在法國陣亡。一戰后,亞歷山德拉再婚,嫁給曼德將軍,結婚時間不詳。曼德,1887年來華,供職于大清海關,1895-1900年跟隨袁世凱在小站練兵,1900年參與解救被困北京的外國駐軍。后曼德成為袁世凱的副官,在辛亥革命中,曾代表袁世凱與他國外交官聯絡。當時擔任袁世凱顧問的莫理循對曼德很是厭惡,認為他是個騎墻派。
亞歷山德拉算得上是多產的作家,曾出版多部詩集、戲劇詩,大多是關于戰爭的,如1915年出版的詩集《悲傷的母親》是為了紀念她的長子。據學者薇薇安·紐曼的研究,她的丈夫和長子均為英國戰死沙場,但由于她出生在德國,遭到懷疑和猜忌,被認為是英國的“敵人”,只能通過詩來表達思念及對戰爭的痛恨。就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京畿筆談》是亞歷山德拉第一本關于中國的著作。她對中國的興趣應與曼德有關,因為是在與曼德結婚之后才移居到北京。再者《京畿筆談》是1918年出版,她不大可能是受到葛量洪的影響,畢竟葛量洪在1922年底才被派到中國。
《京畿筆談》,全書共七章,章節沒有標題,按數字排列。第一章可以算作是總論,像中華文明的特點、中國的歷史、近代中國的遭遇、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的比較等等。第二、三章,介紹了中國從伏羲、夏商周再到秦漢的歷史。第四章,主要是從唐朝到宋朝的歷史。第五、六章,主要介紹元朝、明朝、清前期的歷史。第七章,其中部分是關于清朝的歷史,部分是圍繞北京城來展開,像元明清三代對北京的建設,北京城的價值等。亞歷山德拉坦言到20世紀初西方已有很多關于中國的書籍,其中相當大的比例是來華傳教士所寫,這些書大部分帶有偏見。她在書中以玩笑的口吻說,可能需要再來一次焚書。亞歷山德拉看到中國的歷史如此悠久,對于究竟應該從何寫起,多大的篇幅才能將中國的發展歷程呈現出來,是比較困擾的。盡管如此,《京畿筆談》的時間跨度也很大,回顧了從有巢氏到清滅亡的中國歷史。
《京畿筆談》想要解決的問題是中華文明何以成為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及在20世紀20年代,如何來看待現代與傳統。亞歷山德拉坦言很多歐洲人看中國是不動的,停滯的,是因為歐洲人習慣了快速的轉變,沒有考慮到中國悠久的歷史。歐洲兩三千前的歷史、社會和習俗,除了考古學者、歷史學者外,少有普通民眾關心,而中國幾千年的傳統、習俗還在影響著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國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中國人十分珍視自己的過去。中國人珍視歷史的原因是因為中華文明的發展有其本源,基本上沒有大規模外來傳統的影響,不像北歐和西歐因為在羅馬帝國的潰敗,被迫接受了外來的希臘文明。直到近代,中國人所思所想都是從祖先那里繼承來的。歐洲的情況就不同了,不管是凱爾特人,還是日耳曼人,敬拜從巴勒斯坦來的上帝,遵從從羅馬帝國來的法律,他的思想跟他的血統沒有關系。
討論到中華文明沒有中斷的原因,不少人會提到地理因素,認為是中國地理位置相對封閉,來自外界的威脅較少。亞歷山德拉回顧了中國的歷史,認為中國面臨來自邊界的挑戰并不少,匈奴、突厥、契丹、韃靼等時常侵擾。也是在不斷的沖突與調和中,中國與亞洲北部、西亞、南亞等地區建立聯系,雙方都從中獲益。至到清中期,中國選擇封閉,或許是因為害怕外來的挑戰。從中國長期的歷史發展歷程來看,地理位置封閉并非中華文明延續主要原因。
接著亞歷山德拉討論的是家庭的力量,家庭、宗族將每個成員緊密的連結在一起。家庭而非個人,是社會的基本單位,在其中還有一整套的教導,像尊老愛幼,關愛窮人等。家庭是有益的,保守的力量,怎么看重家庭的力量都是不過分的。家庭固然是中華文明延續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家庭不鼓勵原創和個性,其弱點也是明顯的。對于家庭的重視,在近代是外國人分析中國保守、落后的一方面,如麥高溫所說,中國人把全部精力和感情都傾注在家庭之中了,從而使他們的愛國熱情不復存在了。
第三是“順天”,亞歷山德拉不止一次提到她非常喜歡北京的舊稱——“順天府”。她認為使中華文明保持活力的因素是順天,遵從道、義、理性。國家是建立在順從天意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以自我為中心的野心上。在亞歷山德拉看來,中國是為數不多以道德立國的國家,而非軍事或商業。她舉了幾個例子來對比,如元朝的建立,雖軍事強大,但缺乏穩固根基;拿破侖激起民眾的熱情,但為了滿足自己的野心;羅馬帝國追求利益,催生了高效政府和發達的交通網絡,但主要為物質方面服務;終究都不能長久。
此外,亞歷山德拉花了不少篇幅來論述中國人的信仰。西方人總是認為中國缺乏信仰,亞歷山德拉則認為“中國人什么都拜,是否比其他人更接近真相”的問題。在她看來中國人不僅認為眾多神是神圣的,看祖先、父母都是神圣的。這里提到的“祖先崇拜”的問題,據楊慶堃的研究,是中國本土宗教體系中四個關鍵部分的其中之一,對中國的影響非常深遠。而到近代,西方人不了解中國人及其信仰,視“祖先崇拜”為偶像崇拜,甚至“是解釋中國一切缺點的關鍵”。除此之外,中國人看大地山川、日月星辰都是神圣的,更能欣賞自然之美、自然之和諧。
亞歷山德拉十分看重儒家思想的影響,在她看來,中國圣人看重的是天、地、人,對應精神的力量、物質的力量、自我與社會的關系。在歷史的長河中,發展出一整套詳盡、莊嚴的儀式。孔子就出生在中國,他更了解民眾的需求,也教育得更好。傳教士到中國才多長時間,況且他們在自己的國家都算不上眼界開闊的人。孔子的教導不是超自然的體系——在各種神跡的基礎上,用未來的重生來面對今世的苦難。孔子的教導是一套規則,有知識、有智慧的人,富有經驗,品格高尚,引領跟隨他的民眾過好每天的生活。
亞歷山德拉也推崇儒家對儀式的看重,認為孔子堅持隆重的儀式,不是目的,而是一種方法,達到在沖動的想法和付諸行動之間有停頓,使中國人不至于一時頭腦發熱就去行動,學會控制自己,這恰恰是歐洲欠缺的。她看到20世紀的中國人,放棄了自己的傳統儀式,覺得十分可惜,失去的好像只是外在的禮貌,實際上失去的多得多,自我修養的支柱動搖了。
到了近代,中國在中西交涉中屢屢受挫,開始懷疑自己的傳統,這棵滋養了無數代人的老樹,是否應該被砍了,給外來的植物和種子騰出地方。亞歷山德拉用日本的例子來說明,現代與傳統并非對立,可以學習歐洲的科學、管理的力量,而不破壞本國傳統。她認為日本是融合新舊、東西的典范。日本學了鐵路、汽船、電話、機器、槍炮,各種設備;建立了議會,但是沒有推翻皇室,保留了天皇,也沒有否認古老的信仰,只是在旁邊按照最新,最有效的標準建立了新學校、軍營、工廠。日本不僅將新酒裝在舊瓶里,而且將有價值的新枝接在老樹上,需要高超的技巧,也需要老樹供養新枝,直到新枝成活,成為老樹的一部分,給久經風霜的老樹帶來新的美。
與日本相比,外國的發明和機構,鐵路,郵局,議會,同樣介紹到了,卻給人悲傷的印象。它們作為舶來品,和中國民眾的真實需要沒有多少關聯。中國的問題顯然不是引進一些機器和管理方法就能解決的,而是需要一種信念,根植于民眾血液中,一旦觸動了民眾的心,能夠釋放出他們潛藏的力量。這種信念,是愛國主義,能影響到全國各地,各階層,使得理想中強大、獨立的中國得以實現,這是最好的愛國主義。中國嘗試了最壞的,不是出于對國家的愛,而是出于對外國人的恨,不是出于國家的責任,而是盲目、驕傲自大,就像1900年的義和團。不僅不能展現國家的尊嚴和力量,帶來的后果是屈辱和災難。很快發生了革命,看似是補救,到1918年仍處在實驗階段。在亞歷山德拉看來,中國的危機遠遠比表現出來的嚴重,在這樣深重的危機中,換領袖是很少會有效的。
在這種情況下,公眾思想是混亂、分裂、搖擺不定,中國這艘大船沒辦法再按照古時的方法靠岸。中國需要和平,內部和外部的,需要喘口氣,去想想自己失去的和得到的。不是靠卑躬屈膝或是表面模仿外國的發明,抑或是時斷時續的武力沖突,能幫助中國經受住暴風雨。亞歷山德拉用普魯士的例子來說明,在危機中將愛國情懷轉換為力量需要根植于傳統。愛國精神是微妙的品質,根植于自豪,需要自力更生的意識或是潛在的偉大信念長期滋養。它不會來自現在或是可見的未來,只能到過去尋找。中國無比輝煌的過去,足以成為愛國精神的持續動力。中國人更應從自己的精神財富中汲取力量,需要分辨歷朝歷代給“經典”做的注解,不都是有價值的。中國還是需要去自己圣人的教導中尋求指引。
亞歷山德拉的《京畿筆談》,視野寬廣,將中國放入世界之中,古時的歷史與羅馬、希臘等比較,近代的發展與歐洲、日本相比較。《京畿筆談》在很多外國人都輕看中國,甚至中國人懷疑自我的時候,看到中華文明的閃光點,分析中華文明存續的原因,發現傳統文化的力量,難能可貴。亞歷山德拉看重傳統的力量,同樣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強調要大力弘揚中華傳統文化,要把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標識提煉出來、展示出來,把優秀傳統文化中具有當代價值、世界意義的文化精髓提煉出來、展示出來。時至今日,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領域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的同時,如何讓優秀傳統文化迸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并且走向世界,《京畿筆談》無疑可以帶給我們一些啟示。
除《京畿筆談》外,亞歷山德拉還寫了多本討論中國歷史與文明的著作和小冊子。如1927年出版《中國歷史畫卷:從起初到乾隆》,1934年出版的《一位滿族皇帝:嘉慶帝傳》,還曾寫過關于“天壇”的小冊子,出版年份不詳。從學界的研究來看,目前外國學者多關注她作為詩人和女性的研究,國內學者關注不多。總體來說,亞歷山德拉在“中學西傳”的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還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無論從史料還是專題研究的角度,這些將中國文化介紹到西方的著述,亟需得到學界的重視。
作者簡介:
王靜(1983--)女,博士,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講師,研究方向: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