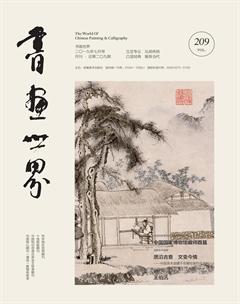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師酉簋
翟勝利



編者按:2018年伊始,安徽美術出版社與中國國家博物館聯袂推出《中華寶典——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法帖書系(第一輯)》,本刊從2018年第一期開始,陸續刊登了法帖部分內容,受到讀者的歡迎。現第一輯已介紹完畢,從2018年第十一期開始,本刊將繼續刊登本書系第二輯和第三輯的內容,包含宋拓顏真卿《東方朔畫贊碑》《劉熊碑》、民國拓《元顯攜基志》等精良拓本,以及董其昌《行書贈張旭、題盧道士房詩卷》、文天祥草書《謝昌元座右辭卷》等珍貴墨跡本,希望廣大讀者能喜歡并提出寶貴意見。
師酉簋是西周中期的一件青銅器。作品通高22.5厘米、口徑19.1厘米、足徑20厘米,重4.94千克。
師酉簋最遲在清代中后期即已出土面世,傳世共有四件,一件現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其余三件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這四件師酉簋的大小、形制、紋飾、銘文基本相同,應屬同時鑄就并成組搭配使用的一套青銅禮器。這套禮器器形典雅莊重,銘文書體優美、規范,具有頗高的考古、歷史、藝術研究價值,值得學界充分重視。現對其基本情況尤其銘文書法方面的特點進行介紹。為便于行文,本文分別稱其為師酉簋甲、乙、丙、丁。
師酉簋甲[《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以下簡稱《銘圖》)編號05347],原藏于阮元、吳云、陳受笙、朱筱漚,后歸故宮博物院,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師酉簋乙(《銘圖》編號05346),先后經阮元、吳云、金香圃遞藏,1959年由國家文物局調撥至故宮博物院。據研究,甲、乙兩件師酉簋的器蓋出現了互置。
師酉簋丙(《銘圖》編號05348),原屬朱筱漚、徐乃昌收藏,后歸故宮博物院。此簋之蓋沿飾竊曲紋,與器身及其他各器蓋紋飾明顯有異,顯然并非原蓋,故《三代吉金文存》《殷周金文集成》《金文總集》等金文著作僅收其器銘拓本。吳鎮烽先生指出,《小校經閣金文拓本》一書所收蓋銘拓片,有可能是該簋蓋上的銘文。
師酉簋丁(《銘圖》編號05349),失蓋,原藏于端方、顧壽康、馮恕,1955年馮公度家屬以其名義捐獻給故宮博物院。
這組師酉簋的器形、紋飾、銘文均屬于西周中晚期的典型樣式,此處僅以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師酉簋甲為例加以介紹。器斂口,鼓腹,圜底,圈足下接鑄三個獸面狀扁足。蓋面隆起,上有圈狀捉手。口沿兩側有一對獸首半環耳,耳上之獸的獸角呈螺旋狀,垂珥上有獸身狀紋飾。蓋沿、器口沿分別飾以大小相間的重環紋,圈足飾單體重環紋一周,蓋面及腹部飾瓦棱紋。
蓋內與器內底對銘107字,分11列,每列9至11字。銘文記載的是一次廷禮冊命的事件,其大意為:周王元年正月,王在吳地,到達吳的太廟并主持師酉的冊命典禮。公族之官釐作為典禮的賓佑,引導師酉進入廟門,站立于庭院之中。王召史官墻宣讀冊命書:“師酉,管理你的祖上世代管理的城市官員邑人和王的近衛部隊,部隊中包含西門、、秦、京、弁狐等地的夷人。賜你大紅色的蔽膝,配有紅色的帶子,還有一套馬籠頭。日夜恭敬其事,不要荒廢我的任命。”師酉拜謝,叩首。為報答和宣揚周天子偉大而美好的任命,師酉制作了這套銅簋, 用來祭祀其亡父乙伯、亡母姬,并希望其子孫后代萬年永遠寶用這套吉金彝器。
該器外底刻有“阮元寶用”銘文,應為阮元收藏時所制,表明阮元對該器異常珍視。
師酉簋的器形、紋飾、銘文皆表現出顯著的西周中晚期特征,結合銘文中出現的年代信息和人物線索推測,銘文記載的冊命事件應發生在周懿王元年(前899)或周孝王元年(前891)正月,該組銅器的鑄造也大致發生在這一時間之后不久。
周武王克商之后,周人在承繼商代青銅禮樂文明的基礎上,對其進行了開拓性的改造和創新,金文書法方面便是如此。西周早期的金文作品,無論首尾尖細或頭粗尾細的線條處理,還是有意為之的波磔肥筆,金文均顯露出濃郁的晚商遺風。西周中期,經歷長期醞釀之后,一系列影響深遠的政治、經濟、軍事措施得以實施和完善,西周王朝逐漸走向鞏固和成熟,周人在文化藝術方面的氣度和風格也逐漸顯現出來。這一時期,青銅禮器的鑄制數量迅速增加,銘文涉及的內容更加豐富,金文的單篇長度和總體數量均遠逾前代。在此過程中,西周金文書法進一步走向成熟。
西周中期是金文書法走向線條化、簡約化和規范化的重要時期。商代和西周早期金文書法的方圓曲直變化顯著,常見修飾性的肥筆,這很大程度上源自早期象形文字的仿形特性,如“王”字下端的肥筆來自斧鉞刃部的形狀,“元”字上端的圓形肥筆源自人頭的形狀,“彝”字下端肥筆源自人類雙手的形狀,等等。西周中期,隨著金文文字本身的發展以及金文書法藝術的日益成熟,肥筆現象迅速減少,西周金文呈現出規范化、線條化的傾向。從文字形體擺脫原始構型,向符號化的形式美方向演進之后,書寫的價值被日益肯定,線條完成了從客觀自然仿形到主觀美化仿形的改造,字形的圖案化使書法藝術從直觀審美轉向抽象審美,線條變得更加含蓄,更加富于象征含義和藝術感染力。
從西周中期開始,金文文字的實用性和書法美的典范性有機地結合成一個整體。法度雍容、線條精勁的金文書法成為西周王朝氣度的一種象征和體現。然而這一時期的金文并未因過分追求規范化而陷入刻板僵化的地步,書寫者利用線條的粗細短長、剛柔變換,結體的疏密工拙,偏旁的位置調節,字形的大小參差,筆意的疾徐沉浮來調節作品的氣韻,多元的變換組合和筆法處理,可以創造出各式各樣的書法風格意蘊。
師酉簋銘文字數多達百字以上,篇幅相對較長,其書法結體勻美、筆意純熟,可以看作是西周中晚期金文的典型代表。在行文布局方面,銘文在保持縱向自然成列的同時,并未勉強追求橫向文字的整齊劃一,避免陷入呆板窠臼;在字形字體方面則方圓兼施,錯落有致,“太”“廟”“公”“族”等字的收放對比和筆法處理使銘文保留了婉轉流暢、跳躍靈動的意趣。認真審視細節,還能發現師酉簋銘文中保留了許多過渡時期的特殊現象。如“年”“釐”“冊”“秦”“朕”“寶”等字,某些部位還保留著早期金文中的肥筆孑遺,但已退化為復筆所畫的圓點;此外,“文”字字形則沿用了典型的西周早期樣式。
由于西周青銅禮器并未實現規模化量產,每器須單獨制范、書寫。師酉簋現存的七篇銘文風格氣韻相當接近,應出自一人之手。然而出于書法作品的不可復制性、早期文字字形的不穩定性以及吉金文字的殘泐漫漶、銹蝕等多方面原因,各篇銘文均反映出不同程度的差異。
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師酉簋甲的器蓋銘文僅有輕微銹蝕,字口清晰可辨,文字寬博雅致,堪稱研究、欣賞、學習西周中期金文書法不可多得的珍稀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