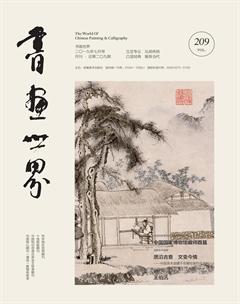中國傳統美學“以形寫神”與傅雷“神似論”的異曲同工之妙
仰靜
內容提要:本文主要探索顧愷之的“以形寫神”與傅雷“神似論”的差異性與共同性。“以形寫神”是中國傳統繪畫美學理論的主流思想之一,“以形寫神”中的“寫”字在形與神之間搭起了橋梁,通過客觀事物的外形描摹達到傳神的境界,最后上升到精神的內涵。“神似論”觀點的提出使得文學作品在翻譯時,須達到形神兼備,如二者不可兼得時要力求“神似”,以達到“化境”的境界。二者是一脈相承的關系。
關鍵詞:以形寫神;神似論;顧愷之
形神是中國傳統美學理論的一個概念,在先秦兩漢時期就已經出現在藝術領域,但這個時期的美術范疇還未形成,只是提出了形神問題,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才在中國藝術領域得到發展,形神的美術概念才被運用。《淮南子·說山訓》提出:“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這里提到的“君形”實質上說的就是神似,因為神似才使得表現的人物具有各自的形態特征。
東晉顧愷之的傳神論提出“ 以形寫神”,認為神是存在客觀物體的形象之中的,沒有形就沒有神,形是一種手段,以此達到傳神的目的。顧愷之在論畫中提出:“伏羲神農,雖不似今世人,有奇骨而兼美好;神屬冥芒,居然有一得之想。”通過對客觀事物的外形描繪,可以描繪神,通過形似來表達神似。在顧愷之的“以形寫神”這個理論中,一個“寫”字很關鍵。它是形與神之間的橋梁,通過“寫”這個動詞來將客觀事物外形傳遞到藝術家內心的情感世界。這個“寫”用得很微妙,用動詞來傳達這整個過程,通過外物的形象傳達出神韻。那這個神又如何表達在畫面中呢?對于形神關系的問題,顧愷之在畫論中認為最關鍵的是眼神傳遞。《世說新語·巧藝》記載:“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于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顧愷之認為繪畫人物的關鍵在于眼睛,這是點睛之筆,但是眼睛達到傳神的目的還不夠,還需要身體的外形來襯托,通過眼神與外形兩者合一來達到傳神的目的,這是局部與整體的和諧統一關系。故顧愷之主張的理論是以傳神為宗旨的形神兼備。當然我們對于繪畫中“神”的理解也不能只停留在一般層面,我們應該將其理解為一種精神層次。畫家對于一個事物的外形描摹會產生不同的精神面貌,個人對于事物的理解存在著不一樣的見解,根據自己經歷、個性、才情、素養等方面表達出的意境也就隨之不一樣了,畫家捕捉到的神應該視為個人精神的特性。
傅雷是中國文學翻譯史上的巨匠,他的“神似論”的提出在文學翻譯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繼嚴復提出“信達雅”之后又一重要的理論,使中國文學翻譯史邁向一個新的方向。傅雷的翻譯“神似論”取之于中國傳統美學,其主要思想是傳神,強調的是形似與神似的和諧統一關系,找到二者之間的平衡點。他在《〈高老頭〉重譯本序》中提出:“以效果而論,翻譯應像臨畫一樣,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在他看來,譯文要做到形神兼備,這是至高境界。這里沒有過多地闡述形似的界定,而是將重點放在“神似”上。有學者認為傅雷的“神似論”只看中神似而忽略形似,這樣的理解是有偏頗的。“神似論”是在盡可能接近原文意思下進行翻譯的,不求與原文翻譯絲毫不差,但一味地直接或機械地翻譯,失去原文的本來韻味,這就不可取了。
傅雷的論述“重神似不重形似”中的“形似”主要指的是保留原文的語言形式,即格式、詞義、修飾等;“神似”指的是用一種語言轉換另一種語言所表現出來的內容、思想、感情,這其實就是翻譯“神似”。通過語言文字的想象與模糊獲得形象化的意境,使得整個文章在形式與內容上和諧統一,最終達到形神兼備。
顧愷之的“以形寫神”理論在中國美學理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傅雷的“神似論”在中國翻譯史中也具有突出貢獻。無論是在繪畫領域還是文學領域,形與神都是相互存在、相互聯系的關系,需要辯證地來看待,兩者之間應該有一個平衡,不應拘泥于單個的形式,而缺乏內容的要求。“以形寫神”“神似論”都要求藝術家、學者對萬物的“形”具有特殊的敏感。藝術家對于繪畫對象外形具有深刻的理解,并對其進行描寫與模仿,把握事物的本質,從而傳達出精神意涵。學者對于原文了如指掌,吃透其含義,在此基礎上對譯文意境進行傳達。“以形寫神”不僅是中國繪畫理論中的主流思想,也成為文學翻譯的最高境界。文學翻譯中的“神似論”與繪畫藝術理論中的“以形寫神”的確有異曲同工之妙。“神似論”也是在繪畫美學理論中受到啟發的,譯文中存在“文”與“質”的理念及“形”與“神”的關系都源于中國傳統美學理論,這些理論是一脈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