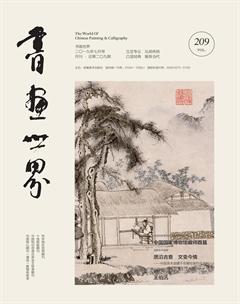淺論石濤《畫語錄》中“資任”說
張歡
內容提要:《資任》是石濤《畫語錄》的末尾章,關于此章,研究者有諸多的見解。本文通過分析《畫語錄》邏輯結構和本章具體內容,指出畫家需要哪方面的資取,從而全面提高創作素養。
關鍵詞:石濤;資任;筆墨;山水
《畫語錄》共計十八章,《資任》作為總結篇呈現在末尾章,有著收聚全篇之意,但關于“資任”一詞的定義尚未有一個明確的說明。
在《資任》章中,石濤以不同含義撰寫“資任”,“資”在全文中撰寫了三次,而“任”撰寫了六十六次。“資”“任”可分開,亦可合并而予以運用。同時“資任”可做動詞,亦可做名詞;可當作詞語來運用,亦可作為句法結構。其意甚是難解。部分研究者認為,“資”在文中呈現出的是審美心理之意,而“任”呈現的是審美對象之意,故“資任”一詞乃是指審美心理反映出審美對象,即“心源”以及“造化”兩者之間的聯系。根據對《畫語錄》原文的解讀,筆者更傾向于這樣的結論:“資”在文章中不作為獨立存在的理論意義,這并非比“任”使用的次數少,“資”可以解釋為資取、酌取之意,“任”以核心詞呈現,故“資任”可解讀為“取任”之意。《資任》大部分問題是涉及“任”。石濤利用中國漢字字義多樣性的特點,將自己的見解巧妙地呈現出來。
筆者想將“資任”放到石濤整個畫學體系中,尋求其真詁,而并非想在語境中逐一解釋此詞。
一、筆墨:任之所任
求藝術之大本源:“必先資其任之所任,然后可以施之于筆。”
《資任》開篇雖未提及“任”,卻是為后文埋下伏筆,即山水畫重在運用筆墨,呈現自然內在的“質”與“乾坤之理”,同時還包括受到天地的滋養和生活蒙養之利。
石濤說:“以墨運觀之,則受蒙養之任;以筆操觀之,則受生活之任;以山川觀之,則受胎骨之任;以皴觀之,則受畫變之任。以滄海觀之,則受天地之任;以坳堂觀之,則受須臾之任;以無為觀之,則受有為之任;以一畫觀之,則受萬畫之任;以虛腕觀之,則受穎脫之任。”此段以九對“受任”來探討筆墨各方面的問題。
首先,“墨運”“筆操”乃指運墨、操筆,都是從筆墨上進行概括,其意乃是表達蒙養之于運墨、生活之于操筆。其次“以山川觀之,則受胎骨之任”,是指山川是自然的脫胎換骨,但山水畫創作需要表現出“胎骨”,即不能空有其形,而須將山川之質與飾相結合。“以皴觀之,則受畫變之任”,皴是作為一種技法,其呈現的形態多種多樣,從皴法來看,山水畫將“畫變”呈現出來,即將大自然中生機勃勃的精神表現出來。“以滄海觀之,則受天地之任”,此句給人以廣大曠遠之感,展現出海天蒼茫、天地遼闊的景象,而“以坳堂觀之,則受須臾之任”乃是表達時光荏苒之意。“以無為觀之,則受有為之任”,其意指畫家須無為不作,無為所以有為,故畫家無為是因為有為的大任被其所承擔。“以一畫觀之,則受萬畫之任”,為什么歸于一畫,是因為畫家承擔著表現天地的大任。“以虛腕觀之,則受穎脫之任”,其意乃是指繪畫時須虛腕,注意其神明的變化,正同《運腕》章云:“腕若虛靈,畫能折變。”
石濤在實踐中將受天地之任落實到創作中去。他指出,畫家需要將天地蒙養生活精神呈現出來,在創作上需要擔當,需要立足于堅實的立腳點。這些都來自一畫,歸于無為。根據詳細的創作手法,畫家應將山川精神作為最終目的。石濤還從宏觀、微觀角度來探討蒙養生活之大任,談到如何在創作中落實表達的意義。
二、山水:自任其任
山水之任:“周游環抱有由,則山水之任息矣。”“山水之任”,討論了三個方面的問題,首先是山之任,其次是水之任,最后是山水“互任”。
山之任:“此山受天之任而任,非山受任以任天也。”此處石濤想表達的是,天雖然賦予山獨特的特點,但這并不表示山要因此服務或受限于天。他想強調山本體精神,這歸于自任。若將之延伸至人,人存在于規章中以及遵守此規章的內在本性是來自天的,這些都需要通過將山水的審美理想和道德理想合二為一來予以資養。山水不僅是一個自然空間的呈現,而且是蘊含著人思想意識及其理想追求的一個實體。創作者選取此作為對象,重在找到天地之間內在的精神所在,在山水之間找到自我的價值,以此將藝術與人性統一。
水之任:“水非無為而無任之也。”山受天之任而任,水亦如此。其水受天之任有“汪洋廣澤”“卑下循禮”“潮汐不息”“決行激越”“瀠洄平一”“盈遠通達”“沁泓鮮潔”以及“折旋朝東”。水的“德”“義”“道”“勇”“法”“察”“善”“志”,都是“素行其任”的見證。由于資稟的資養,故水呈現“周天下之山川,通天下之血脈”的生機與活力。
山水之任,在總體上是互補的,也是互動的。石濤說:“非山之任,不足以見天下之廣;非水之任……則周流環抱無由,則山水之任息矣。”即沒有山的作用不顯世界的遼闊,沒有水的作用不著世界的廣大。沒有山的靜,不見水之周流;沒有水之動,不顯山之環抱。山環抱著水,而水周游著山,表達的是山與水互任,呈現出周流、環抱之勢,讓生命間彼此相融,以至“山水之任息矣”,即讓一切在互任中滋長。此乃山水自然本身的“客觀性”,也是蒙養生活的安頓處。
三、繪畫:山水之任
“吾人之任山水也,任不在廣,則任其可制;任不在多,則任其可易。”
從現象客體來說,作為畫家所師法的對象,自然造化是無限的,它有其自身的統一性以及在中國文化傳統視野中特有的人文特征。在繪畫中要充分體現造化的無限生命精神和人文特征。這樣,石濤使繪畫深深地植根于自然造化的泥土中,奠定了繪畫通天地、怡性情的本體論基礎。
從繪畫主體來說,一方面要“受”自然的生命形式,以體驗、領悟的方式對待造化,它體現為藝術家的“意圖”;另一方面要“識”繪畫的基本技術,它是中國文化傳統中和天地交通的程式和方式,有其自身的獨立性和接受的普遍性,它意味著公眾的藝術世界的價值。
從繪畫本身來說,雖然繪畫的形式語言、筆墨技法有其獨立性,但必須在操作自由的前提下力求變化和創新。因為繪畫不僅是對生活的美化和對環境的裝飾,而且是對生命新感受的表達,是實現個人的生命情思和對象的形式意味的“視界融合”,通過“解蔽”的方式,不斷體驗把對象從實用的關聯中“孤立”出來的情味,用自然的詩意和神性溫暖塵俗中人的靈魂。最后作品的藝術氣息就是通過主體和客體、操作和審美、“我”和天地這三對的統一來實現的。
四、主體:是任也,是有其資也
任不在廣,任其可制,任其可易,人不能企圖表現一切東西,只能表現那些可以控制和變易的東西,也就是變成自己可以表現的東西。這里是藝術活動的對象性問題和對象的表現潛力問題,也即客觀見之以主觀的問題以及納萬物于主體的問題。此處主體性是指通過選擇及改變對象來完成。
任不在山水,創作山水畫,并非面面俱到地將山水形象描繪出來,而是在于通過畫家有意識的提煉取舍抓住其本質特征以及精粹之所在。抓住了本質、精粹的特征,就能夠以簡馭繁、以一總萬。石濤說:“吾人之任山水也,任不在廣……則任其可靜任不在水,則任其可動。”山水精粹是其內在的生命,所以,畫家不是以外在的形式,而是以內在的精神和生命為描寫對象。這就避免了藝術創作的“匠氣”,而能夠使之通向人的精神世界。
任不在筆墨,石濤說:“任不在筆,則任其可傳;任不在墨……任不在古,則任其無荒;任不在今,則任其無障。”即畫家的目的不是致力于獲得運筆的單純技巧,而是著力于表現山水的意趣神態;亦非是獲得運墨的技法,而是對山水內在生命的呈現;并非是對名畫的臨摹,而是需要畫家擺脫傳統的束縛,從而使得作品得到不斷革新與提升。由此,也就能夠做到筆墨章法既有所繼承又有所創新,筆墨線條既寫出山水的形貌又寫出山水的內在生命力。這是因為致力于辯證地處理傳統與創新的關系、筆墨技巧和山水畫理的關系,從而避免了可能出現的片面性。
任不在古今,石濤托古人以述藝術創造自由的理想:“古之人寄興于筆墨,假道于山川……載之寰宇,已受山川之質也。”即古人寄情于筆墨,抒發志趣于山水,以超脫的心態對待變動不居的現實,以順乎自然的心態專注于藝術創作,他們找到了天地之變化以及山川之內在本質,因此得到藝術成功之道。
任不在圣人,石濤說:“然則此任者,誠蒙養生活之理……是任也,是有其資也。”畫家對蒙養生活之理應有系統全面的認識,同時深刻把握“一畫”之法,對于萬物歸于“一畫”進行深入剖析。
五、結論
藝術創作的自由在于,不是致力于眼前一山一水的形貌描寫,不是致力于筆墨技巧的簡單掌握,不是致力于模擬古今名作的惟妙惟肖,不是致力于獲得“畫圣”的廉價桂冠,而是致力于寫山水本質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畫家既通自然山川之精神,又悉操筆運墨之技巧,如此方能實現對現象客體的包容和超越。
同時創作者的能力不是來自“山”的能力,不是來自“水”的能力,不是來自“筆墨”的能力,不是來自“古今”的能力,更不是來自“圣人”的能力。藝術家的能力,是來自他自身的資質,貫通古今、自成一格才是藝術家最終的資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