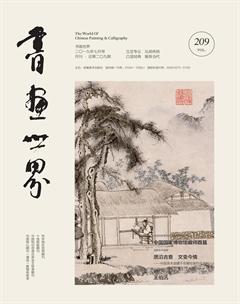澳門美術研究綜述
王霞霞
內容提要:筆者通過對“澳門美術”相關關鍵詞進行搜索,并到澳門本地公共圖書館進行館藏書籍查詢,對澳門美術研究成果進行整理歸納,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對比分析。從錢納利、高劍父到繆鵬飛,一批美術家對澳門美術發展做出了貢獻。國內學者通過對澳門美術起源、美術家流寓到創作風格交融的研究,展示了澳門美術作為中西方文化藝術傳播重要渠道的獨特魅力。同時,在對比分析中,筆者發現研究的差異性,一并提出并希望得到專家學者的準確考證。
關鍵詞:澳門美術;研究綜述;錢納利;高劍父
一、澳門美術的研究歷史背景
從16世紀中葉開始,中西文化在澳門交匯,歷經400多年的碰撞、過渡、融合而形成的澳門文化,是以中華文化為主體、中葡文化交匯、多元共存的文化,是東西方文明的結晶、歷史的見證。葡萄牙人進入澳門,帶來了文藝復興后的歐洲美術。伴隨《圣經》的印刷和普及,西畫以最易于流行的方式滲透到最基層的民眾之中。大眾傳媒的圖像文本與獨具風格特征的創作教學活動,分別從兩方面帶動了中國近代美術的變革,不僅奠定了澳門在中國近代美術史上的地位,而且奠定了澳門主流美術形態發展的基礎,如版畫、油畫、水彩與速寫。
1757年,清政府關閉全國對外通商口岸,只允許廣州對外貿易。許多外國商旅漸漸集結于澳門、廣州地區。當時有一批西方畫家經澳門進入內地,其間創作了較多素描、水彩和油畫作品,大多是以澳門、珠江三角洲和中國沿岸的地方風貌為題材,帶有紀游性質。他們的畫作被制成各類版畫廣泛印行,成為西方人了解東方風物的視覺媒介。
抗日戰爭期間,廣東及香港先后淪陷,一批嶺南美術家避居澳門,澳門的文藝氣氛頓然濃厚起來。嶺南畫派畫家的美術活動和富有時代氣息、思想性、戰斗性的創作不僅繁榮了澳門畫壇,使澳門成了他們進行抗戰美術創作、中國畫創新與展示的基地和大本營,也使澳門成為中國“新國畫”的重鎮,成為嶺南畫派強盛、人才脫穎而出的一方沃土。
20世紀以來,對澳門美術史研究的學者先后有本澳葡人文第士、高美士、文德泉神父;抗戰時期來澳的有高劍父、黃蘊玉;近20年來有徐新、陳繼春;內地有鄭工、莫小也等。他們對澳門美術史的研究有很大的貢獻,在學術研究方面以及對推動澳門美術史的發展具有積極的意義。
二、澳門美術的研究進展
(一)澳門美術家“流寓”現象研究
澳門美術具有很多特殊性。澳門既是歐洲藝術最早傳入地和中國西洋風格繪畫的發源地,也是西方耶穌會士畫家、西方外交使團隨行畫家的必經之地以及西方環球旅行畫家、地志畫家向往的東方熱土。因其特色性,美術家“流寓”現象就成為澳門美術的特殊現象。所有對澳門美術及澳門畫家的研究都無法脫離對“流寓”現象的研究。這種流寓的碰撞才使得澳門美術變得異彩紛呈。其中以莫小也《澳門美術史上的“流寓”現象探討》研究最為深入。另外,鄭工《邊緣上的行走—澳門美術》、陳繼春《濠江畫人掇錄》、吳方洲和陳炳輝《19世紀以來澳門美術歷程》、盛恩養《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美術》等都有提到澳門美術家的“流寓”現象。
莫小也認為澳門的流寓畫家主要分三種情況:第一種是途經澳門的,如1680年,清初著名畫家吳歷欲與柏應理赴羅馬,住澳門三巴寺半載,學教會會規,卻沒有在澳門作畫的實證;第二種是短暫寓居并為作畫而來,除西洋畫家之外,還有張大千、徐悲鴻等人流寓澳門并作畫;第三種就是有相當長時間的定居者,如錢納利、高劍父、鄭錦等人,最后在澳門逝世。
對于吳歷的流寓情況,鄭工有不同的解釋。他提出,吳歷在澳門前后三年,1681年作畫最多,有畫跋,亦見其詩集《三巴集》。畫作多見山水。吳歷旅澳,以畫表達某種心情。吳歷在澳門的作品,還是文人畫的路子,畫山水、竹梅。17世紀,圣像畫通過各種渠道從海外源源不斷地傳入澳門。吳歷身在基督教會,是否畫過圣像畫未見文獻著錄。
1939年后,高劍父及其弟子與其他嶺南的優秀畫家流寓澳門,如廣州春睡畫院的弟子司徒奇、何磊、關山月、方人定紛紛抵澳。陳樹人、楊善深、李研山等嶺南書畫名流也把澳門作為避風港。他們舉辦畫展,收授門徒,培養了澳門第一代的中國畫家,也培育了澳門現代中國畫發展的人文環境和社會基礎。
1987年,馬若龍、繆鵬飛、吳衛鳴等人籌辦澳門文化體·現代畫會,將人們的關注從抽象的形式轉到文化的問題,在澳門美術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20世紀80年代,澳門面臨著新一輪的移民浪潮,澳門的現代美術人員構成也出現新的變化。從海外移民澳門的現代藝術家,較早有琥茹,后來有澳大利亞人馬維斯等。隨著澳門與內地畫家的交流增多,創作空間變換也越來越快。
(二)澳門美術代表畫家研究
1.喬治·錢納利與澳門
1825年抵達澳門并終老于此的英國畫家喬治·錢納利(George Chinnery,1774-1852),被視為19世紀在東方最有影響力的西洋畫家。對錢納利的研究較多,1995年澳門基金會出版的陳繼春著述的《錢納利與澳門》一書,是第一本詳細介紹錢納利生平的中文書,不同于其他十多位學者出版的錢納利著作的英文或葡文版。陳繼春從錢納利出生的英國,到流經的印度,再到定居的中國澳門,詳細介紹了錢納利的創作經歷及作品流向。另外,胡光華《錢納利與19世紀中西繪畫的交流》、莫小也《錢納利與中國早期水彩畫》等文章也對錢納利的生平、繪畫創作風格以及藝術成就做了深入研究。
28歲的錢納利來到東方,此時期錢納利的繪畫技巧尚未形成其個人風格,技巧尚未成熟,畫作中有學院式的習作之感,類似荷蘭畫家的表現模式。在澳門時期,外在環境的穩定使得他能全心全意地投入藝術創作。他筆下的人物,已經不是對“固有形象”的描繪,而是進入了對“應有形象”的階段。在構圖和色彩處理上,明顯異于其在印度時期,他以澳門社會生活為主,著重描繪人物的內心世界。
在澳門,錢納利的藝術成就突出地表現在他繪制了數以萬計的速寫和寫生稿。這些即時性、原創性的作品猶如19世紀前期澳門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生動地記錄了澳門千姿百態的社會生活。這些作品,不僅是優秀的畫作,還是述說歷史的極其珍貴的圖像文獻。錢納利對中西繪畫交流所做的突出貢獻,是他開拓了以粵、港、澳三地名勝古跡、地志風景等為主題的油畫、水彩畫,為澳門文化遺產的保護提供了真實而寶貴的資料。
2.高劍父與澳門
高劍父與澳門的關系以“就學”始,以“畫學”終,一遇戰亂,即避難澳門,澳門給予高劍父以人生的安全感,高劍父給予澳門以“澳門現代中國畫”之啟蒙。對高劍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是嶺南畫派研究,如馮伯衡《高劍父與嶺南畫派》、王堅《認識嶺南畫派》、陳繼春《高劍父與澳門》就對高劍父和嶺南畫派的藝術成就進行詳細探究;第二是對高劍父“折衷”思想的深入研究,以張繁文的研究最為透徹,陶小軍、楊心珉《從“折衷”到“現代” : 抗戰寓澳時期高劍父繪畫思想的嬗變》也對高劍父的“ 折衷” 思想進行了研究。
張繁文認為高劍父的“折衷”思想明顯分為三個階段,在其早、中、晚三個時期對“折衷中外、融合古今”的藝術實驗是不同的。他早期的創作和“折衷”思想具有明顯的移植性,表現為對日本、西方繪畫語言引進過多,與中國傳統繪畫融合得比較生硬;其中期創作實踐及“折衷”思想則表現為以中國語言為核心的融合,企圖熔各國繪畫于一爐;其晚期藝術則表現出向文人畫回歸的傾向。
高劍父的畫路很寬,風格多變,想法很多,但也存在著不變的因素,即畫面的構成意識和筆墨趣味。前者受“取景寫生”的影響,有西畫的因素也有院體的因素,但他將其演化為有意識的“布局”;后者受“狂禪之風”的影響,有文人的因素也有僧道的因素,但他將其外化為不拘一格的“筆墨”。澳門的高劍父確實很注重內心的感受,很注重書寫和表達,可我們只看到高劍父隨著心境變換著畫面,很少在同一畫面中看到兩種不同的心境與不同的技法風格。
3.繆鵬飛與澳門
繆鵬飛對澳門現代藝術的發展功不可沒,也有眾多學者對其進行研究,如莊文永、鄭工、李超、莫小也、殷雙喜等學者都對繆鵬飛的現代藝術貢獻進行了研究。
莊文永的《澳門現當代藝術概觀》指出,繆鵬飛在澳門現代藝術的發展過程中發揮著重大作用。繆鵬飛出生于上海,1982年移居澳門,之后與馬若龍等眾畫家共同創建澳門文化體·現代繪畫,“把藝術新潮引進澳門,并掀起了一股現代藝術之風”。繆鵬飛是以現代畫(抽象畫)的形式在澳門舉辦畫展的第一個中國人。賈梅士博物院院長江連浩這樣評價:“繆鵬飛,這位出生于上海的畫家,他的勇敢精神在于沖破澳門對于現代派的偏見。繆鵬飛的作品體現出感情上和形式上的成熟,這與他本人的文化背景有關,使他成為澳門現代畫的柱石之一。”繆鵬飛將自己的藝術開拓稱為“新東方主義”,主要表現為對于東方文化的尊重和理解。雖然繆鵬飛抽象藝術在當時是極具前衛性的,但是他的作品仍然包含著巨大的中華傳統文化的豐富內容。
鄭工卻認為,與其說澳門的現代美術是繆鵬飛帶動的,毋寧說是內地現代藝術的實驗浪潮波及了澳門地區。在1985年12月繆鵬飛舉行畫展之前,路易斯·迪美個人回顧展就展示了這位澳門土生葡人從澳門碼頭、漁船的寫實風景到理性的抽象幾何結構,又從抽象的結構布局返回寫實圖像的轉變過程,所以澳門人將“澳門現代繪畫的先驅”這一桂冠贈予路易斯·迪美。
除上述畫家外,利瑪竇、鄧芬、杜連玉、江連浩、馬若龍、吳衛鳴、郭恒等一批有影響力的畫家對澳門美術都產生了一定影響。
三、澳門美術的研究展望
澳門美術沒有太濃的“仿古”風氣,卻有面向現實生活的繪畫傳統,從錢納利到高劍父,帶給澳門的都是“寫生”的概念,而高劍父及鄧芬、司徒奇等人同時開啟了澳門畫家“寫意”的心靈之窗。于是我們看到了20世紀50-70年代處在傳統和現代變革中的澳門美術,看到80年代澳門現代美術的形式觀念,看到90年代后澳門新生代的出現。
文章通過梳理當下現有澳門美術研究成果,對其進行歸納、整理,發現在研究實證方面存在一定差異。澳門作為東西方文化的集合地以及戰爭時期的避難所,為藝術家們提供了創作思路和交流空間。澳門美術根本屬于移植文化類型,但也存在本土的生成問題—在外來的各種文化交匯融合中,澳門美術逐漸在這塊土地上沉淀并形成本土現象。土生的葡人畫家和本地的畫家社團成為我們關注澳門美術“本土現象”的兩個基本點。對于外來傳教士和流寓畫家的研究已經開始,未來可以繼續深入探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要把握繪畫考證的準確性,尤其是一些尚未確定的畫家作品及其創作背景。除此之外,未來研究學者可以在澳門本土美術現象與澳門宗教美術方面繼續進行深入研究,澳門美術對于我們理解東西方藝術交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同時為我們深入了解澳門歷史提供重要的研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