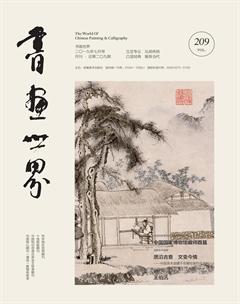論明清時期徽派篆刻藝術傳統的確立和發展
楊潔
內容提要:明清時期徽派篆刻藝術取得長足發展,在中國篆刻史上譜寫了華美的新篇章。徽派篆刻的發展大致經歷了明萬歷至崇禎時期的徽派篆刻確立階段,這一階段徽派篆刻注重技法,由“崇古”而確立“以刀代筆”的徽派篆刻傳統。隨后,自清初至道光時期是徽派篆刻的發展階段。這一階段以鄧石如的“印從書出”為代表的新徽派篆刻出現,彰顯了博采眾長、獨樹一幟的徽派新印風。考察徽派篆刻藝術的發展歷程,對于研究徽派篆刻傳統在中國篆刻歷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徽派篆刻;藝術傳統;確立和發展
中國篆刻藝術的歷史源遠流長,歷經數千年的發展演變,在各個時期都曾顯示出不同的藝術風貌。研究中國篆刻發展演變的歷史,涉及書法觀念的變化以及社會思潮、美學風氣等因素。徽派篆刻藝術在明清時期達到鼎盛,涌現出一大批卓有成就的篆刻大家,而且形成獨具特色的徽派篆刻傳統。研究徽派篆刻藝術的發展演變,對于整個中國篆刻藝術的發展也是一個很好的促進。
徽派篆刻的藝術成就集中體現了中國篆刻藝術的特點:一是篆法效果和金石技法的結合;二是篆刻藝術不斷向書法藝術靠攏,體現出書法藝術的高妙境界。
一、由“崇古”理念演化出的“以刀代筆”的篆刻傳統
徽派篆刻的“崇古”思想主要體現在尊崇秦漢篆刻的意趣率真特點上。秦代作為中國印章發展的轉折時期,其形成與發展是與秦漢時期漢字的演變進化密不可分的。漢字發展到了秦代,形成了新的結構體勢,經李斯等人的規范化整理,小篆成為漢字的主流,秦印的風格與小篆的興起是密不可分的。秦代以印章刻石為代表的秦代銘刻傳統引導印章文字走向平整莊重,一改戰國時期奇詭的面貌。秦印的體制經過官印與民間藝術的融合表現出率真、自然的拙樸之美。這正是中國書法和印章藝術共有的審美傳統。秦漢時期的印章由于采取于印坯鑿刻文字的工藝,形成了“屋漏痕”的線條。這與中國書法的含蓄蘊藉的用筆又是暗合的。漢代印章早期沿襲秦印的遺風,到東漢以后,隨著漢字逐步規范化,印章風格轉向端嚴寬博的審美傾向,這對后世篆刻的風格有重要影響。
徽派篆刻早期形成的“崇古”理念主要體現在對印章的樣式和篆刻技法的繼承和發展。徽派文化博大精深,徽派文人具有精深的文化造詣,對于古法的傳承顯示了徽派篆刻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血脈緊密相連,同時也說明徽派篆刻在藝術上一直遵守著較為純正的中國篆刻大道。以徽派篆刻的早期代表人物何震為例,他自幼精研六書,對秦代的石刻藝術有著精深的造詣。他曾說道:“下筆如下營,審字如審敵,對篆如對壘,臨刻如臨敵。”何震的古文字修養和對篆刻古法的繼承形成了他剛健有力、方圓并施的藝術風格。何震堪稱徽派早期篆刻的奠基者,正是在他的啟發下,徽派篆刻才在不斷繼承和發展中形成了自身傳統。何震的后繼者有程邃、巴慰祖、胡唐、汪關,合稱“皖四家”,其中以巴慰祖的成就最大。“皖四家”可以視作明清徽派篆刻雛形階段的代表人物,真正的徽派篆刻群體形成應該以巴慰祖和胡唐等人形成的“歙派”為標志;歙派的中堅人物是清乾隆時期的巴慰祖。巴慰祖在藝術上師承多家,在年輕時曾大量摹刻古印,風格上更為淳樸、規范,法度嚴謹而又內涵深厚。巴慰祖在技法上采用程邃的雙刀沖刻,豐厚內斂,在印章形制上更為典雅細潤,刀法流暢。巴慰祖的外甥胡唐將巴慰祖的技法更加精致化。胡唐沿用漢印的諸多精華,筆法細膩,印章視覺效果精美絕倫。徽派篆刻的早期成就顯示了徽派篆刻立足傳統、取法乎上的高雅氣質和超凡追求,這對于后期徽派篆刻的發展和突破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以鄧石如為代表的“印從書出”的徽派新印風
鄧石如是后期徽派篆刻的代表人物,也是將徽派篆刻藝術進一步發揚光大的中堅力量。鄧石如的人生歷程和篆刻藝術為徽派新風格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絕佳的研究范本。鄧石如可以看作是從徽派篆刻傳統中突圍出來并獨樹一幟的新徽派篆刻的一代大家。鄧石如出生于安徽懷寧,一生清貧,癡迷于中國書法和篆刻藝術。他早年對李斯的書法、何震的印章極為推崇,特別在篆書的體勢和線條變化上有很深的造詣。后來,鄧石如在多年精研篆刻藝術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種意趣為先的藝術風格。
“鄧石如的理論和創作實踐突破了當時書壇、印壇的所謂正統樊籠,以石破天驚的面貌,開拓了新的境界。”鄧石如開創了中國篆刻藝術的新天地。他有效地將書法與篆刻藝術相結合,改變了篆刻藝術一直以來被書法界視為“小道”的不利局面。而且鄧石如的最大貢獻在于,他的篆刻藝術形成了全新的藝術理念,其核心思想就是“印從書出”。
魏錫曾對鄧石如的篆刻評價道:“印從書出,書從印入。”這一評價精準地概括了鄧石如篆刻藝術的藝術特征。鄧石如的書法與篆刻藝術在旨趣和造詣上一脈相承。這在以往的篆刻家身上是很難看到的。鄧石如的印章很好地解決了一直以來“篆”與“刻”的矛盾,他將篆書這一文字載體在線條和造型上的書法特點與金石刻制技法完美地統一。自秦漢以來,篆刻家一直孜孜以求的是要將篆刻的刻法痕跡不斷去掉,以達到書法技法上圓融含蓄的境界。鄧石如的篆刻藝術開創了一個獨特的“鄧派”傳統。對于這一傳統,有研究者這樣寫道:“鄧石如篆刻在徽派的基礎上,參以秦權、詔版,又結合了他流利雄健的篆書,形成了剛健婀娜、大氣磅礴的氣概,成為一個新的流派—‘鄧派。至此,篆刻理論家以書法入印的理想得以實現。”
以鄧石如的具體作品為例來論證“以書如印”的藝術風貌,可以分明地看出鄧派篆刻的獨特之處。現藏于西泠印社的《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印是鄧石如印章中的精品,集中反映了他驅刀如筆、強調書意表達的創作思路。下刀之處輕淺流暢,注重刀法的動態美感和言外之意。此印將中國書法的計白當黑、奇趣乃出的藝術特色表現無遺。
鄧石如45歲時曾作《我書意造本無法》印章,此印文字在方圓結體和筆法走勢上集中體現出鄧石如在篆書上的高超成就。鄧石如的篆刻將中國書法藝術乃至繪畫的諸多藝術手法融會其中,藝術成就嘆為觀止。鄧石如曾有一方題為“鐵鉤鎖”的印章,此印也能窺見鄧派篆刻的藝術創新。“鐵鉤鎖原是中國畫用筆的一種技法,筆勢往來,如用鐵絲糾纏。”本為繪畫技法,卻為鄧派篆刻所用,其中奧妙在于中國傳統藝術書畫同源的理論。據說,柳公權正是用此技法使得柳體字剛勁有力、結體緊湊,而鄧石如在篆刻上對此技的使用進行探索并取得成功。
有論者對鄧石如的《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印進行“鐵鉤鎖”視角下的闡釋,別開生面。“江、岸、千、尺等字筆畫較少,顯得疏朗;流、聲、斷三字筆畫多,顯得茂密。為了保持對稱,有的字在字形上做了適當處理,使全印顯得和諧統一,且每行四字之間均各有穿插,兩行字間又互相呼應,全印緊湊不松散。在線質上,筆畫少的字厚重樸實,筆畫多的字纖細秀美。與之呼應的邊線則是右行字的筆畫較繁,邊線厚實;左行字的筆畫較少,邊線虛靈,粗細相間,對比協調。其中左上角的斷字殘損與右下角的邊線殘破更耐人尋味,斷字的殘破能在其點畫雷同過多時得到一種釋放,而且殘損自然,并無造作之意。右下角邊線的殘缺正好位于聲字右側,其中‘殳的末筆與邊線相連,殘破剛好落于此處,宛如一條蜿蜒的小河緩緩流向大海。”鄧派篆刻與書法的關系通過該精彩解讀可見一斑。
徽派篆刻在明清的崛起既是對秦漢以來篆刻古法的繼承,又是以鄧石如為代表的集大成者們不斷創新、不斷精研的結果。徽派篆刻傳統在明清時代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這一方面是中國篆刻歷經數代發展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徽派文化博大精深、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文化氣息造成的。在今天大力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打造區域文化品牌的時代背景下,重新解讀并認識徽派篆刻藝術的歷史傳承和高妙成就,對于促進文化繁榮,傳承優秀文化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