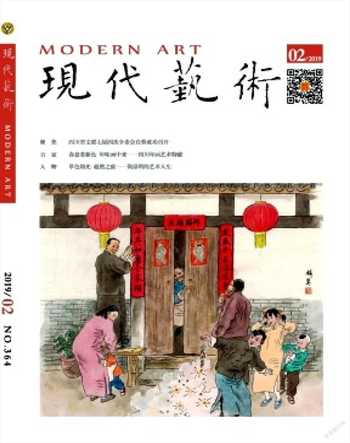半世浮萍隨逝水
羅仆世
全世界都知道梵高是著名藝術家,除了他自己。
晃動拙筆之前,我將自己整個浸入黃家駒名曲《海闊天空》中,試圖以渺小生命去參透被苦難和信仰浸泡的大師靈魂,像螢火蟲努力仰望星辰的光亮。
太多人品評過他,如果列成名單組成隊,可以從湘鄉(xiāng)排到荷蘭。我鼓搗著肚子里有限的藏貨,行文時仍然感到言辭左右支拙。
閱讀梵高有三類境界。第一境界是門外漢、反對派和有密集恐懼癥的人——“這次第,怎一個亂字了得!”;第二境界是隔岸觀火的打醬油畫手——“雖然不知道好在哪里,但是,看起來很厲害的樣子。”;“第三類境界是后印象派信徒和梵高死忠粉——“別人笑你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
鐘愛黑白,是我小小的偏執(zhí)。那樣漫天翻滾厚不透氣的色彩,像一鍋燒得滾燙的地溝油,看得人蛋疼無比。年歲漸長,多少年獨自在成長路上打拼,卻每每被現實的南墻撞得頭破血流。再觀梵高,竟毫無征兆地,被紙背滲透出的無可言說的狂熱激情和深刻孤獨感所折服,這個精神異常、受理想和藥物刺激太深的男人,喜歡用濃烈亢奮的色彩來釋放找不到缺口的靈魂。想想自己是否已被平庸所俘虜、被潮流所挾持、被挫敗所擊倒,再回過頭來看那些畫作,就能夠觸摸那些魔幻的色彩、不羈的線條和畫家高貴而狂亂的心靈。那是靈魂無法突破的孤獨,是壯志未酬而又壯心不滅的不甘。就像那朵拼命仰望太陽、即使被藝術灼傷也從不轉向的向日葵。
漂泊江湖君莫問,天涯游子本無根。生活在低處,靈魂在高處,這就是梵高。歷史以琥珀的形式保存了他的樣貌。苦大仇深的招牌表情,油煙氣十足的裝扮,極易使人聯想到半個月沒換衣服的市井人。
人的悲劇大體可歸為兩類:你與這個世界太相同,或,你與這個世界太不同。結果是,“一個人如果遵照他的內心去活著,他要么成為一個瘋子,要么成為一個傳奇。”
年輕的時候,他是一名有為青年。出生于顯赫的藝術家族,有著全歐洲最好的畫廊,本可以悠閑地當個富二代,卻偏偏劍走偏鋒。他的背后有一個偉大的男人,那個文藝史上最有名的兄控,每次梵高被自己的熱情整得不成人形時,總會在第一時間感知他的歡欣和落寞。
畢加索早就斷言:“這人如不是瘋子,就是我們當中最出色的。”這個餓幾天肚子也不能不畫畫的信徒,畢生流浪,除了弟弟,親人都排斥他,其畫在有生之年只賣掉過一幅。沒有人知道,他到底是在浪費顏料,還是在創(chuàng)造歷史。
這個極端個性化、辨識度最高的藝術家,摒棄了一切后天所習,漠視學院派那些循規(guī)蹈矩的教條,充分代表了印象派咄咄逼人、包裹萬物、吞吐天地的大氣,且更具明亮、想象和熱情,油彩像被擠壓的靈魂,又像混亂的手指,因為無法抓住空虛而扭曲。
那是一場視覺革命,所有色彩并非各就各位、各行其是,那是一副放任自流的模樣。原生顏色取代了傳統藝術家對整體色調的依賴,在永遠的暴露與隱匿、靜止與運動以及色彩與精神之間發(fā)現了一條神秘的甬道。那灼灼其華的色彩,以自發(fā)、奔放的方式融合,涌動著無規(guī)可循的線段,畫家內心的張揚恣肆甚至劍拔弩張撲面而來。
他初期的繪畫風格充滿對勞動人民的體恤和尊敬。《吃土豆的人》一臉漠然,露出在梵高臉上永遠不會出現的安于生存不求生活的表情。無處不在的斑駁,像墻面剝落的破舊屋舍,每一滴顏料都藏著他靈魂的碎片。
最后幾年中,他的創(chuàng)作達到巔峰。仿佛一個生命垂危的人,急于在臨死前說出所有的話。著名的《星空》以藍和黑暗示長期壓抑扭曲的心理,再用明黃色的大片繁星映射出遙不可及的希望與夢想。那極具運動感的、連續(xù)不斷的、波浪般急速流動的筆觸,樹木、天空、山脈甚至空氣,都發(fā)瘋般地扭曲變形,將被一個深不可測的漩渦吸進去。放大的星宿仿佛無數神靈俯窺大地,閃射著火一樣的瞳仁。那里有強烈的生命在蠕動,動靜隨性,張馳無度。從靜謐的星空到凝然不動的大地,都潛藏著爆炸般的巨能。
他邀請高來阿爾同住同創(chuàng)作,兩位“雞血哥”在“黃色小屋”中屁顛屁顛地創(chuàng)作了一屋子的畫。合作的名畫《阿爾的舞廳》,意在給世界留下“一份新藝術的遺言”。搶眼的金黃,詭異的靛藍,色彩純粹,氣氛熱鬧,追求“色彩的音樂”或“象征主義的詩意”,強烈的反差讓空間具有飽和感,烘托出莫可名狀的不安而又充滿迷幻未知的美。
他們像閃電一樣撞在一起,又像同極電磁一樣排斥對峙,不斷地鬧別扭。高更終于悟出“不要和神經病吵架,否則人們會搞不清誰是神經病”的真理,咱不玩了,你愛咋地咋地!甩手要走。梵高便上演了藝術史上最著名的“一哭二鬧三上吊”的橋段。無辜的耳朵被斬斷,寄給據說是心上人的妓女。然后……就沒有然后了。那枚著名的耳朵和它的主人一起名垂青史,至今也沒有失去聽覺,化身主人藝術和人生的聽診器,收集著后人的莫衷一是。
“也許我的靈魂中有一團烈火,但沒有一個人前來取暖。”可憐人說。
《烏鴉群飛的麥田》是他的絕響。凌亂低飛的烏鴉、波動起伏的地平線和狂暴跳動的激蕩筆觸,暗流洶涌,百般不安,營造出幾乎要溢出紙外的壓迫感、反抗感和絕望感。第二天,他來到這塊麥田對著自己開了一槍。
他的生命像放完電的電池枯竭了。對于星宿般的藝術生命而言,他微塵般的自然生命,是臨產前撕心裂肺的陣痛。正如泰戈爾所說:“熾烈的火焰對自己說,這是我的死亡,也是我的花朵。”也印證了他自己的斷言:“創(chuàng)造新東西的藝術家,都會遭到嘲笑,并且被當做精神病看待,藝術家無法忍受冷酷的環(huán)境,最后就會走上毀滅的悲劇。”
我總會不自覺地拿梵高跟尼采并列,在我看來,他們最大的共同點不是都瘋了,而是都在最后幾年里實現了生命的突圍。并借著死亡,直逼天上的星辰。
他是輕音樂陣營中的搖滾樂手。梵高所處的時代,學院派仍是主流,印象派作為前衛(wèi)流派尚未被主流接受,更別說后印象派了。不是時代拋棄了他,而是他跑得太快拋棄了那個時代。“相識滿天下,知己能幾人”這實在是所有天才的悲哀。追日的前行者,懷揣血液一樣滾燙的信仰,執(zhí)著而熱烈地探求后印象派發(fā)展之路,并且孤軍深入,即使無處可逃,仍然拒絕被世俗招安。付出青春與未來,收獲絕望與不朽。
“在藝術作品中,最富有意義的部分即是技巧以外的個性(林語堂)”。他和高更、塞尚等后印象派組成的美壇星座,折射出新銳藝術的靈光,從而在繪畫各類領域全面開花,梵高便是其中的北辰。他不只追求光與色的瞬間印象,在印象畫派只重光色不重形象的觀念基礎上,除了對自然光影和色彩的捕捉,更注重于畫面的表現性及繪畫的感受,色彩成為傳遞情緒的語言,凸顯包羅萬象的象征意義。藝術家洶涌的激情,是鞘不住的劍氣,最終噴薄而出,直到把讀者也燒得澎湃起來。
后人對梵高的理解總是過于感性。比起在意他飛得高不高,我更心疼他飛得累不累。他本可以先生存、再生活的。無論精神疾病還是自裁都是他和自己擰巴的結果,由此還引發(fā)了弟弟半年后憂傷過度去世的次生災難。任何摧殘生命的行為都不值得同情和救贖,不論是流著鼻涕的智障,還是傾倒眾生的藝術家。
世界于他,是幅被畫壞的習作。“何必為部分生活而哭泣,君不見全部人生都催人淚下(塞內加)”。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大家都沒有去死,為什么偏偏你要去死?
一言敝之梵高一生,竟是:要么畫!要么死!
無論如何,世界是值得擁抱的。高更說得對:“除了毒藥,還有解毒的藥。”
半世浮萍隨逝水——懷念色彩魔法師梵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