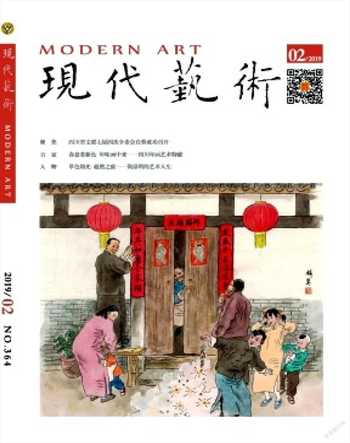石真先生的筆情墨意
木子
先生讓心靈游牧于自然山水之間,頓悟其間無限禪意,大自然的饋贈賦予了筆墨溫度。先生的山水作品雅麗而有文采,簡約的構成、灑脫的筆墨、靈動的線條、詩化的氛圍,構成了他的繪畫語式,正是因為有著老師不倦的教誨和淡泊寧靜的心態,從而鑄就了先生詩般的意境。
國畫,作為一門民族藝術,深深扎根于中華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中,擁有著不同于西方繪畫的獨特意蘊,歷經數千年的傳承與發展,成為我們民族藝術的瑰寶,具有深刻的精神內涵和寶貴的文化價值。杰出的畫家猶如璀璨群星,在歷史的長河中閃耀著奪目的光芒,留下無數曠世杰作。而國畫藝術家水平的高低,卻并不僅僅取決于繪畫技法的高低,更重要的還在于國畫藝術家自身的國學修養。石真先生不斷地跬積而成心懷文,積累下功夫技法之外的深厚的國學修養。
石真先生師承石壺,也就是現代國畫大師陳子莊先生。說起二十世紀的四川畫壇,我們不得不提起陳子莊先生。時齊白石、黃賓虹入川,得以相晤,切磋畫藝,領受教益。眾所周知,石壺先生是中國近現代享譽世界的國畫大師,其成就在于寫西蜀山水之骨,融中華文化之魂,形神合一,為西蜀丘陵國畫寫意之開山鼻祖,成一代宗師,與徐悲鴻、張大千、齊白石等齊名,給中國美術史濃墨重彩地添上了一筆亮色。石真先生追隨石壺先生,朝夕相處,勤習苦練,盡得先生真傳。聞名不如見面,一次機會有幸采訪到先生,可謂是見面勝似聞名。
我們一行三人來到先生的工作室。印象中,書畫家們大都不修邊幅,工作室里也常是一片狼藉。止步于玻璃門前,等待鑰匙與鎖槽的成功契合,透過玻璃,一張偌大的會議桌搭建成的畫臺上,毛筆、宣紙、畫盤錯落有致。走進工作室,左邊的書柜、茶臺才現出全貌,一只茶壺呼嚕嚕鼓著清香。轉身,一整面墻上掛滿了畫,散發出淡雅的墨香,畫中煙波浩渺處,是云,亦或是縷縷茶香。先生喜歡貼近生活,更喜歡充滿田園野趣的巴山蜀水,先生謂之為“更能接近人們的生活情調”。觀先生的作品,在嵯峨峻嶺間,在陡然蒼巖下,在一泓秋水之上,粗細變化的墨線勾勒出山石模樣,花青著墨暈出遠處青山,筆法自然而多變化,而人跡則多以蜿蜒的臺階﹑房舍﹑寺院﹑樵夫﹑農人為表現對象,生動而鮮活的山居生活畫卷躍然紙上。無論是層巒疊嶂的山峰,還是田園野趣的山居生活,撲面而來的自然氣息,田園之樂,引人入勝,徘徊于先生的畫中,靜靜地聽自然講述生活中的美好故事。
先生提到,“作畫之前先讀書”是老師的教誨。唐岱于《繪事發微·讀書》中寫到:“胸中具上下千古之思,腕下具縱橫萬里之勢。立身畫外,存心畫中,潑墨揮毫,皆成天趣。讀書之功,焉可少哉!”“未知不學而能得其微妙者,未有不遵古法而自能超越名賢者。” 先生讓心靈游牧于自然山水之間,頓悟其間無限禪意,大自然的饋贈賦予了筆墨溫度。先生的山水作品雅麗而有文采,簡約的構成、灑脫的筆墨、靈動的線條、詩化的氛圍,構成了他的繪畫語式,正是因為有著老師不倦的教誨和淡泊寧靜的心態,從而鑄就了先生詩般的意境。歷史證明凡有成就的書法家、畫家沒有一位不是學問家的。越是中國傳統文化修養深厚的,越是能夠彰顯國畫水平的高度,最終進入化境。
先生為人豪爽、低調,對時事充滿不俗的看法。有幸聽他講述一番,實在是撥云睹日,催人深思。創作時他要求自己做到“三不昧”。一不昧:天地自然大道。遵循自然之法,自然之美;二不昧:人文祖宗傳承。中華民族深厚的傳統文化要代代相傳,作品中蘊含傳統;三不昧:自心。具有自己的藝術符號,無中生有,技法求精。石真乃先生名號,說起其中緣由,他表示:“‘石真’的含義就是實實在在,真真切切,讓筆墨成為靈魂的賦行,止于浮世,成于自然的止息。”如此看來,名副其實。
國畫之路,是一條曠日持久、生生不息的天地繪心之路。在這條長路上,有一位將傳統藝者與文人身份聚合的國畫藝術家。他身體力行地告訴我們學識修養對于創作有文化深意的作品的重要性,同時還展現出這種為天地立心的擔當, 恰逢其時地溫故與拓新,以精深的筆墨表現造化與心源統一的優秀作品,顯現出中國畫的時代之美。石真先生的國畫成就是新世紀的生命力和創造力,是骨髓和靈魂,是高明國畫藝術家的潛質與才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