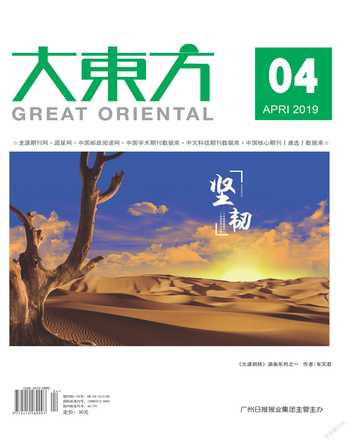西方‘詩’與‘藝術’的概念演變
金春燕
摘 要:西方‘詩’與‘藝術’概念的起源可以溯源到古希臘時期,其概念的形成和發展經歷了漫長而復雜的過程。本文介紹了西方代表文論家對‘詩’和‘藝術’概念的界定,追溯了‘詩’和‘藝術’概念的提出與發展,分析了兩者間的關系。
關鍵詞:西方;詩;藝術;技藝;概念
一、西方古典文論中‘詩’概念的變遷
古希臘時期,柏拉圖的《理想國》和亞里士多德的《詩學》是詩學發展史的重要文獻,推動了詩的發展。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將詩歌分為兩類:“一種是完全通過模仿,即悲劇或喜劇;另一種是詩人表達自己情感的,如酒神贊美歌”。對于第一種詩及詩人柏拉圖是持貶斥態度的。在柏拉圖看來,模仿與“和真理隔兩層的第三級事物相關”,認為這類靠模仿形成的詩是不具真實性并且有“縱容快樂和痛苦替代法律和理性”,從而“腐蝕最優秀人物”的惡果,因此他認為應該將其逐出理想國。而對于酒神頌歌、神靈附體的詩歌之類的第二種詩,他還是持著積極的態度。他認為詩是使人在神靈附體的情況下傳遞出來的神的話語,認為“文藝創作來自詩人的靈感,來自神力憑附時的一種迷狂沖動”,而非技藝可以習得,將詩藝與技藝區別開來。
而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將詩視為有規則的技藝的一部分,且認為詩是模仿的藝術,提出模仿是出于人的本能和天性,模仿的藝術不僅可以幫助人們求知,還可以給人帶來快感,將創造與模仿結合起來,肯定文藝的價值,肯定模仿藝術。
到了中世紀,詩長久地依附于語法學、修辭學、邏輯學與哲學中,仍然不被視作是一門獨立的學科。中世紀時期,詩作為語法課上常用的例子而出現,昆體良曾將語法學定義為:“正確言談的科學,詩人的學問”,維克托利努斯也在《論語法藝術》中把語法學定義為:“解讀詩人和歷史學家的科學”。在古代著作中,除亞里士多德《詩學》外,幾乎所有的批評作品都借助了修辭學的理論,如朗吉弩斯的《論崇高》,德美特里烏斯的《論風格》等都是當時典范的修辭學文本,賀拉斯的《詩藝》也得益于西塞羅的修辭學理論,可見當時的詩學與修辭學密不可分的聯系。而將詩與邏輯學相聯系早在古典主義晚期亞里士多德的評論者那里已經建立,而其后亞里士多德主義的復興,“詩是邏輯學的一部分”的觀點隨之產生。但這種說法其實是宣稱詩學是一種工具或才能,不具有內容;是技藝而不是科學;否定了寓教于樂的傳統,在當時也引起了爭論,到十六世紀,關于詩在科學中的位置也成為學者們爭論不休的話題。不同于詩與三學科的關聯,詩與四學科是處于相對獨立的位置,被視作哲學或神學的一支,也由此產生了中世紀批評的主要類型。
錫德尼的《為詩辯護》是文藝復興時期關于詩的論述的重要文本。錫德尼對詩歌本質和詩歌的社會功用進行了辯護,他堅持著創造性摹仿的詩學觀,強調詩的目的是“導致德行,怡悅性情”,從歷史起源上來追溯,通過詩與其他學科間的對比,確立了詩作為文化之源的不朽地位。錫德尼還將詩分為“模仿上帝的不可思議的美德的”、“屬于搞哲學的人們的”說教詩及“真正的詩”即為了教育和怡情從事模仿的詩。從錫德尼對于第三種詩歌的論述可以看出當時詩的概念已逐漸明晰,開始接近現代意義上的詩歌概念了。而對于詩歌怡情悅性和啟發德行的論述則在一定程度上承襲了古代以來一直流行的寓教于樂的詩學觀念。
到了康德《判斷力批判》中,康德將語言藝術分為演講術和詩藝,將詩藝定義為“把想象力的一種自由游戲作為知性的事務來實施的藝術”。康德認為詩人雖然宣告的只是一種娛樂性的理念游戲,卻可以促進知性的事物,且在一切美的藝術中,詩藝保持著至高無上的等級,同樣具有康德論及美的藝術時談及的藝術豐富性。
二、西方古典文論中‘藝術’概念的變遷
‘art’(藝術)一詞源于拉丁文‘ars’,而這一詞又可以追溯到希臘文的‘Τ?χνη’,用來表示技藝、技巧、技術等。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討論到城邦的建設及城邦統治者、護衛者所必須具備的品質正義時談到了一些關于技藝的看法,他認為醫學、烹調、軍事、制鞋等諸多方面都是技藝的一個層面。當時技藝的概念范圍十分廣泛,把音樂、繪畫、建筑乃至詩歌這些被后世認作是藝術的門類歸入了技藝中。而亞里士多德將知識分為理論、實踐與制作三類,其中制作可以說就是當時所說的技藝,而詩也屬于制作科學或技藝的范疇。這一時期,還沒有單獨的藝術概念,因為當時的人們還未能認識到兩者的區別,將科學、手工藝都與藝術聯系在一起。
“liberal arts”這一詞始于古羅馬時代,據目前所知這一概念最早由古羅馬時期的西塞羅提出,而瓦羅在其《學科九卷》中列舉九門自由藝術,與粗俗藝術相區分,但當時雕塑和繪畫卻不屬于在內。到了中世紀更加詳細地提出了“自由七藝”,以將其與所謂的機械藝術相區別,但這時的藝術仍然不同于現代人對于藝術的定義。
直到公元16世紀,藝術一直被認為是以規則為依據的生產3,仍然側重于技藝、實踐技巧等含義,但藝術的概念開始有了轉變。在深受人文主義思想的影響的意大利,迪賽諾概念被提出,將繪畫、雕塑以及建筑希納入自由藝術領域,與手工技藝相區分,但藝術還未能從科學之中分離出來。達芬奇在其《畫論》中試圖將繪畫與雕塑、詩歌等其他門類做比較,說明其優越性,并力圖證明繪畫是科學中的一部分,而非藝術的一部分。從達芬奇在其繪畫理論中大篇幅的講解透視、解剖、光影關系等就可看出在當時藝術與科學的界線并不明顯;而現代意義上的哲學觀念在文藝復興早期的定義也并不十分清晰,在達芬奇的時代,科學一詞還往往與自然哲學的觀念更為接近。
到了18世紀,巴圖將詩歌、繪畫、音樂、雕塑、舞蹈、建筑、修辭等納入“美的藝術”范疇中,“美的藝術”概念也被提出來4,而后萊辛、康德、席勒、黑格爾等人在此基礎上發展了美學觀點,完善了美學體系。18世紀中葉起,藝術從手工藝和科學中獨立出來,人們開始將‘美的藝術’稱為藝術。
康德在其《判斷力批判》中將藝術與科學、自然及手藝進行了區分以明晰其特點。他將藝術區分為審美的藝術和機械的藝術,又將審美的藝術分為快適藝術和美的藝術,并重點對美的藝術進行了界定。康德還進一步細分,將美的藝術分為語言的藝術、造型的藝術和藝術作為諸感覺的自由游戲。康德將藝術這個概念與美聯系在一起,大篇幅地闡述了美的藝術的相關概念,對美的藝術進行了分類,塑造了現代人對于藝術定義及內容的基本觀念,并強調了創作主體和審美主體的主體性對于藝術的重要意義。
三、西方古典文論中‘詩’與‘藝術’的關系
在柏拉圖的論述里,模仿的詩歌與技藝相關,而反映真實感情、來源于靈感的詩歌顯然是不同于屬于技藝的模仿詩歌。在《高爾吉亞》中,柏拉圖表示非理性的作品不能稱之為藝術。可以說柏拉圖由于對模仿的排斥,貶低了這類詩歌,也在一定程度上強調了真正被認可的詩與技藝的區別;亞里士多德則不然,他肯定了模仿是人類積極的天性,又論述了詩的模仿對象、媒介、方式等,可見他更為注重詩與技藝的相似之處,并肯定了詩作為技藝的一部分的觀點。
其實,亞里士多德為詩確立規則的《詩學》已暗示其將詩作為技藝的一部分的觀念,只是這種觀念長時期以來被遺忘。中世紀,詩一直被定位在與語法學、修辭學、邏輯學和哲學相關的位置上,不被視作是藝術的一部分,詩與藝術再次被區分開來。直至16世紀中葉,《詩學》在意大利被翻譯出版,引來大批模仿者,詩成為藝術中的一份子不再有疑問。
康德開始把詩歸入藝術門類中,并不再將其視作技藝。康德把詩藝視作美的藝術中的一種,比較了不同美的藝術的審美價值,并認為在一切美的藝術中,詩藝保持著至高無上的地位。
參考文獻
[1]柏拉圖.《理想國》[M].張竹明譯,商務印書館,1986
[2]達芬奇.《繪畫論》[M].戴勉譯,人民美術出版社,1979
[3]符·塔達基維奇.《西方美學概念史》[M].褚朔維譯,學苑出版社,1990
[4]康德.《判斷力批判》上卷[M].宗白華譯,商務印書館,1964
[5]錫德尼.《為詩辯護》[M].錢學熙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6]亞里士多德.《詩學》[M].陳中梅譯,商務印書館,2007
[7]張華,中世紀文學批評的幾種主要模式[J],黑龍江社會科學,2008年03期
注釋:
[1]張華:中世紀文學批評的幾種主要模式,黑龍江社會科學,2008年03期,119-121頁
[2]沈文欽:何謂“liberal arts”,北京大學研究生學志,2007年第1期,79頁
[3]符·塔達基維奇.《西方美學概念史》[M].褚朔維譯,學苑出版社,1990年,30頁
[4]比厄斯利. 《西方美學簡史》[M].高建平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136頁
(作者單位:中央民族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