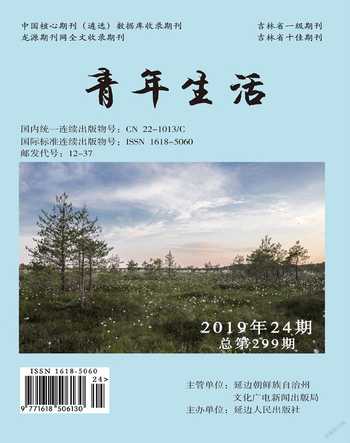先秦儒道兩家生死觀的探析
包春
摘要: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與社會競爭的日益加劇,使得不少大學生在面臨與之而來的就業壓力、生活壓力甚至是生存壓力時手足無措,更有甚者走上了自殺這條不歸路。先秦儒道兩家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兩大支柱,通過對先秦儒道兩家生死觀進行合理的比較探析,對于當代大學生樹立正確的生死觀、人生觀、價值觀無疑具有積極的引導意義。
關鍵詞:先秦;儒道兩家;生死觀
引言
生是什么?死又是什么?如何對待生與死?等等這些問題,中外的哲學家、思想家早已有了不同的見解。如西方哲學家叔本華所認為的,“大多數人的生活不過是求生存的持續的斗爭,人每一次呼吸都是對威脅自己的死亡的抵御,每一秒鐘都為抵御死亡而戰斗,但是死亡終于必然取得勝利。”或者如西漢司馬遷所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他們都認為死亡乃是人類的一種必然的生命現象,但不同之處在于是選擇消極面對、迎接死亡的到來,還是雖已知死是必然卻無所畏懼,進而彰顯人生的價值,死得其所。另外,西方的“創世說”與寄希望于來世的觀點同儒道兩家注重現世的生活,在當世解決生死價值的實現問題存在尖銳地對立。因此,不難發現如何選取正確的生死觀,合適的生死觀,對于個人樹立起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具有重要的指導價值與指導意義。在某種程度上,先秦儒道兩家對于生死觀上的理性主義見解,使得當時的人們免于陷入對宗教的迷狂之中,化解宗教在生死觀上對人的誘惑意義非凡。下文主要從先秦儒道兩家生死觀上的相同點與不同點進行切入,進行具體的分析。
一、先秦儒道兩家生死觀的相同點
先秦儒道兩家在生死問題上的觀點有其相通之處,首先他們都肯定死是人生的終結,是種必然的現象。儒家認為,生是人之始,死是人之終,生死變化是自然變化的常道、常理,也就是必然之路,有生則有死。“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荀子·禮論》)同樣地在道家的老子看來,除了“道”以外,宇宙萬物包括人都是有生必有死的。“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乎人?”(《老子》)莊子也認為天與地雖是無窮盡的,人的死亡卻是有時限的,“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莊子·盜跖》)其次儒道兩家都肯定死生是命定的。儒家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顏淵》)道家代表人物莊子也說:“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莊子·大宗師》)可見,儒道兩家對于生死問題的見解上都認為“命”是種非人力所能干預的客觀必然性。
二、先秦儒道兩家生死觀的不同點
(一)生與死的本質問題
在關于什么是生?什么是死?這樣一類事關生死的本質的問題上面,儒家采取一種“存而不論”的態度。《論語》記載:“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在這里,可以說孔子是不談論具體的死是怎么一回事的,對未知的死常常采取回避的態度,但其實可以說孔子只是更加強調現實的生的意義。而道家在這方面則有較多的論述,道家將萬物之生歸結為無為之道的作用,“道”賦予萬物以生命的潛能。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莊子也說:“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莊子·漁父》)萬物及人是生是死,取決于其與“道”的關系。只要萬物和人按照“道”的規律生存,內含著“道”這一生命根據,就能保持其生命的存在和持續;相反,如果萬物和人違反了“道”的規律,其生命軌跡與“道”相分離,就會失去“道”作為其生命存在的根據而死亡。另外道家或者直接將人的生死看作是由道變化而來的氣的作用,氣聚而為人之生,氣散而為人之死。“人之生,氣之聚則生也,散則為死。”(《莊子·知北游》)
(二)生與死的關系問題
前面提到儒家在對于死的問題上持一種“存而不論”的態度,因此,在涉及生與死之間的關系問題上,儒家自然而然地很少去提及討論。相反,道家在這一方面思想甚多,有些思想頗具辯證的意味。“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的思想是建立在他的無為之道的基礎之上的,他看到強大了就接近死亡,剛強會帶來挫折,因此安于居弱守雌,生死亦如此,柔弱勝剛強。同樣地,莊子也得出了死生齊同一體,死生循環相繼的思想。“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莊子·天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莊子·大宗師》),“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莊子·知北游》)
(三)如何對待生與死的問題
先秦儒道兩家在生死觀上最大的不同點集中于兩家對待生與死的態度上,分別由以下幾點來說明:
1.儒家的“悅生惡死”與道家的“不悅生惡死”
儒家悅生惡死,對死亡采取“存而不論”之態,立足于解決現實生活的問題,再去考慮死的問題,孟子就曾說過“生,亦我所欲也”“死亦我所惡”這類的話,可見儒家在這方面的態度。而道家在生死觀上,卻是種不悅生、不惡死的態度,悅生樂死,進而歌贊死亡。道家這種不悅生惡死的態度表現在其認為死是一種休息,是一種人生勞累痛苦的解脫。莊子說“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生為附贅縣玩,以死為決疽潰癰。”(《莊子·大宗師》)另外如《莊子·至樂》中描述莊子妻子死后,莊子“箕踞鼓盆而歌”,都足以反映出道家這種生死不入于心的樂觀態度。這樣的態度其實是與道家以“道”為萬物之本源的思想分不開的,既然死生循環相繼、齊同一體,死乃返歸大道、返璞歸真,又何必執著于死的悲傷中無法自拔呢。
2.儒家的“舍生取義”與道家的“貴生重生”
儒家雖重視生厭惡死,但當生死問題與社會問題聯系起來時,或者說生死問題直面重大社會問題時,儒家認為有比生死來得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仁與義。因此,孔子提倡“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孟子也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茍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孟子·告子上》)荀子說過:“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荀子·正名》)可見儒家高揚仁與義,認為道德操守遠重于人的生命,當社會問題引發生死思考時,切不可茍且偷生,拋棄仁義,而應當舍生取義。而道家卻并不認為人需要為了國家、社會利益而犧牲“小我”成就“大我”,人的生死需要合乎禮義的要求,相反道家認為人的生死只需合乎自然之道。“道之真以治身,其緒余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不以國傷生”。(《莊子·讓王》)
3.儒家看重“死后之名”與道家不博取“死后之名”
儒家賦予了死亡以一定的價值意義,把個體的死亡建立在社會價值判斷之上。孔子曾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論語·衛靈公》)“齊景公有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下,民到今稱之。”(《論語·季氏》)儒家所看重、所追求的正是這種“民到今稱之”的效果,旨在說明個人死亡的意義不在于生前財富有多少、能力有多強,而在于生前的氣節有多高尚,死后有多少人稱頌。這也正呼應了前面所述的,為何當生死問題面對社會仁義問題時,需舍生取義、彰顯個人道德價值,“殺身以成仁”了。相反,道家卻認為“民到今稱之”與“民到今不稱之”沒有什么實際的意義,不去追求這種死后之名,而是主張“且趨當生,何遑死后”,“死后之名非所取也”。“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列子·楊朱》)
4.儒家“修德治身”與道家“因任自然”的養生之道
儒家重視生的價值,將修德治身作為養生之本,孟子就曾說過:“養心莫善于寡欲”(《孟子·盡心章句下》),他又說:“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荀子也說:“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荀子·強國》),又說:“材愨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樂易者常長壽,憂險者常夭折。”(《荀子·榮辱》)由此可見儒家都強調養生要清靜寡欲,循乎禮義。而道家在養生問題上并無禮義、修德治身這一說法,其強調的是“緣督以為經”,也就是因任自然、遵循自然之道為常法來養生修道。當然在這里所說的自然,具體是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這樣一種清靜無為的自然,還是指順應自然之性,即縱情任性而不人為地去矯情損性的自然,暫且不做進一步的探討,可以具體語境具體分析。但可以確定的是道家在養生之道上強調的確實是“自然”這么一種無為之態。
5.儒家“因禮循禮”的喪葬制度與道家的“送死略矣”
儒家的喪葬制度是其生死觀的重要體現,從孔子開始便有“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為政》)的說法,直接表達出對于死亡儀式的重視,孟子也說:“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孟子·離婁下》)另外這樣的喪葬制度又必須建立在“禮”的基礎之上,儒家主張合禮之葬,在治喪送死方面需嚴格按照等級制度的要求與相應地喪葬時間制度的要求。因此由于顏淵家貧,在其死后,孔子不同意顏淵父親厚葬顏淵,因為這樣的厚葬與顏淵的身份不相符。以及孔子斥責弟子宰我認為應改變“三年之喪”時,發出了“予之不仁也……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論語·陽貨》)的呵斥。反觀道家,對于人死后的喪葬方面并無太繁瑣的禮節,持一種無所謂的態度,主張“送死略矣”。莊子說:“吾以天地為棺廓,以日月為連壁,星辰為珠璣,萬物為濟送,吾葬具豈不備耶,何以加此?在上為鳥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莊子·列御寇》)《列子·楊朱》中說:“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沉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死公死裳而納諸石槨亦可,唯所遇焉。”
三、總結
用今人的眼光來看,任何古代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會存在一定的歷史局限性,先秦儒道兩家的生死觀思想也同樣如此。先秦儒家重視道德性、現實性,以至于過分注重生命的社會性,用道德規范衡量生與死的價值,卻忽略了生命的自然性這一前提,沒有自然的生命又怎么能夠實現社會性生命的價值。相反,道家似乎是過分地強調了生命的自然性,高揚因任自然之態,看破生死,無欲無求,缺乏一定的社會責任感。但是我們不能就此來否認先秦儒道兩家生死觀中的深厚智慧,它們對于現代人尤其是大學生們理性地認知生命與死亡,找尋人生的意義無疑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看破生死,不等于看輕生死,辯證看待先秦儒道兩家生死觀思想,以其中精華部分作為個人前進的思想動力,從而更好地面對當今社會產生的一系列壓力,安身立命。
參考文獻
[1]梯利.西方哲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2]郭齊勇.中國哲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5.
[3]徐慶玲.現實關懷下的生死智慧——先秦儒家生死觀研究[D].南京大學,2017.
[4]邵林凡.《莊子》生死觀研究[D].浙江師范大學,2016.
[5]蘇陽.先秦儒道兩家生死觀研究[D].陜西師范大學,2011.
[6]李霞.老莊道家生死觀研究[J]. 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06):1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