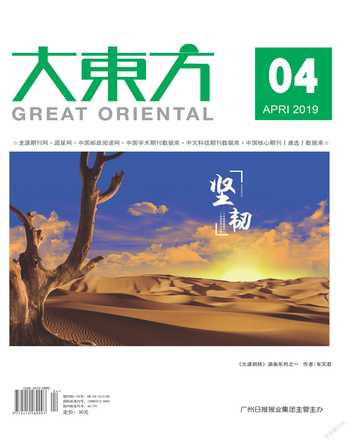美國生態損害賠償制度之于我國的啟示與借鑒
摘 要:建設美麗中國,就是要保護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避免生態損害。然而,縱觀我國現行的生態損害賠償的法律制度,基于“污染者付費、受益者補償”原則的環境資源稅費等經濟激勵制度并未涵蓋生態價值;基于“填補原則”的民法侵權救濟模式亦不足以解決生態損害問題;加之我國生態資源數據庫尚未建立、缺乏生態損害衡量標準,更是無法對生態損害進行充分、有效的賠償。美國的環境法研究較早,立法上對“環境損害”做了越來越清晰的界定。我國應當借鑒美國生態損害的立法及判例成果,在立法中明確生態損害的訴權及相關法律責任,建立生態損害衡量標準和生態損害全過程防治法律制度。
關鍵詞:美國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法律規制;立法完善
一、美國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的構成
(一)賠償主體
1、《清潔水法》中的賠償主體.在1977年修訂后的《清潔水法》中所涉及的是美國內陸水域以及海岸線和海域毗連區內因污染行為、漏油事件而產生的水質變化而導致的損害的情形,因此,該法所規定的賠償主體一般是指油船的所有或者機構或者直接管理者、負責人或者潛在的責任人。
2、《超級基金法案》中的賠償主體.在《超級基金法案》中則針對更為具體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的成本以及重建方案和評估方案的承擔者或者潛在的承擔者所設定,主要的責任主體包括現任或者過去的所有人或者經營者,安排有害物質處理和運輸者。
3、聯邦制定法中的潛在賠償主體.在美國生態環境損害制度中賠償主體除了前文所提到的主題外,還有一類主體值得關注,即潛在賠償主體,或者說潛在責任人。美國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的貴任人的認定大部分還是采用了傳統民法中的責任人的認定標準,即實施損害的行為人,包括了財產的所有人和主要負責人或者運營人、運輸的第三人。
(二)賠償對象
在美國損害賠償制度中,賠償對象或者說求償主體,基于其所有權或者基于法理學理念賦予其托管、信托權利,或者從另一個角度說是對其所有或者授權管轄的的損害而要求損害主體賠償的自然人或者機構或者州政府,同時該主題還有權協商、選擇賠償的方式和享有對賠償金的處置權利。
(三)賠償范圍
總體而言,美國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是指通過對土地、水源(包括地表和地下水源)空氣、植物群落、動物群落以及其他為羅列的對生態環境(包括食物鏈、生態物理性質、化學性質、生物性質等性質)造成包括所有和使用權在內的所有損害進行賠償。
二、中美生態損害賠償的法律規制比較
在美國,有關生態損害的訴訟也并非無往不勝,只有在立法明確的情況下,生態損害才能得到有效的救濟。在Commonwealth v.Shell Oil Co.一案中,原告波多黎各就被告在波多黎各出售和使用甲基叔丁基醚的行為提起訴訟,要求被告停止這一行為,并且應當對此行為所導致的生態損害、道德損害和經濟損害進行賠償。美國聯邦上訴法院法官Shira A.Scheindlin 認為,雖然被告這一行為所導致的損害可以有不同分類,生態損害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根據原告提供的證據進行衡量,但是生態恢復基本上無法實現。
我國與生態環境損害有關的立法主要見于《環境保護法》、《侵權責任法》和各項污染防治單行法當中。我國《海洋環境保護法》第九十條第二款規定:“對破壞海洋生態、海洋水產資源、海洋保護區,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的,由依照本法規定行使海洋環境監督管理權的部門代表國家對責任者提出損害賠償要求。”《侵權責任法》的第六十五條雖然規定了“因污染環境造成損害的,污染者應當承擔侵權責任”。但是,該法第二條列舉的“本法所稱的”十八項“民事權益”,其中生命權、健康權、所有權、用益物權、擔保物權等人身、財產權益均未直接指向生態利益,并未涉及生態環境權益。
綜合上述立法觀之,相較于美國環境保護的立法和判例,我國現行環境保護立法傾向于保護環境資源的經濟價值,將生態環境、作為“財產”或者“財源”來進行保護,現行法律條文的表述及法律規范還沒有顯示出對生態價值的關注,并且缺乏對該生態價值所需要的公法和私法制度的綜合調整。
三、我國生態損害賠償制度的立法完善建議
(一)明確生態損害之訴權
追究生態損害責任,應當“立法在先,行事在后”。一方面,應當確立生態利益的法益歸屬。除一般民事訴訟所涉及的物的生態價值的情形之外,生態損害一定程度上屬于“公共妨害”,其所涉及的生態利益屬于公共利益。由于生態利益的主體不能歸屬于明確指向的私人主體,因此私人主體往往限于權利范域的局限而無法對破壞生態的行為提起訴訟。
(二)明確生態損害之法律責任
在現行立法內容體系之下,可以運用傳統的“命令與控制”(command and control)措施及理念,從生態損害相關主體法律責任的角度對生態損害行為加以規制。如,在現行的《環境保護法》、《侵權責任法》和各項環境保護單行法中,設立減輕和賠償生態損害的法律義務和法律責任。規定政府部門、檢察機關和社會環境保護組織代表公眾提起生態損害之訴的權利。
(三)盡快建立生態損害衡量標準
生態損害如何量化是目前很多國家生態立法的難題。美國運用了許可證、銀行、保險、稅收等多種命令與控制措施以解決生態損害的問題。相對于訴訟途徑,命令與控制措施的優勢在于,能夠就生態保護一般可能發生的狀態進行制度預設。作為具有命令與控制措施特點的生態損害衡量標準,同樣可以事先確立生態損害行為的違法成本。
結論
在我國,生態問題日益嚴重,同時,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范圍不斷擴大和深入,排污者造成的重大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損失得不賠償,從而使得公眾的環境權益和生態系統都得不到保護。隨著2016年《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試點方案》的提出,建構完整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是接下來幾年我國環境法學領域的重點之一。鑒于此,文章通過對美國的自然資源環境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的研宄,以期對建構我國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提供思路。
參考文獻
[1]KATHLEEN CHANDLER SCHMID.The Depletion of the Superfund and Natural Resource Damages,[J].16 NYU ELJ 483,488(2008):Branney V Keokuk,94 U S 324(1876).
[2]殷鑫.生態正義視野下的生態損害賠償法律制度研究[D].華中師范大學.2013.
[3]梅宏.生態損害預防的法理[D].中國海洋大學.2007.
[4]王曦、胡苑:《美國的污染治理超級基金制度》,載《環境保護》2007年第5期.
[5]陳岳琴、Storm King:《美國環境公益訴訟的經典案例》,載《世界環境》2006 年第6期.
作者簡介:
常琦(1993,10-今),女,漢族,河南漯河,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經濟法
(作者單位:西南財經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