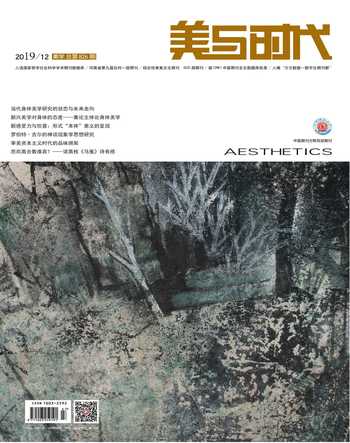略論國家在藝術創作中的地位與作用

摘? 要:在藝術作品的誕生和評價機制中,國家是一項值得深入探討的因素。對此,不同學者也從不同方面論述了兩者之間的關系。高爾基作為蘇聯時期的文學泰斗,其一生的境遇及其文學創作在不同時期都有著不同的特點,而這些特點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高爾基的藝術創作與國家之間的深層互動關系。
關鍵詞:藝術創作;國家;高爾基;地位
關于國家在藝術創作過程中的地位,不同的研究者給出了不同的觀點。貝克爾的《藝術界》認為,“所有的藝術家都依賴于國家,他們的作品都蘊含了這種依賴”[1]150。他認為,國家總是在藝術品制作過程中發揮作用并產生一定的影響。比如,國家的利益可能會與藝術家的利益一致,藝術家需要在國家法律的條條框框中創作。這些都會使藝術家們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煩對自己的藝術創作進行調整,在這些調整中體現了藝術家對國家的依賴以及國家對藝術創作過程的某些限制。貝克爾認為政治對藝術有一定的壓制性,很多學者則認為二者之間的關系應當是一個雙向的互動過程。薛雯、劉鋒杰曾表示,“藝術與政治之間應當用想象來結緣,相互關聯,相互作用,卻又各具特性,不會相互取代。”[2]這里意在說明藝術與政治的雙向互動過程,即認為藝術和政治是一個相互影響和改變的關系,二者之間不存在取代。所以,從另一個層面來說,我們討論藝術的政治性,討論藝術對社會在政治維度上的貢獻性并肯定這一點,就是在證明藝術的有用性,證明二者之間的這種雙向互動。這種雙向互動也決定了藝術與政治之間可以影響,但是藝術不能成為政治實施的手段。正如文苑仲所說:“藝術絕不能充當說教的工具,其政治功能不在于‘介入’現實,而是存在于藝術的獨立與自主之中,通過保持與現實世界的審美分離而發揮歧感效用,去擾亂所謂‘正確’的觀看、言說與行動的方式,改變主體對自身的‘位置’。”[3]
總之,不同的學者基于不同的時代和立場給出了不同的觀點,本文無意對其進行全面的梳理或對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空洞的探討。藝術的影響和印記可以體現在許多政治斗爭和革命歷史中,比如我們耳熟能詳的《馬賽曲》《國際歌》《自由引導人民》《格爾尼卡》等,藝術的光輝無處不在。當代的一些藝術家更是將藝術極好地應用到現實生活中,他們從藝術的角度,將關注點對準復雜、抽象的政治、社會問題,對此進行批判和反思。而我們熟知的大文豪高爾基,無疑是蘇聯時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學家之一,同時也是反映藝術家與政治之間關系的典范。那么,高爾基在不同的人生階段進行的文學創作有哪些不同的特點?這些特點與國家又有著怎樣的關系?以此論之,高爾基的文學成就與國家有怎樣的關系?國家在藝術創作中的地位是怎樣的?本文將就上述問題展開探討。
一、高爾基的文學生涯
高爾基作為蘇聯時期的大文豪,一生的政治立場和價值觀在不斷發生轉變,這些變化的價值觀與他本人所處的政治環境包括他與當局者的關系有密切聯系,這些都反映在他不同階段的文學創作中。
高爾基是偉大的作家,被譽為“無產階級藝術最偉大的代表者”。在1905年以前,高爾基屬于文學圈內人,他的政治觀點與知識界的主流思想一樣,屬于反對暴力革命的改良主義。1906年的法美之旅是他的思想左傾化的一個轉折點。高爾基迅速接受并轉向馬克思主義觀,主要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逐漸失去了活力和熱度,他個人的思想轉變也使他的革命性大大增強。這一時期描寫工人運動的小說,比如《母親》《仇敵》《夏天》《懺悔》等,高爾基深刻地描繪了工人階級從自發到自覺的過程以及革命的歷史必然,論證了群眾一旦掌握革命理論,就將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這一典型的馬克思主義原理。以小說《母親》為例,其中的人物雷賓對尼羅娜說:“跟著兒子走,走兒子的道路,他大概是第一個吧,是第一個!”[4]283這里的“第一個”代表了當時那一代人的先鋒精神和整體的精神面貌,“母親”則代表了整個時代的精神領袖。
而后的“十月革命”成為高爾基與列寧發生沖突的導火索,高爾基也因此被稱為當時“不合時宜者”的代表,他基本上站在布爾什維克的立場,主辦《新生活報》為它發聲。當新的當權者開始對布爾什維克進行殘酷的封殺之后,高爾基以筆作為槍桿子,開始將批判的矛頭對準“十月革命”中的暴力和非人道行徑。他精煉的語言文字猶如一排排大炮將那些慘絕人寰的行徑揭露得干干凈凈。他寫道:“這是一場沒有精神上的社會主義者、沒有社會主義心理參與的俄國式的暴動……”;“列寧在用工人的血、工人的皮做一場極端的獸性實驗,列寧為了自己的試驗讓人民血流成河……”等。在高爾基的文集《不合時宜的思想》中,這樣的言論反復出現。從他對蘇維埃政權種種猛烈的批判中我們看到一個承擔著“社會良心”角色的高爾基,他坦誠、率真地揭示了十月革命初期一些令人難以理解的行為,《不合時宜的思想》這一題名本身也就意味高爾基藝術創作的現實性。此時,高爾基與布爾什維克的關系既不是戰友也沒有變為敵人,他們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分歧,尤其在關于革命與文化的關系方面。一方面,高爾基承認俄國社會變革的必要性,但是執政黨使用暴力對待文化遺產及科學家等行徑違背了人道主義;另一方面,高爾基的人道主義的理想在革命的發展中似乎已經變了味道,不得已,他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即寫出來的作品來與當局對抗。他說這個政權“正在激起我對它的反感”。斯大林曾說,這時的高爾基與反革命沒什么兩樣,他是一具“政治僵尸”。
1921年,內心對蘇維埃政權強烈的不滿和失望的高爾基出國,先后在德國和意大利長住。國外生活的十年間,蘇維埃政權的發展讓高爾基大跌眼鏡,因為它不僅生存下來了,而且發展得越來越壯大。在這種時代背景下,高爾基的相關言論轉向發生了潛移默化的變化。他說蘇聯“進入了新生時代”,“國內生活的進步越來越顯著”,“我相信他們可以找到阿基米德支點”。高爾基言論的轉變也可以體現出他對當局政權態度的變化。一開始,高爾基處在一個“不合時宜”的尷尬地帶,后來,布爾什維克的發展壯大使他從對其專政的批判轉而投向對黨的“一元化”和“政治一致性”的支持和贊美。
緊接著,高爾基在當權者斯大林的幫助下回國,回國后的高爾基似乎變成了一個對斯大林體制的吹捧者。相比于十月革命時的口無遮攔,高爾基變得小心翼翼,他和斯大林的關系也相當親密,并慢慢參與到斯大林的政治游戲中,這決定了他價值觀的轉變。從1930年開始,高爾基對斯大林大加贊揚。1931年,他對斯大林的相關事宜的描述較為平實和單調,如“斯大林同志說……”;1932年,高爾基眼中的斯大林逐漸升格,他成為“列寧的忠實、堅定的學生”、稱之為“我們的領袖”等;到1934年,高爾基對斯大林的贊美之情溢于言表,“斯大林在世界的作用和意義,增長的越來越快”,斯大林是“第二個列寧”等,從高爾基對斯大林的描述和贊美中,我們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轉變,以及在政治生活中對斯大林個人形象的完美塑造。
20世紀90年代,高爾基褪去了曾經的模樣,對于當時的國家政治,他沒有用他犀利的筆鋒發出“正義的怒吼”,反而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黨的傳話筒。對于當權者斯大林而言,高爾基是當時塑造革命史最恰當的人選。俄國政黨可以靠“鐵的紀律”來約束,然而,知識分子的思想自由和獨立卻需一個有權威的知識分子做表率才更有說服力,高爾基在斯大林時期扮演的正是這樣一個角色,這極好地體現了國家在高爾基藝術創作中起到的關鍵性作用。
二、高爾基的藝術成就
高爾基可謂是文學史上的風云人物,他剛剛走進文壇時,是一位浪漫主義作家。從《海燕》開始,他的浪漫主義風格逐漸發生轉變,文學作品與現實的聯系日益緊密,現實主義風格愈來愈明顯,而《母親》被認定為“是本奠定無產階級文學史基的作品”。高爾基從浪漫主義到現實主義的轉變反映了他在文學取向上的重要轉變,這也為他創作革命題材的作品奠定了基礎。
毫無疑問,高爾基是一位大文豪,除此之外,他還冠有革命文學家的名號。他用手中的筆桿子表現了革命斗爭的必要性,他的文學作品中所體現的時代精神和革命精神又讓人們備受鼓舞,去創造、去抗爭、去革命。《海燕之歌》和《母親》是高爾基用他的文學作品去革命的最好證明。1907年發表的《母親》正值革命發展的低谷期,在“沒有拿武器的必要的時代”成為時代的口號。高爾基卻不以為然,他認為武力革命是必要和正當的。這兩部作品成為一支有力的革命進行曲,這與最初高爾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并主張革命的政治觀相一致。所以,回蕩在高爾基作品中的主旋律始終是對革命和自由的高昂吶喊。事實上,高爾基前期的作品與政治聯系最為緊密,包括他的自傳體三部曲、流浪漢小說等。十月革命發生時,國內出現的流血事件和暴力行徑讓高爾基意識到傳統的封建制度已經成了人民心中的精神毒瘤,即使實現了外在的解放,人們心中的奴性卻根深蒂固。為此,高爾基的《羅斯游記》《日記片段》《1922-1924年短篇小說集》極好地展示了當時的民族問題,他還抨擊了當時的民族心態。
總而言之,每一場革命都使得高爾基意識到了提高民族文化水平的重要性。“在他看來,在以農民為主體的俄羅斯,之所以連續不斷的出現許多令人難以理解和接受的現象,根本原因就在于民族精神文化水準偏低,而政治斗爭則為民族劣根性的膨脹性顯露提供了最肆無忌憚的時空。”高爾基的創作成就了自己,成就了當時的時代。因此,與其說是時代塑造了高爾基的藝術風格,倒不如說高爾基的藝術充分體現了時代的要求。也正是高爾基的作品從文學和藝術上保留了人們的生活、追求和夢想,也保留了時代的殘酷、暴力和希望,高爾基在這種掙扎的希望中不斷表現著斯拉夫民族所經歷的歷史階段。
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高爾基取得了十分出色的文學成就,這種成就深深植根于高爾基對民族的深切眷戀之中,也植根于高爾基早期文學訓練所達到的水平之上。如果能夠摒棄蘇聯國家的影響單純評判高爾基的藝術,那么他的藝術成就無疑已經達到了一種十分高超的水平。
三、結語
高爾基布滿荊棘的人生和曲折的文學創作之路在俄國文學界和工人階級長達四十年的發展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他所留下的大量文學作品不僅豐富了蘇聯時代的藝術形式,而且在世界文學殿堂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高爾基的文學創作之路充分體現了藝術家與國家之間的互動:列寧時期的高爾基因為不能完全適應政治形勢使其藝術地位始終處于比較低的狀態,從他在這一時期顛沛流離的生活狀態可見一斑;斯大林時期的高爾基完全成為政治宣傳的工具,他與斯大林的合作也顯得十分曖昧,高爾基的藝術地位直線上升,并且成為家喻戶曉的文學家和藝術家。前后兩種巨大的反差反映了藝術家如果能夠適應政治的發展需要就有取得聲望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所塑造的藝術家實質上能夠代表某一時期的政治取向和審美要求。
顯而易見,不能將國家與藝術的關系簡單地化約為互相成就或者互相促進,這樣的認識可能引起藝術創作和藝術成就中的一種悖論。藝術的創作與成就取決于藝術家的人生經歷,別樣的人生經歷必定塑造不同形式的藝術作品,而高爾基所經歷的人生恰恰是紅色政權極其隆盛的階段,這種階段極易塑造政治家的御用文人。因此與其說藝術家是時代的產物,倒不如說任何有成就的藝術家都會將人生經歷寫進個人的藝術作品之中。當然,藝術成就的高低還與藝術所達到的整體水平有著密切的關系,高爾基所在的時代是俄國蘇聯文學已經積淀了近千年的時期,因此高爾基是在繼承斯拉夫民族優秀文化傳統之基礎上所達到的藝術高度。
本文以高爾基為例著重探討了藝術與國家之間的關系,這無疑是一個個案研究,不能將類似的研究推論至廣闊的學術視野之中。這一探討的意義就在于為藝術與國家之間的關系研究提供了一種具有典型性的案例,這個案例不能全面說明國家與藝術在何種程度和何種維度上的互動和交流,也不能表明藝術與國家之間存在著簡單的邏輯關系。只能說明高爾基的藝術成就與國家之間有著緊密的相關關系,這種相關關系是不可或缺的,正是因為這種相關關系直接塑造了高爾基及其文學成就。
參考文獻:
[1]貝克爾.藝術界[M].盧文超,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
[2]薛雯,劉鋒杰.藝術的反抗性——藝術與政治關系的一個維度的理解[J].文藝爭鳴,2015(7):97-105.
[3]文苑仲.走向歧感現實,回歸審美之真——雅克·朗西埃論藝術的政治功能[J].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2015(5):155-160.
[4]高爾基.母親[M].吳興勇,劉心語,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15.
作者簡介:伊丹丹,上海大學文學院全球學專業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