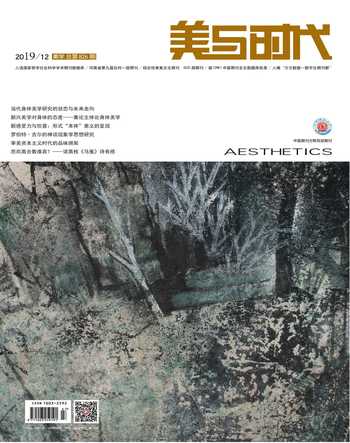淺談反烏托邦思想
摘? 要:隨著工業技術、民主政治等一系列現代化概念的出現,反烏托邦也悄然出現。烏托邦最重要的思想就是理性和科學,柏拉圖的《理想國》將詩人驅逐出理想國就是因為詩人過于熱情,而理想國是一個理性的世界。但反烏托邦就是從這入手,將烏托邦的理性和科學極端化,從根源上對于烏托邦提出質疑。在時代的大潮流下,反烏托邦也許已經失去了其活力,消散在那段特殊的歷史中,但其警示意義卻永遠具有價值。
關鍵詞:烏托邦;反烏托邦;理性;科學
提到反烏托邦,也許人們感覺不如烏托邦熟悉。要想弄清楚反烏托邦是什么,首先要明白烏托邦是什么。烏托邦自古希臘時期就已有雛形,阿里斯托芬的《鳥》、柏拉圖的《理想國》都為人們塑造了一個理想的世界。柏拉圖《理想國》中提出了理念世界與現實世界,而柏拉圖認為理念世界是真實的,現實世界是虛幻的,是對理念世界的模仿以及人們對自己欲望的表達等。所以,柏拉圖塑造的烏托邦世界是無法實現的,只是一種理想化的社會構想。而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推崇共產主義,反對私有制,打下了近代烏托邦文學創作的主基調。反烏托邦與之相對,描寫的大多是看似穩定又平等的社會表面下,有無數暗潮涌動。人民的思想觀念、本能欲望被壓制,規則禁令囊括生活中的各個方面。在極度壓抑的思想、政治禁錮之下,統一化的管理標準和生活準則使得個體發展趨向扭曲,個性化發展被壓制,社會變成了標準化生產車間,個人成了流水線上制造出來的工具,按照嚴密的組織形式推動國家機器的運行。
一、反烏托邦產生的背景
20世紀初,資本主義私有制為人所詬病,金融危機爆發,資本主義的缺點開始暴露出來,人們對其感到失望并逐漸開始探索新的出路。烏托邦所營造出的理想社會給人們帶來了一線希望,人們對此投入了極大的熱情。共產主義漸漸走入了人們的視野,社會平等、物資充足,人們各司其職、按需分配,沒有壓迫,人們憧憬著共產主義的曙光。但“二戰”爆發了,法西斯披著社會主義的外衣進行種族屠殺,強權暴力,對內進行冷酷剝削、恐怖統治,對外殘酷鎮壓侵略掠奪,歐亞非陷入人間地獄。
二、反烏托邦的特征
烏托邦最重要的思想就是理性和科學。柏拉圖的《理想國》將詩人驅逐出理想國就是因為詩人過于熱情,而理想國是一個理性的世界。但反烏托邦就是從這入手,將烏托邦的理性和科學極端化,從根源上對于烏托邦提出質疑。
(一)反對以理性主義為教條
烏托邦主義者的理性主義是和真理觀上的絕對主義、權威主義聯系在一起,這種真理觀容易導致壓迫和強制,是一種不寬容的真理觀。烏托邦主義者看不到人的理性認識能力的局限[1]76,就如《我們》中,人民沒有名字,而是以字母和數字組成的號碼來識別彼此。他們認為舞蹈之所以優美是因為它的不自由,娛樂活動就是大家邁著整齊的步伐踩著拍子一起伴著音樂在大街上踏步。人們生活在不能拉上簾子的玻璃房中。人的原始欲望被極端壓制,想要發泄欲望需要領取玫瑰券,然后填上對象的號碼。人們自由繁衍后代是違法的,延續幾萬年的自然規律就這樣被加上了禁錮。而且不幸的是,身處扭曲社會環境中的人們認同這種強加的禁錮,并且在這種畸形的環境中適應了模式化的“幸福”生活。“如果他們不能理解我們帶給他們的是算數般準確無誤的幸福,那么我們將有責任強制他們幸福。”[2]1打著為了人類幸福的旗號,但是本就感性的東西在外部強制施加理性是不會得到真正的幸福的。幸福不能強制,是當人在體會到了身心愉悅自然產生的情緒表達。絕對理性且不說能否做得到,即使能做到也是在極大程度上消磨人性的代價之上實現的。
社會之所以進步,理性是不可缺少的推動劑。理性使人們看到了君主統治的局限性,開啟了認識自我的大門。人們不再盲目服從統治者、權威者的說法,不再低頭苦干,而是開始肯定自己的能力、看到個人的價值。對社會進行理性批判,可以使得個人產生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的意識,保持社會進步的同時維護其民主性。而將理性主義推向極致并以之為教條,就達到了另一種狀態的神性真理主義,將理性放置在神的高臺上,認為理性、人的能力無所不能本身就帶有片面性。人具有思想是人與動物的一個區別,人可以獨立思考,這就使得人在做決定或者日常生活中都不可避免地帶有感性色彩。人的生活經歷、社會狀況等一系列因素都決定了每個人針對同一突發狀況也許會做出帶有個人色彩的反應。所以,反烏托邦主義者對于絕對理性主義是持懷疑不認可態度的。既然個人不是機器,就不應該用各種條條框框事無巨細地對人的生活、精神、思想等進行禁錮和束縛。就如《1984》和《我們》中的主人公,無論社會多么黑暗專制,即使是先進殘忍如電幕、氣鐘罩等依然無法阻止人思想的解放和追求自由的渴望,壓制越強,反抗就越早到來。理性和感性在人類的日常生活中是同等重要的,對于處理不同類型的事務,它們會發揮不同的作用。僅依靠理性去解決感性才能解決的問題是不合時宜的,這種違背人類本能沖動的做法很容易導致人性的扭曲和異化,而勉強維持社會運轉的上層建筑的崩潰則遲早會發生。
三、唯科學技術主義的祛魅
自文藝復興之后,科學的地位不斷提高。科學對社會的發展也是至關重要的。航海術的改進促成了新大陸的發現,伽利略、哥白尼等發展了天文學,打破了地球中心論,用科學否定了上帝創造萬物的宗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為顛覆教皇統治奠定了基礎。自自然科學獨立之日起,科學便滲透進了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從19世紀初期至今的200多年里,很多人預測科技烏托邦即將到來,相信科學技術將會把人類從勞動、疾病、痛苦甚至死亡中解脫出來[3]3。實證主義是科學主義思潮的源頭,它產生于19世紀30-40年代初的法國,后流行于英國[4]。這就催生了“科學萬能論”的唯科學主義。唯科學主義將自然科學知識當做人類知識的典范,將科學方法看做是萬能的,認為科學在人類活動中具有絕對有效性。唯科學主義對科學文化秉持至高無上的優越感,把科學視為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普遍有效的知識和方法[3]117。“書本與噪音,鮮花與觸電——已經在這些嬰兒的頭腦中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經過兩百次相同或類似的重復教育,將會變得根深蒂固。人類締造的聯系是大自然無力解開的。”[5]這就將科學技術上升到自然也無法干涉的高度,想要借科學技術干涉人類的自然發展,這本身的科學性就難以使人信服。
科學對于近代社會的發展功不可沒,但任何事物的發展都具有雙面性,“物極必反”是亙古不變的真理。人工智能的出現使人類的現代生活便捷高效,科學家窮盡畢生的能力想要賦予機器人思維,使其可以像人類一樣思考甚至創造。當機器人可以擁有思維,它是否愿意一直作為人類的朋友為人類服務?它是否不會想著為自己爭取利益最大化?就能力本身而言機器比人類擁有太多先天優勢,如果再加上人類獨有的頭腦思維,人類是否還可以控制得了機器?這一切都是未知數。科學技術擁有兩種極端社會形象:一種是宙斯式形象,一如至高無上、威力無比的巨人;一種是撒旦式的形象,一如《圣經》中的魔鬼,帶給人類災難,使人性墮落[6]。這句話的準確性先暫且不論,但它十分形象地比喻了科學技術的兩面性。有許多科幻作品都表達了對這個角度的思考,《生化危機》被不少人看做恐怖片的代表,但它的實質卻是為了讓人們看到隨著科技進步,人類的欲望不斷膨脹,當人性被撒旦引誘,手中所持有的科學技術就如同潘多拉的寶盒被打開一樣,人間就會變成地獄。就如同“二戰”時期,人們以為的烏托邦社會并沒有到來,卻迎來了核武器投入戰爭、日本在戰場使用生化武器、美國在廣島投下原子彈……回顧歷史,科技帶來的不只是幸福和快樂,當它被不加節制地濫用之后,之前帶給人們的短暫幸福瞬間煙消云散,而其產生的巨大災難卻是人類所無法承受的。
四、對集體主義的反思
“集體”一直被當做團結、合作的象征。當國家遇到災難,由無數個人組成的向心力會產生巨大的能量。但凡好的事物都是有其可適用的范圍,超過了這個范圍便會產生相悖的作用力。烏托邦者的思想帶有一元論的色彩,柏林認為,一元論是一種壓迫性的哲學觀念,因為,它相信“一”是本質的、真實的,而“多”則是非本質的、虛假的。“一”是高級價值,“多”是低級價值。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人們容易借高級價值之名對低級價值進行強迫和壓制,借集體、民族、國家之名對個人的強制就是它的表現[1]10。“二戰”時期納粹對德國民眾進行思想麻痹,宣稱日耳曼民族至高無上,猶太群體則應該清除。在德國很有淵源的民族主義此時成為巨大的社會凝聚力,在這個社會中,每個人都是作為實現民族理想而存在的工具,狂熱的社會氛圍帶走了人們的理智。個體無論情愿與否都無法從集體中脫離開來,失去了自由和主觀能動性的個體消失在集體中,個體無法掌控事態的發展,局面也隨之開始變得失去控制。
“烏托邦”的初衷是要帶領人們獲得自由平等的權力,使人獲得獨立自主,人格被保障并得以健康發展,但在實踐過程中卻往往難以控制其走向。有統治階層就會有一定程度的強制性,這樣才可以保證大多數人的基本權利。而其中對于壓迫和民主的使用體現的便是統治者的智慧。壓迫著所有個體為了所謂個人的利益服從于集體的管制,就如同《動物農場》中所寫的那樣“殺戮和恐怖并不是老少校第一次鼓動大家造反的那一天晚上,大家所期待的。如果她能想象出未來的圖景的話,那應該是一個動物們不再挨餓、挨打的社會,大家平等,各盡所能的勞動,強者保護弱者……誰也不敢坦率地說出自己的想法,兇惡怒吠的大狗四處游蕩,而你不得不看著自己的同志在供述了可怕的罪行后被撕成碎片”[7]。人們對于所處時代感到厭惡,想要尋求一個美好自由又幸福的世界的愿望會激勵人們不斷奮斗,為了實現如此宏偉的目標,個人的能力就顯示出了其局限性,只有個人凝聚在一起形成集體才能不斷向這個美好愿望靠近。而這個過程中一旦出現偏差,就需要個人暫時放棄某些權力以實現集體利益,這種暫時放棄可能會不斷延續下去,直到人們忘記了當初屬于自己的基本權利。畢竟革命之前的社會狀況并不美好,人們不愿意因為爭取自己的權利而失去現在所謂的美好。個人融入集體之中,就不再需要個性了,只要保障集體平穩運行,個人利益就成了可以隨時被放棄的東西。在奮斗過程中出現的偏差往往沒有被糾正,而是愈走愈遠。“你看,甚至思想。這是因為沒有人是‘唯一’,而只是‘我們中的一個’。我們是如此相像……”[2]6失去了個性的人已經不能稱作是完整的人了,他們不過是統治者用來維持國家運行的傀儡,如此說來科技也將停步不前,人們失去了創造性的思維,不再追求進步與發展,如此這般對于整個社會來說絕對不是進步,而是返古。尊重個體差異,在鼓勵其個性發展的同時使之以建設社會為抱負,以國家民族為向心力,才能推動社會健康穩定發展。
五、結語
在時代的大潮流下,反烏托邦也許已經失去了其活力,消散在那段特殊的歷史中,但其警示意義卻永遠具有價值。喬治·奧威爾的《1984》準確地預測了蘇聯現實的發生,反烏托邦主義者并非是崇尚暴力、血腥及戰爭的狂熱之徒,也不是滿腹黑暗恐怖色彩的悲觀主義者,他們其實與烏托邦主義者一樣相信理性和科學,但同時他們也看到了理性和科學的局限性。在完善所處時代的同時,又該怎么科學合理地控制制度的發展以及如何避免極端理想化的烏托邦統治是他們關心的問題。也許有人會說反烏托邦思想帶有些許極端,其中蘊含的深刻思考值得我們關注。事物在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小裂縫會變成大溝壑,在及時反思歷史、規避風險的同時也應步伐堅定地創造美好的明天。
參考文獻:
[1]謝江平.反烏托邦思想的哲學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2]扎米亞金.我們[M].王莒,譯.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13.
[3]鄔曉燕.科學烏托邦主義的建構與解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4]夏基松.現代西方哲學教程新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2.
[5]赫胥黎.美麗新世界[M].陳超,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7:25.
[6]李伯聰.略論科學技術的社會形象和對科學技術的社會態度[J].自然辯證法研究,1988:4.
[7]奧威爾.動物農場[M].余謹,譯.北京:中華書局,2014:54.
作者簡介:邵路鳴,鄭州大學文學院文藝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學思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