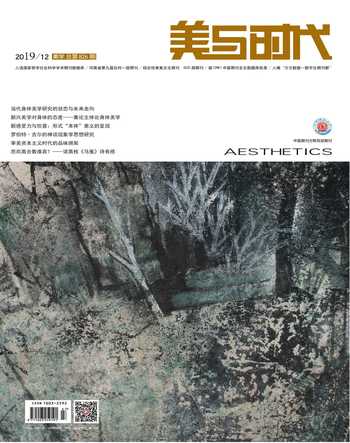動畫紀錄片是否只會讓人“崩潰”




摘? 要:動畫紀錄片是近年來國內較為流行的一種紀錄片類型,越來越多的記錄性影片開始采用動畫的表現形式,這不僅增加了影片的看點,更充實了紀錄片的表現空間。動畫紀錄片較之普通紀錄片,除了具備基本表述功能,還表現出彌補紀錄片中資料的不足、節約時間、節約制作成本等優勢。此外,動畫紀錄片突破了傳統格局,豐富了場景轉換效果,增加了趣味感,擴大了受眾年齡層。
關鍵詞:動畫;紀錄片;動漫發展
動畫紀錄片的概念可以追溯到2009年《動畫紀錄片——一種值得關注的紀錄片類型》一文,國內學者由此開始對“動畫紀錄片”展開深入探討,討論的過程中充滿歧義的解釋持續不斷。從創作實踐的層面看,雖然國產動畫紀錄片作品眾多,但理論界對諸多影片的分析卻并未得到業界認可。其爭議的焦點在于動畫紀錄片作為一種類型片存在的真實性及合法性兩方面。
對此學界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聶欣如等學者認為“動畫紀錄片”的概念難以成立,因為凸顯動畫技術能達到所謂真實,是對動畫藝術與影像記錄的混淆,有消解藝術分類,濫用、錯譯國外定義的趨勢。此外,他認為新事物不必通過似是而非的概念來擾亂一般的知識體系。王遲先生則認為動畫紀錄片具有合法性,強調動畫作為一種自由的藝術媒介,為紀錄片的表達增加了一個維度表達心靈。此外,孫紅云及喬東亮等人則試圖用“量值”來為動畫紀錄片的合法性進行驗證,認為動畫和紀錄片最終將回歸像素層面并無本質差異。
2011年《中華五千年》(如圖1)橫空出世,被譽為“中國首部動畫歷史紀錄片”[1],共51集。以時間為軸,分成上古、遠古、夏商周、春秋戰國、秦、漢、唐宋元、明清等章節,涵蓋神話史說、歷史文化、名人故事等方面,如盤古開天、禪讓禮制、武王伐紂與周代文化、儒學思想、孫子兵論、武帝之功、絲綢商路等傳統歷史文化內容。歷史的恢弘氣勢充分展現出泱泱大國的風范與底蘊。
影片有金戈鐵馬的壯烈,有神話人物的傳奇,有中華文明的璀璨。作者將二維動畫與三維動畫集于一體,用先進的動畫技術還原中華文明五千年面貌,再現跌宕起伏、五彩斑斕的華夏圖卷。
片中人物設定從比例結構到舉止衣著都切合時代背景。文物、亭臺樓閣的形象也都還原了真實歷史面貌,并在劇情進展中穿插史料書籍、傳世畫卷加以佐證,力求將最貼近史實的敘事、最真切的情感、最高質的畫面呈現給觀眾。
但爭議也隨之而來。就“真實”二字,專家學者們各執一詞,究竟什么才是動畫紀錄片?動畫紀錄片能否抵達“真實”?倘若動畫紀錄片合法,它又具有怎樣的根本屬性?未來發展前景如何?這一系列問題都是學者們孜孜探究的內容。
一、關于動畫紀錄片概念的界定
何為動畫紀錄片?國內明確的定義共見兩處:一是尉天驕先生提出的:“所謂動畫紀錄片,就是采用計算機圖形技術,利用電腦生成的虛擬場景,全部或部分代替現實社會不存在的、無法復原的視覺景觀的紀錄片。”二是王遲先生:“用動畫形式來表現、處理現實世界中非虛構人物或事件的影片類型即為動畫紀錄片。”[2]
兩處定義均提到:在動畫紀錄片中,動畫作為一種技術手段介入到紀錄片的拍攝過程中,彌補了傳統拍攝手段無法復原真實的不足。定義的方法和角度集中在此類影片的技術層面,但又落腳在紀錄片這一中心語上。此種定義基本能夠概括動畫紀錄片的屬性。但對于動畫成分在整部紀錄片中所占比重的界定略顯模糊。若籠統地將由大量且重要的部分采用實拍技術,或者只有少量或某處次重要的部分輔以動畫手段而完成的紀錄片,全部歸類為動畫紀錄片顯然是不妥當的。因此,筆者認為:只有當紀錄片中大部分或全部影像為動畫時才更貼合動畫紀錄片的本質。
二、動畫紀錄片的特征
(一)真實性
“真實”一直是紀錄片的首要特征,隨著動畫技術的飛速發展,強烈逼真的視覺效果,幾近真實的光線效果使人體驗到身臨其境的真實之感,可見動畫早已成為紀錄片制作的一柄利器。當動畫技術介入到紀錄片領域后,可謂大展拳腳,不僅出現了全動畫的紀錄片,還夾雜了三維動畫應用的實拍紀錄片。1926年英國的約翰·格里爾遜最早提出“紀錄片”一詞,并闡釋為,“紀錄片不僅要拍攝自然的生活,而且要通過細節的并置創造性地闡釋自然的生活”[3]。可見作為一種藝術形式,紀錄片的真實并非絕對的真實,而是基于不“戲說”、減弱主觀代入、講述“真理”三條原則下的藝術再創造[4]。
(二)富于藝術表現力
動畫紀錄片在表現政治主題、歷史內容、戰爭題材、宗教信仰或個人隱私等新銳話題時,能作為一種有效的平衡手段。動畫紀錄片遵循動畫片的一般創作方式,將抽象事物符號化,即以弱化某些細節為代價,凸顯和放大了最為本質的內容。以《路斯坦尼亞號的沉沒》(如圖2)為例,罹難者的慘狀,著力描畫的一些孩子的面部表情,令觀眾深感震撼。這類歷史題材的動畫紀錄片具備對戰爭、死亡、暴力等內容的書寫功能,生命的厚度使其必然籠罩在沉郁之下,往往帶有一種人生的悲涼感,一種歷史的滄桑感。
動畫紀錄片通過動畫形象和整體敘事設計迅速實現了紀錄片創作者的價值立場和主觀判斷,傳達了紀錄片被塑客體的個性化闡釋。
(三)“間離性”
動畫紀錄片的獨特性還源于它帶給觀眾的間離感。“間離”原為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提出的表演方法,其目的是產生陌生感。在動畫中,觀眾需要在頭腦中將動畫影像轉化為可以理解的視覺信息,陌生感便在轉化過程中得以生成。動畫紀錄片與其他動畫作品的不同之處在于其材料層中含有真實的聲音,有時還會出現真實的影像。材料層中的真實與動畫的虛擬之間形成了一種矛盾的新奇感,而當觀眾欣賞與領悟作品意蘊時,它又逃不開動畫紀錄片本身立足于歷史事件和現實的問題,紀錄動畫的間離效果由此而來。當人們從被表現的主體轉而成為處于客位的觀察者,這種轉變帶給人們的差異化體驗正是藝術的超越現實之處[5]。
三、動畫紀錄片典例分析
2008年,二維動畫紀錄片《和巴什爾跳華爾茲》(如圖3),作為一部成功的反戰題材動畫紀錄片,影片幾乎達到了完整的紀實性。影片敘述了第一次黎巴嫩戰爭的真實事件,人物形象的個性設計、比例、面部神情都立求還原現實人物的狀態。影片中的道路、飛機、坦克等造型都極為寫實。
整部影片色調沉重、明暗對比強烈,導演用光影的效果來表達人物的心情,烘托影片沉重的氛圍,映射出人們的絕望與戰爭的殺戮與冷酷,奠定了整部影片沉重的歷史基調。
巧妙的配樂為影片錦上添花,制造出緊張的氣氛,引起了觀眾對歷史真實的猜想。導演將殘酷的殺戮畫面進行藝術處理,宛如舒緩的華爾茲,運用肖邦的古典音樂與戰爭中震耳欲聾的槍炮聲對比,畫面悲壯慘烈,體現出創作者對戰爭的不滿與諷刺。
此外,影片在夢境與現實間游刃有余的轉換,體現出動畫紀錄片打破空間與時間束縛的優勢,這是傳統紀錄片難以實現的。
BBC經典動畫紀錄片《恐龍星球》(《Planet Dinosaur》)(如圖4)堪稱三維動畫紀錄片的代表。該片向觀眾呈現了一個由恐龍統治的早已失落的荒蠻世界,片中全面闡述了亞洲、歐洲、北美洲、南美洲的二十種形態各異的恐龍。與以往通過黏土模型制作的所有恐龍形象不同,該片以計算機中準確的基本建模、精致的雕刻與繪畫為基礎,推敲恐龍的骨骼結構、皮膚質感、數量規模、重量、運動軌跡以及其他各種細節,制作中涉及到基本建模、FX(特殊效果)、Digital Matte繪畫、可視化預覽、3D效果等尖端技術。正是在高尖端的技術支撐下,遠古巨獸的神秘面紗才緩緩揭開。它們極富質感的褶皺的皮膚,殺氣騰騰泛著暗光的片甲,尖銳的布滿鮮血和肉屑的牙齒,乃至它們不經意間流露出的眼神,甚至是它們興奮與痛苦的嚎叫都被分毫不差地刻畫出來。
眾所周知,科學性一直是BBC紀錄片的核心,主創團隊收集了過去10年中大量關于恐龍的古生物學最新知識和信息,其中不乏以前發現卻難以呈現的研究成果,如今卻通過CG動畫全都完美地展現出來。
該片秉承紀錄片的創作手法,將戲劇性的故事演繹與古生物學的發現巧妙地融為一體。影片故事線索完全依據真實的恐龍化石考古發現推理而來,每一部分恐龍生存敘事的切入點都基于最新的科學考據成果。正如解說詞中所說:“然而長久以來,大眾對恐龍知之甚少,這些怪獸究竟是什么樣子的?它們的皮膚是什么顏色的?它們的眼神是否真如電影中那般兇狠?它們究竟是如何捕獵與繁衍的呢?剛剛破殼而出的恐龍寶寶也許不會那么兇巴巴的吧,會不會很萌呢?想要對這些問題有所了解,只去博物館看看泛黃的恐龍骨架、聽聽解說小姐不停重復的陳詞濫調可算不上是個好主意。”[6]動畫紀錄片的發展無疑為還原史前生物、地貌、歷史等提供了一個嶄新出口。
國產動畫紀錄片《大唐西游記》算是比較成功的作品,該片動畫人物形象生動逼真,劇情基本還原歷史。其人物原型均基于古代書畫中記錄的形象,可謂做到了角色的“真實”。該片主人公玄奘按年齡劃分為少年、壯年和晚年。觀眾深刻體會到了“生命成長的真實”。其中壯年階段的玄奘則是參考了《玄奘取經圖》中的形象。《玄奘取經圖》中的畫像,從年代和參考價值來講,都是最接近玄奘法師真實形象的史料。
老年的玄奘法師體態上比青年玄奘更顯佝僂。多年的游歷、飽經歲月的洗禮也都通過滄桑的面頰顯露無疑。晚年的玄奘法師經歷了西行取經的歷練,迎來了佛法弘揚的輝煌,不僅受到君王的褒獎,更被后世敬仰。這些閱歷通過玄奘神情的微妙變化,使我們看見了從容和寧靜。
片中另一個重要角色是李世民,其原型參考了《唐太宗寫真圖》。片中李世民的帝王風采,開國之君的文韜武略,人物面部表情的英明神武,目光如炬及儀態的從容,都展現得淋漓盡致[7]。
此外,《圓明園》《大明宮》等大型國產動畫紀錄片也口碑不俗,它們或是展示我國歷史建筑、文物,或是運用“以物說史”的方式講述人物、事件及其觀點。片中特效純熟,再現了歷史更迭、人物命運的變遷。動畫紀錄片在更好地表現生活真實,提高紀錄片的敘述能力,在真實性的基礎上,更直觀地將真實推向真理。直觀的動畫形象在紀錄片中的恰當運用,能讓觀眾及時捕捉到真實信息。動畫紀錄片是對紀錄片的一種革新,革新不能一蹴而就,但卻能一步步獲得大眾認可[8]。
四、 總結及展望
為動畫紀錄片做界定并梳理相關理論是有必要的,但我們更應用包容與開放的眼光來看待動畫紀錄片這種獨特影像類型,動畫紀錄片讓觀眾產生的“真實之感”并非哲學上的“絕對真實”,固執地糾結于動畫紀錄片是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紀錄片只會使動畫的發展走向狹隘的道路[9]。
動畫紀錄片具有紀錄片的紀實性和動畫片的藝術性的雙重屬性。在動畫紀錄片中呈現為兩種藝術形式的彼此借鑒、互相促進的狀態。動畫技術解決了傳統紀錄片素材有限的問題,并迎合時代審美需要,為紀錄片的可看性提供了新的元素,動畫技術形象調節了傳統紀錄片觀看過程的沉悶氛圍,為紀錄片帶來了更具創新意義的審美效果。從效率的角度看,動畫技術還能極大地節約制作成本,縮短制作周期。
動畫紀錄片的爭論現象在西方國家其實并不多見,一則“動畫紀錄片”一詞最早源自西方,國內爭議不斷,可能與“動畫紀錄片(Animated documentary)這一外來術語的翻譯有關。二則國際上各大專業組織機構也為動畫紀錄片開設獨立單元表現出對動畫紀錄片形式的認可,如萊比錫電影節為其設置了獨立板塊,謝菲爾德紀錄片電影節也開辟出了獨立單元等。而反觀國內動畫紀錄片,可謂是在風雨中坎坷成長。筆者認為,動畫紀錄片不僅發揚傳承傳統,更是一個向世界觀眾展現中國文化的良好平臺。就此,希望業界對動畫紀錄片這一形式多加包容與指正、鼓勵與幫助,在堅守“底線”與原則的基礎上發展動畫記錄片,使紀錄片、動畫兩個領域都更加豐富多彩。
此外,以往人們在談及動畫紀錄片時只是將動畫作為紀錄片的一種表現形式,卻忽視了將動畫作為題材內容來討論。傳統對紀錄電影的分類,一般分為政論紀錄片、生活紀錄片、時事報導片、歷史紀錄片、舞臺紀錄片、傳記紀錄片、人文地理片和專題系列紀錄片等。還未曾將動畫影片的制作過程本身,以及與動畫制作有關的工作層面的真實當作記錄對象,希望未來以此為表現對象的紀錄片,也能成為一種新的發展方向。
參考文獻:
[1]胡立德, 王雪歡. 紀錄片和動畫片:關聯與分界[J].中國電視,2014(11):68-72.
[2]劉玉亭. 動畫紀錄片艱難的發展歷程及展望[J].影視制作,2017(5):87-90.
[3]袁夢.何謂紀錄片——淺談紀錄片的“真實性”[J].戲劇之家,2019(12):98.
[4]張馨予.紀錄片的真實性與藝術性探討[J].傳播力研究,2018,(20):51.
[5]朱逸倫.論紀錄動畫及其美學特征[J].當代電視,2019(5):47-50.
[6]紀錄片《恐龍星球》:帶您親歷恐龍為王的世界[EB/OL].[2012-11-01].http://jishi.cntv.cn/20121101/100212.shtml.
[7]閆志遠. 動畫與紀錄片形式的完美結合——探析《大唐西游記》成功之道[J]. 名作欣賞,2015(15):68-69.
[8]彭國華, 陳紅娟. 以紀錄片《圓明園》與《大明宮》試論“動畫紀錄片”[J]. 時代文學(上半月), 2010(6):221-221.
[9]尉天驕,吳思媛.動畫對紀錄片“真實”的解構、顛覆與重構[J].新聞愛好者,2012(12):69-70.
作者簡介:姜仕燁,天津美術學院藝術學專業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