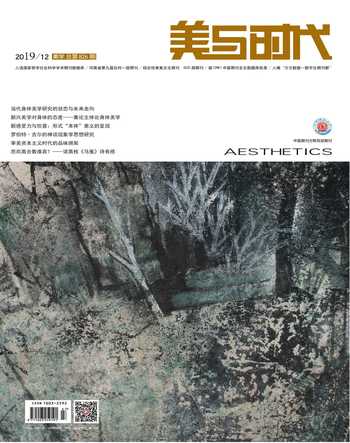誘惑:從美學階段到自我解構的升華
摘? 要:20世紀身體美學的異軍突起,拓寬了尼采關于身體覺醒的理論,而后克爾凱郭爾在《論誘惑》中對美學階段的身體進行了解讀。結合鮑德里亞身體消費的觀點,將誘惑顯現為身體的感性行為,具有美學和誘導真理的作用,在社會場域中凸顯后現代的解構特征,形成了身體、精神、信仰的三重誘惑。在電影《我不是藥神》中,文牧野導演將誘惑進行了分層解讀,分為程父住院的身體誘惑與呂受益之死的精神誘惑,以及程勇如耶穌般拯救世人的信仰誘惑。同時,電影更呈現了誘惑深層次的本質,后現代的鏡像理論,在現實與虛幻、矛盾與救贖、人性與本真等鏡像關系之間搭建了一座橋梁,從而闡明二元對立固有場域的出路,自我解構對人神性的升華。
關鍵詞:我不是藥神;誘惑;美學階段;鏡像理論;升華
一、美學階段的誘惑:身體、精神、信仰
存在主義哲學的先驅克爾凱郭爾把人存在的諸種形態分為“美學”“倫理”“宗教”三個階段,也就是說人只能以感性、理性或信仰的方式存在。他將誘惑分為唐璜的肉體誘惑與約翰尼斯的精神誘惑,以及耶穌間接誘惑亞伯拉罕的信仰誘惑。在這里,克爾凱郭爾注意到了身體維度的重要性,拋棄了古希臘哲學對身體貶斥的態度。
作為身體美學的代表人物,理查德·舒斯特曼強調了凸顯執行性品格的“實踐身體美學”,表現出對身體意識的關懷,并在分析美學的譜系學、社會學和文化分析中彰顯了其獨特的意義。由此,從哲學上身體話語權的轉移,我們明白了身體符號對現代以及后現代社會的重大意義。而在《我不是藥神》里,程勇一開始便受到身體意識的誘惑。
電影一開場便是一位頹廢的男子——程勇在臟亂的小店賣印度神油,也就是俗稱的壯陽藥。這一幕,仿佛是對這個物欲社會的批判,身體欲望引發的物質消費,誘惑程勇走上了這條道路。然而,令程勇沒有想到的是,現代社會物質欲望過于強烈,導致消費產品快速更新換代,印度神油已經很少有人用了。面對著老板的催租、前妻的嘲諷指責,苦苦掙扎的程勇徘徊在現實社會的邊緣,一度陷入迷茫與崩潰。
在進入市場前,程勇的認知是基于身體欲望消費的理念,這里主要是女性對男性誘惑的消解游戲。而后,失去這種誘惑模式的生存空間,迷茫期的程勇,受到了男性呂受益身體與金錢方面的誘惑。然而在法律面前,程勇還是有所顧忌。正巧程父重病在床、急需開刀,在渴望父親身體康復的誘惑下,程勇走上了走私假藥的犯罪道路。
電影雖然是戲劇化沖突,然而藝術理論卻源于現實,作為小人物的悲劇,或許最初便是俄狄浦斯般的命運遭遇,身體只是悲劇的一個伏筆。為了得病的女兒活著,劉思慧不得不出賣身體,在夜店誘惑男性而換取金錢。為了報答程勇贈與的格列寧,用身體去消解他的欲望。同樣,為了身體能夠存活,呂受益等一大批白血病人不得不依附于賣印度神油的程勇,這體現了身體生命的本能。正如影片中白發老太太對刑警曹斌所說的:她只是想簡單地活著,沒有人想拖累家人,也沒有人想去死。活著,就是生命的本質,所以病人們為了活著竭盡全力地去誘惑程勇。
然而,在物質獲得了滿足之后,程勇選擇了激流勇退,火鍋店里眾人的分開便是本劇的一大高潮,為接下來人物的轉變以及呂受益的精神誘惑埋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程勇不是救世主,他只是為了利益而去印度買藥,而當他一步步完成資本的積累,變得很有錢時,曾經的戰友呂受益瀕臨死亡。面對著呂妻撕心裂肺的求助,以及衰老不堪的兄弟,程勇的惻隱之心萌動了,他也開始進行人性的自我批判與反思:活著,人該怎樣活著?呂受益的死亡極大地打擊了程勇,這同時也是一種精神誘惑,程勇開始了他人性的轉變。
接著,程勇將這種態度的轉變付諸實際的行動。將格列寧這種藥原價甚至貼錢出售,他擺脫了感性與理性的認識,為精神誘惑而服務社會。在善的誘導下,一直看不起他的黃毛又回到了他的身邊,并對他的拯救表現為一種信仰,如亞伯拉罕般追尋著真理與上帝。最終,在這種信仰誘惑下付出了生命,構成了悲劇的崇高美感,給予人與社會極大的震撼力量,完成了自我與他我的拯救。
二、后現代鏡像理論——二元對立的關系
拉康認為,鏡像理論是指將一切混淆了現實與想象的情景意識稱為鏡像體驗的理論。除了身體推動電影敘事之外,《我不是藥神》中的鏡像關系也促進了故事的走向。
在電影中,現實主義與虛幻主義的手法不斷交叉運用,形成了一個二元對立又統一的關系。電影的開頭有這么一幕,即程勇答應呂受益去印度時比較歡笑的場景,并與后來呂受益死后程勇再去印度購藥時,出現的一些佛像、迷霧、幻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電影通過藝術化的手法,將現實與想象結合起來,這使得情感更加具有爆發力。如影片結尾時程勇坐上警車在人群中看到了黃毛和呂受益,這種虛虛實實、亦真亦幻的手法給人以極大的震撼。
同樣,矛盾和救贖也是本片的另一大鏡像關系。程勇一開始只是一個市井小民,他并沒有那么高的思想覺悟,賣藥只是為了掙錢,這也注定了之后的過程肯定充滿了矛盾。影片中程勇與自己是有矛盾的,在掙錢與道德之間他時常徘徊不定,甚至為了自己的將來,中途停止販藥,可以說背叛了最初的幾個人。而且,也正是程勇的收手,使他與呂受益有了矛盾,并且間接導致了呂的死亡。由此,觸動了程勇的惻隱之心。正如三字經所說的:“人之初,性本善。”程勇的這種蛻變也不是一時完成的,是與矛盾做了無數的斗爭,最后終于完成了救贖。
我們從程勇的故事里可以看到很多東西,比如人性,比如本真。一部優秀的電影刻畫的社會必然是現實的,描繪的人物是飽滿的,既有底層小人物的生活,又有代表著大資本主義的諾瓦制藥公司,還有警察、商人、牧師等一系列人物。可以說,電影是現實主義的,是具有后現代特征的。正是在這種基調下,人性被解剖得淋漓盡致。假藥販子張長林就說過這么一句話:這世界上只有一種病,那就是窮病。人性充滿了貪、惡、欲,以及佛家的八苦,很少有人能夠超脫。如諾瓦公司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不顧人民死活;張長林、程勇看到商機,販賣假藥;病人為了活命,吃垮了家里的房子、車子;警察為了破案,顧不上百姓的生存一幅幅赤裸裸的畫面。而影片為了照顧觀影人的感受,這種深不見底的人性還是被弱化了的。似乎,社會充滿了壓抑、絕望。
然而,盡管這樣,人性最終還是戰勝了丑惡,往最本真的一面前進。假藥販子張長林被抓時,沒有供出程勇;程勇最后虧本給病人去印度買藥;警察曹斌良心不忍,放棄去抓捕藥販;當程勇被抓時,長路上站滿了人,所有病人都脫下了口罩,那是對一個英雄的敬意。
三、自我解構:從悲劇、誘惑中升華的神性
本片有很多幽默搞笑的情節,如程勇為賺錢去印度代藥, 和賣藥之人討價還價、隨口爆臟話的情節以及劉牧師被逼著用英語和印度賣藥公司交涉, 程勇逼夜店經理跳鋼管舞,黃毛剪掉頭發等片段,令人捧腹大笑,但在笑聲背后實則蘊含著深刻的悲劇因素。
首先,利益與道德的困境。影片通過程勇在利與義的道德困境中的掙扎、搏斗揭示了悲劇意義的崇高性。程勇的每一次選擇都伴隨著內心激烈的搏斗。其次,民情與法律的困境。影片《我不是藥神》便沿襲了古希臘這一悲劇傳統。程勇低價甚至虧本為病人代購格列寧, 既是救人的義舉, 卻也犯了走私罪和販賣假藥罪, 兩者之間, 程勇選擇了“情”。警察抓程勇時, 一位患病的老奶奶懇請法律能夠網開一面, 此乃“情”。警察曹斌面對眾多病人的懇求, 于心不忍, 在“情、法”之間備受拷問, 情與法的沖突被推到了極致。最終“法”戰勝了“情”, 程勇被判入獄。“法”困住了程勇, 卻也呈現出了程勇內心世界的崇高。還有,窮與病的命運困境。黃毛、呂受益以及其他慢粒白血病患者, 他們必須不間斷地服用格列寧, 一旦停用, 生命即刻便會受到威脅, 然而他們的家庭條件難以支撐高昂的費用。他們便在這窮與病的困境中苦苦掙扎, 企圖與命運進行抗爭。
《我不是藥神》中充分展示了人所面臨的三大困境,以及社會、他人、自我造成的悲劇。而在人類的歷史上,悲劇是一個永恒的主題,從古希臘時期開始,悲劇就彰顯了它巨大的意義。也正是因為悲劇,人物展示出了一種崇高美感的悲劇精神,最后人性得以升華,上升為神性的特征。而一旦形成這種神性,反過來又對他人進行精神誘惑,從而完成雙向的升華。
在影片中,程勇最后的轉變給人帶來了極大的震撼,他在自我救贖的同時,也在救贖著他人,實現了從身體到靈魂的全面救贖。他如布道的耶穌一般拯救世人。程勇在矛盾中蛻變,在悲劇中升華。他身上帶有崇高美感,而影片中另一個悲劇又崇高的人物是一直跟著他的黃毛。
黃毛從一開始就是個徹徹底底的悲劇,從小被家人拋棄,沒有關愛。并且自身也是白血病患者,身處底層,沒錢買藥。是一個從身體到精神都是悲劇的人。然而,他有一顆善良的心,雖然屢遭不幸,但對生活還是心懷希望。在遇到程勇后,由一開始的看不起,到后來受到精神誘惑,心甘情愿地為程勇的逃脫付出了生命,從而完成了由悲劇向崇高的轉化。可以說,黃毛是本片中另一個極具美感的人物,是程勇的另一面。他們互為鏡像,相互誘惑,最終都走向了神性。
四、結語
自電影產生以來,取自現實題材的電影不在少數,但大部分都不具有像《我不是藥神》這樣崇高的悲劇美感。魯迅先生曾說過,悲劇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通過《我不是藥神》這部影片,我們見識了人性的矛盾與崇高。在觀影的同時,也在鏡像中看到了另一個自我,從而開始反思、解構存在的意義。
參考文獻:
[1]尚景建.誘惑:從“美學階段”到后現代鏡像——論鮑德里亞對克爾凱郭爾的解讀[J].文藝理論研究,2017(5):185-202.
[2]田雅麗.含淚的笑——從劇作的角度分析《我不是藥神》[J]. 戲劇之家,2018(31):85.
[3]程孟輝.西方悲劇學說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2009.
作者簡介:袁兵,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美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