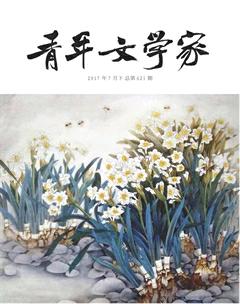從鏡像理論與人格理論看田耳長篇新作《天體懸浮》
索果++彭在欽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新世紀中國長篇小說創作的現代性與本土化路徑研究(編號:13YJA751039);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編號:13YBA149)。
摘 要:田耳新作《天體懸浮》給讀者留下關于“善念”的思考:物欲與人道的交織,人性變得敏感、脆弱,但這不能成為善念缺失的理由,善念是物欲橫流的世界里維持靈魂純凈的良藥,也是心靈救贖的良方。拉康的鏡像理論和佛洛伊德的人格理論對人性、善與惡、法律與道德的界定給人以啟示,在生命的天平中,每個人的選擇和境遇有所差異,甚至會分道揚鑣,走向命運天平的兩頭,但維持和傳播善念是人類的天職,它應嵌入人的靈魂,因為在蒼穹之下,生命太渺小,唯有善念才是永恒。
關鍵詞:天體懸浮;鏡像理論;人格理論;善念傳播
作者簡介:索果(1992-),女,貴州平塘人,湖南科技大學教育學院研究生,主要從事語文教育與文學評論工作;彭在欽(1964-),男,湖南瀏陽人,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現當代文學學科、戲劇與影視學學科帶頭人,碩士生導師,湖南省現代文學學會副會長,主要從事當代文學與影視文學、語文教育研究工作。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21-0-03
湘籍作家田耳的新作《天體懸浮》以符啟明與丁一騰這對基層派出所的“患難兄弟”為故事主線,講述兩位基層派出所非正式工作人員的生活史和成長歷程,并以二人的生存環境的變遷側面呈現出當今社會不同階層的生活狀態,作品中,田耳通過“競爭編制”、“打野食”、“放狗”等諸多事件埋在伏筆,兩位性格迥異的主人公隨著故事情節的發展逐漸走向生命天平的兩端。從埋藏在作品中的暗線可以看出,作品在人物塑造、情節結構等方面通過鏡像理論和人格理論可以獲得一個獨特的視角欣賞這部關于靈魂和人性的佳作,同時,作者獨特的筆法和樸實的語言,從不同的視角描述了當今社會底層人民的生活狀況,小說中,還有許多考驗人性的臨界點,不僅觸發讀者的思考,而且也給讀者留下了極大的思考空間。接下來,筆者把鏡像理論和人格理論作為切入點,分析、評價《天體懸浮》。
一、鏡易圓,人難圓
拉康的鏡像理論提出,嬰兒的自我認識階段有三個時期,即前鏡子時期,鏡子時期,后鏡子時期。此理論將主體的形成過程分為現實界、想象界和象征界三個階段,并依次遞進最終構成一個有意識、有感知的理性主體。如果三個階段的順序顛倒,則意味著主體從理性陷入非理性,直至無理性,這個過程其實就是個體精神分裂的過程,并最終導致個體進入現實界[1]。用拉康的鏡像理論分析《天體懸浮》,可以反證出人物的性格特點和歸宿,這也是小說的亮點所在。小說的主人公符啟明十分圓滑,他仿佛天生具有某些“超能力”,許多看似不可能的事,他都能辦成。他身具“拉皮條”的能力,能把有限的人脈和社會資源盤活,通俗地講,這是一位白道與黑道通吃的角色;而丁一騰正好相反,與符啟明相比,丁一騰的老實和木訥更加襯托出了符啟明的靈活和圓滑,這也從側面反證了符啟明是條“道士命”。
象征界的特性是欲求,它是主體進入“象征界”的動力。作品中,主體進入“象征界”的過程就是認同“道士命”的過程,也就是說符啟明內心不僅接受了自己是“道士命”,而且他的言行都遵從“道士命”特有的標準,例如:在與人相處的過程中,要讓別人對自己形成“依賴”和“崇拜”,當你讓別人為你做事時,別人不僅會竭盡全力地幫忙,而且還會對你千恩萬謝;男人一定要“壞”,適當地放出信號,這樣才能俘獲芳心……雖然他擁有很強的社會性,諳熟江湖規矩,頭腦靈活,但由于生活環境和階層所迫,他不得不背井離鄉來到佴城尋求生存空間,后因欲求過勝,肆意發揮人性的惡意,觸碰了人性和法律的底線,導致靈魂走向魔道,正因如此,他才沉迷于觀星的愛好中,或許,在符啟明看來,這是自我救贖的一種方式。而丁一騰恰好相反,他在生命行走的過程中,一直航行在“正義”的航線中,所以,他能從天平的混沌區走向天平的另一端。在想象界階段中,符啟明與丁一騰處于混沌區,由于存在一些非理性因素,他們互相認可對方的生存方式,符啟明欣賞丁一騰的品格,丁一騰則對符啟明五花八門的生意經和三教九流的人脈產生認同。正因處于一個混沌區,兩人一直曾有游離于天堂與地獄之間。在現實世界,二人的人性正式走向分裂,一個成為律師,另一個則成為長期從事各種社會非法活動的首腦。
在鏡像理論中,若是現實界、想象界和象征界三個階段的順序倒置,則導致個體精神分裂,把此理論用于分析這部作品恰好證明了符啟明對自己命運的定義——道士命,這是小說的關鍵點。若按常規的情節發展,洛井派出所轉正的編制應該是符啟明的,但因他擁有道士命“能折騰、愛折騰”的特點,才把小說引入高潮。這是田耳的高明之處,他“就子打子”,把即將順勢流下的溪流,導入另外一條河流,最后,小說的結局如同丁一騰說的一樣:“人與人的關系便是那么微妙,稍微一個眼神不注意,就會產生隔閡。”雖然二位主人公并未在語言上撕裂,但內心早已被各自的信仰隔開,這是一條永遠都跨不過洪流。盡管開庭前,符啟明開誠布公地與丁一騰談話、交底,但二人終究是回不到過去了,就像丁一騰再次遇見沈頌芬,符啟明找到小末一樣,信仰不同,如何能再如往常一樣飲酒、作詩、觀星,畢竟,靈魂陷入歧途是無法拯救的。所以,保持善念,傳播善念,并把它鑲入靈魂里,生命才變得有意義。
二、勘探人性,救贖靈魂
人性是生命中最珍貴、最稀有的品質,也是生命中最灰暗、最見不得光的部分,它既有真、善、美,也有丑、惡、毒,它是生命中最難界定的一部分,所以說,人性是復雜的。《天體懸浮》中的兩位男主人公即是人類個體的代表,也是人類整體的代表,人類與動物的區別就在于“人性”,而人性的界定往往是最復雜,最混沌的,丁一騰與符啟明是生命天平兩端的代表,他們也是在混沌中逐漸摸清自己的人生軌道,從而一步步走向分裂。佛洛伊德的人格論、善與惡的交錯對人性的勘探、靈魂的救贖是很好的證明。
(一)人格論
佛洛伊德的人格論提出,本我、自我、超我構建成完整的人格,個體的發展以“本我、自我、超我”作為標準,在這三者的關系中,本我和超我分別是個體生物性和個體精神境界的體現,二者由自我連接,在小說中,符啟明與丁一騰的人物性格,從某種意義上就是本我和超我的體現。符啟明是一位物欲很強的人,他油嘴滑舌、濫情、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與丁一騰的正義、陽光相比,符啟明的性格顯得有些黑暗。但從另外一個角度而言,符啟明的角色更接近與本我狀態,丁一騰的角色接近超我狀態,二者的人格狀態綜合起來,十分接近現實生活中個體的本質狀態。人是具有多面性,從本我到超我,需要經過中間地帶,同樣,處于生命天平兩端的符啟明和丁一騰中間也有中間地帶,在這里二者目睹三教九流的嘴臉,也體會了人性脆弱、自私的一面,所以,作者把觀星的情景作為小說里人物自我救贖的過程。小說是從第三人稱“我”(丁一騰)的角度展開,從“我”第一次觀星到把望遠鏡送給初戀情人沈頌芬的過程,每一次觀星都是對觀星者的救贖。浩瀚無邊的星空是對觀星者最好的釋放,只有在星空面前,才知曉個體的渺小,渺小到猶如塵埃。
觀星是令人敬仰的行為。仰望星空,勘探宇宙,把宇宙一剎那便閃過的美麗用相機定格成永恒,把浮躁的當代人帶到靜謐浩繁的神秘世界,闊別塵世的渾濁與欲望,以是,“觀星”在小說是靈魂救贖的一種方法。“我”第一次觀星是在小末、符啟明和沈頌芬的鼓舞下開始的,當時,丁一騰和符啟明還是洛井派出所的輔警,天天與管轄區內的三教九流打交道,這個階段也是二人關系最好的時刻。“我”最后一次觀星是與符啟明一起,當時的“我”并不知道,符啟明正在策劃一起殺人計劃,而“我”則成為了兇手不在場的證明人。其實,在這之前“我”與符啟明已分道揚鑣,但丁一騰與符啟明最后一次觀星是本部小說高潮部分。小說中,在丁一騰最后一次與符啟明觀星時,符啟明拍下丁一騰觀星的背影,這一部分作者沒有過多地對人物和環境進行描寫,只是通過“我”的闡述表達,星空竟然會有不同的顏色。從某個角度來說,這是丁一騰的靈魂與符啟明的靈魂徹底走向生命天平兩端的標志,曾經的兄弟,其中一位通過不斷地努力成為法律的代表,從執法者變成掌握殺生權的律師;而另一位,從法律者釀成經濟罪犯、淫穢罪犯、殺人犯。符啟明為滿足個人的生存欲望,無原則,無底線地采取非法手段獲得利益,體現出了符啟明的生物性,為了生存而生存。雖然,丁一騰屢次遭受生活的壓迫,但他一直努力朝自己的目標靠近,直至實現目標,他是小說中唯一擁有穩定家庭的人物,這更加能襯托出丁一騰內心的光明。當輔警時抓粉哥、粉姐,抓小偷,打擊賭徒,丁一騰的工作對象無不顯示出人性灰暗、向下的一面,盡管在這樣的環境中,丁一騰依然保持這積極、平和的心態去面對生活,這些都表現出了丁一騰內心的陽關。
上文中,即論述了符啟明人性里的物欲、貪念、灰暗面,也論述了丁一騰積極、平和、正義、陽光的人格,一個是本我的代表,一個是超我的代表,著眼于現實生活中,這即是對生活的描述,更是對個別、對人道的描寫,與其說,《天體懸浮》主要講述符啟明和丁一騰的故事,還不如說本書講述了現實生活中個體的人性以及善與惡的一面。人性的善與惡,簡而言之,就是對原欲的控制程度,蘇妹子、夏新漪、春姐等人的墮落和不自愛,在原欲的誘惑下,她們沒有把握住女性的底線,誤入歧途后,她們一步步深陷犯罪的泥潭,以至于徹底失去底線和人性。
(二)善與惡
“善與惡”是人性中最尖銳的矛盾,就如小說中的符啟明,他利用執法權利謀取利益,同時,也為一些無業游民提供了就業機會。如他開娛樂場所,雖然存在一些非法交易,但是也為王寶琴這類窮人家的單純女孩提供就業機會,即使這些崗位與公務員、教師等正式的工作相比缺乏主流性,但與春姐、夏新漪、蘇妹子這類人相比起來,王寶琴要正派一些,而且,王寶琴也是通過這份工作,獲得了好歸宿,從某種程度上說,符啟明也算是做了好事,但整體而言,符啟明也做了不少壞事,所以,小說中符啟明是一個復雜的角色,他無所謂好壞,他人性里的特質,留給讀者們更多的思考空間。這也啟示讀者,對待生活中的“符啟明們”,既需要有對人、對事與人性深刻而犀利的洞察力,也需要有大氣而精微的筆燈燭照。這不僅僅是由人情世界的復雜性決定的,也是因男人之間義與利關系難以把捉使然[2]。
小說中的另一位人物伍能升同樣也游離于“善與惡”的邊緣,為了維護母親,在新仇舊恨的“唆使”下,親手殺死母親的情夫。從善的角度來說,他不可取,畢竟性命關天;從惡的角度來說,他這么做無可厚非,一個男人難以忍受一位侮辱親父,傷害親母的人,所以在看到母親的情人從肉體上傷害母親時,伍能升心生惡意,沖擊房間里把母親的情人殺害。從此角度出發,伍能升也是一位很復雜的人設,他仿佛被夾在道德與法律之間,難以從他的行為對他進行判斷。
(三)責任與道德
在小說的尾聲,作者通過語言描寫、動作描寫、環境描寫,把符啟明與丁一騰內心最敏感的情感表達出來了。作者的高明之處在于,沒有直接對二位主人公內心的獨白進行描寫,而是把“責任與道德”作為試紙,把二位主人公的內心世界展現出來。
符啟明深知自己難逃法網,便邀請丁一騰前往廣州,并向丁一騰攤牌多年前的事實,讓丁一騰知曉事情的真相,同時,也暗示丁一騰陷害安志勇的緣由,符啟明做出這一系列決定的動機,既有對初戀的愛,也有對安志勇的嫉妒和恨,更多的是對道德的誤解。他認為,自己這么做是在幫助馬氏父女,但他忽略了一點:生命的不可侵犯性。無論出于何種理由,抱著何種目的,生命都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更不能以“道德”的名義,剝奪任何人的生命,何況,還是通過帶有侮辱性的方式讓馬桑自行結束自己的生命,這樣的做法違背人性,違背道德,無論是從人道主義的角度,還是法律的角度,這都是不可取的。
一直行駛在正義道路上的丁一騰也面臨一場道德和責任的考驗。符啟明的案子結束后,丁一騰不想讓妻子王寶琴過渡迷戀觀星,便把符啟明送的望遠鏡送給初戀女友沈頌芬,沈頌芬借此機會制造了一場與丁一騰獨處的機會,丁一騰險些“失足”,慶幸的是在誘惑面前,丁一騰最后選擇了責任,他想起自己的女兒和妻子,清楚家庭的重要性,所以,在誘惑面前,他選擇了家庭、責任、道德。
通過上述比較,可以看出,丁一騰與符啟明最大的差異就在于靈魂的差異。與其說這是命運給二人的安排,不如說是二人的選擇和人性造成的。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具有“人性”,既然具有人性,那么必定會有強烈的生存觀,在物欲橫流的社會中,底層人民的生存空間本來就狹小,所以他們對物欲的需求也十分強烈,只有充足的物質才能支撐起整個家庭,才能獲得相對寬闊的生存空間,這一目標不僅是符啟明與丁一騰所追求的,也是許多底層人民的追求,但需要強調的是,追求物欲的同時,不可丟掉人性,這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失去人味,也就失去了底線、原則和道德。失去道德的控制,就容易做出一些冠冕堂皇的事情,活著也猶如行尸走肉,毫無意義,這也是小說留給人們的反思人性空間。
這部小說的亮點在于,作者通過平角視角,以一種平淡的心態來描述底層人民的生活狀況,給讀者呈現出了底層人民最真實的生活狀態和心理動向,同時,作者打破了公安題材小說的常規,沒有可以去丑化、惡化任何一個人物形象,而是通過許多側面描寫和反證的方式,把評價的標尺交給讀者。在小說中,人性兩端的灰色地帶、法律與道德的灰色地帶被展現得淋漓盡致,兩性間的欲望、物質的欲望、人與人之間的惡意作者都以一種平淡的口吻和心境一一展現在讀者面前,給讀者留下廣闊的思考空間。最后,作者把角度引入星空,小說的格局直接被擴大,在浩瀚無垠的星空下,無論是人性、人道主義、江湖義氣、利益、恩德、抱怨、物欲……都顯得十分渺小,且輕如塵埃,仿佛唯有“善念”才是這個宇宙中最有分量,最永恒的信仰,同時,這也是作者想傳達給讀者的信念。結合當下的社會現狀,在物欲橫流的社會中,“功利、黑暗、利益、現實”似乎已經成為了社會主流,“善念”仿佛只存在于理想的烏托邦里,在現實的環境下,我們該如何發現善念、保持善念、傳播善念,這是《天梯懸浮》留給我們的思考。
參考文獻:
[1]胡朝霞 蔣天平.鏡像理論和倫理學雙重視閩下的《海爾格倫的海盜》[J].求索.2015.10—80.
[2]張永祿.含混的詩學:《<天體懸浮>解碼》[J].南方文壇.2016.2—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