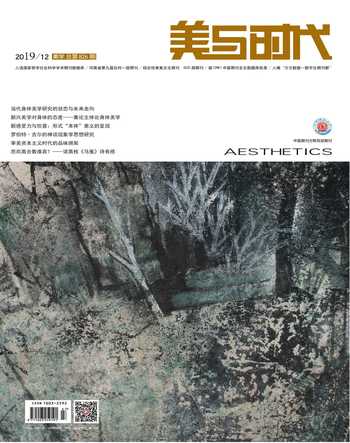梵高繪畫作品中色彩的澄明與遮蔽




摘? 要:從梵高的繪畫作品中可以看到,色彩將一個(gè)個(gè)世界“澄明”出來(lái),正是因?yàn)檫@一個(gè)個(gè)世界的“澄明”,才讓我們認(rèn)識(shí)到色彩本身的存在,那個(gè)“遮蔽”在作品世界后面的質(zhì)料,才“敞開(kāi)”在我們眼前。我們就是在這樣一個(gè)個(gè)“澄明”與“遮蔽”的爭(zhēng)執(zhí)間發(fā)現(xiàn)了“美”,而這“爭(zhēng)執(zhí)”的保持也讓梵高的作品得以永恒地以藝術(shù)作品的存在而存在。
關(guān)鍵詞:梵高;繪畫;色彩;澄明;遮蔽
畫廊的墻上,并排懸掛了大約七十到八十幅光輝燦爛的油畫,都是溫森特在阿爾、圣雷米和瓦茲河邊的奧維爾畫的。當(dāng)筆者驚詫不已地徘徊于一幅又一幅壯麗輝煌的油畫面前時(shí),便油然進(jìn)入了一個(gè)新的境界,整個(gè)世界豁然開(kāi)朗:人、植物、動(dòng)物從那富有生命感的大地升向富有生命感的天空和太陽(yáng),然后又向下會(huì)聚到同一中心的運(yùn)動(dòng)中,一切生命的有機(jī)成分都融合在一起,成為一個(gè)偉大崇高的統(tǒng)一體[1]1。讀到《渴望生活:梵高傳》中的這段文字時(shí)筆者內(nèi)心是激動(dòng)的、共鳴的,那種對(duì)色彩的驚嘆是共通的。電影《至愛(ài)梵高》中流動(dòng)的光影、極具沖擊力的色彩又一次浮現(xiàn)在眼前,那種無(wú)法用概念來(lái)言說(shuō)的美深深地抓住了筆者。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提出了四大審美判斷要素:無(wú)利害而有愉悅、無(wú)概念而有普遍性、無(wú)目的而有合目的性、無(wú)推理而且有必然性,而這樣一種美,在梵高的繪畫作品中體驗(yàn)到了,在《渴望生活:梵高傳》的文字里體驗(yàn)到了。
筆者無(wú)法用短暫、悲愴、輝煌來(lái)形容梵高的一生,合上書本,記憶最深刻的是他對(duì)生活的渴望、對(duì)真實(shí)的渴望。這樣的渴望散落在他的每個(gè)人生階段里:散落在倫敦,在他對(duì)羅伊爾純粹真誠(chéng)的初戀里;散落在博里納日,在他對(duì)煤礦工人們無(wú)私又無(wú)望的布道與救治里,在他放下《圣經(jīng)》拿起畫紙和顏色的歡喜里;散落在埃頓、在海牙、在鈕恩南、在巴黎這一個(gè)個(gè)他對(duì)繪畫技藝的探索和學(xué)習(xí)的地方;散落在阿爾,在狂熱的黃色、濃烈的藍(lán)色、純粹的綠色間;散落在圣雷米的《星夜》《奧維爾教堂》的藍(lán)色里。正是帶著這樣的渴望讓他找到了自己獨(dú)特的色彩,而這些色彩不再是毫無(wú)生機(jī)的顏料,而是梵高對(duì)生活的渴望。當(dāng)人們?cè)谛蕾p這些色彩時(shí),看到的不再是作品存在的質(zhì)料——顏料,而是進(jìn)入那個(gè)作品所打開(kāi)的世界,當(dāng)這個(gè)世界被打開(kāi)時(shí),作品的質(zhì)料也在這個(gè)作品的世界中被“澄明”了。
一、澄明與遮蔽:海德格爾的美學(xué)思想
“澄明”是海德格爾最早在《藝術(shù)作品的本源》一文中提出的[2]10。海德格爾認(rèn)為,“在存在者整體中有一個(gè)敞開(kāi)的處所,一種‘澄明在焉’(Lichtung)。這個(gè)敞開(kāi)的中心并非由存在者包圍著,這個(gè)光亮中心本身就像我們所不認(rèn)識(shí)的‘無(wú)’(Nichts)一樣,圍繞一切存在者而運(yùn)行”[3]34。從這里可以看出,海德格爾所指的“澄明”不是指存在者的顯現(xiàn),而是指經(jīng)由存在者打開(kāi)的一個(gè)“世界”的顯現(xiàn)。
“遮蔽”一詞是在海德格爾《論真理的本質(zhì)》一書中被凸顯出來(lái)的,自此成為后期海德格爾的一個(gè)關(guān)鍵詞。經(jīng)由這一概念海德格爾提請(qǐng)出來(lái)的是一種“為無(wú)蔽保持著它的固有的最本己的東西”的狀態(tài)。這一狀態(tài)在《論真理的本質(zhì)》中被海德格爾冠之以一個(gè)頗玄乎的詞語(yǔ)——“神秘”。在《藝術(shù)作品的本源》中經(jīng)由“大地”概念的引入被說(shuō)成一種“自行鎖閉”狀態(tài)。無(wú)論詞語(yǔ)如何變換,海德格爾的意思都是要表明:此在的到場(chǎng)這一存在的澄明過(guò)程,同時(shí)是一個(gè)對(duì)“遮蔽狀態(tài)”進(jìn)行遮蔽的過(guò)程[2]12。
“建立一個(gè)世界和制造大地,乃是作品之作品存在的兩個(gè)基本特征。當(dāng)然,它們是休戚相關(guān)的,處于作品存在的統(tǒng)一體中。”[3]29藝術(shù)作品“建立世界”同時(shí)“制造大地”,就是將存在者的澄明與自然萬(wàn)物的遮蔽性質(zhì)同時(shí)凸顯出來(lái)。但是“世界”并非等同于“澄明”,而是處在“澄明”所謂的“敞開(kāi)領(lǐng)域”之中,“大地”也不直接就是遮蔽,而是具有遮蔽的本性[2]21。如此,藝術(shù)作品中的“世界”與“大地”都意味著一種敞開(kāi)。“世界”經(jīng)由農(nóng)婦的鞋敞開(kāi)為此在在世的勞作、苦難、煩擾、歡欣,即敞開(kāi)為此在的生存;“大地”經(jīng)由希臘神廟敞開(kāi)為巖石的笨拙、木頭的堅(jiān)韌、白晝的光明、天空的遼闊、夜的幽暗,即敞開(kāi)為自然萬(wàn)物的本然狀態(tài)。
二、梵高繪畫作品中色彩的澄明與遮蔽
梵高是19世紀(jì)荷蘭后印象派畫家的代表人物。色彩在他的繪畫作品中不僅是描摹造型的表現(xiàn)手段,更是與“世界”相連的窗口。梵高的色彩不是來(lái)源于外部的自然,而是來(lái)源于自己的內(nèi)心,他要通過(guò)色彩顯現(xiàn)的不是一個(gè)存在物,而是經(jīng)由這個(gè)存在物所打開(kāi)的世界。他將全部的情感都交付在色彩上,由色彩去顯現(xiàn)他對(duì)這一即將打開(kāi)的“世界”的全部熱情。我們就三幅梵高不同時(shí)期的繪畫作品《吃土豆的人》《夜間咖啡館》《星夜》來(lái)具體談?wù)勂渥髌分猩实某蚊髋c遮蔽。
《吃土豆的人》創(chuàng)作于紐恩南時(shí)期,這一時(shí)期的梵高還延續(xù)著荷蘭畫的傳統(tǒng),色調(diào)偏暗。彼時(shí)的他非常鐘情于繪畫農(nóng)民生活,鄉(xiāng)村景象。深色調(diào)的背景,大地色系的厚重,在作品中再現(xiàn)了農(nóng)民生活中所背負(fù)的艱辛。當(dāng)我們細(xì)細(xì)觀看這幅作品時(shí),一種深沉厚重的壓抑之感涌上心頭。畫面上呈現(xiàn)的是幽暗的燈光、做好一天工作的貧困農(nóng)家,坐在只放有土豆的簡(jiǎn)陋餐桌前,表情呆滯,視線投射在不同的地方,滿臉疲倦。四周是熏黑色的墻壁。畫中每個(gè)人物身上穿著的衣服是介于黑色與藏青色之間的深色,與四周墻壁的顏色相稱托。畫中唯一的明亮之處便是那盞油燈,而這盞油燈的光亮也僅僅只能照亮一家人吃土豆的桌子而已,桌子以外的地方都是和墻壁一般的熏黑色。燈光照亮之處,他涂成一種沾著灰土的、未剝皮的新鮮土豆的顏色,那是一種沾著灰土的顏色,絕不是上流社會(huì)那種光鮮亮麗、一塵不染、窗明幾凈的顏色。
這樣的色彩和明暗,將吃土豆的農(nóng)民的真實(shí)世界敞開(kāi)在作品中。它讓我們走進(jìn)了德格魯特一家的世界,但是我們看到的不是德格魯特家里的房屋擺設(shè),不是他們一家人的真實(shí)樣貌。當(dāng)我們進(jìn)入這幅作品時(shí),作品中這些對(duì)現(xiàn)實(shí)場(chǎng)景的描繪都被“遮蔽”了,作為作品存在的質(zhì)料——顏料也在這里被“遮蔽”了,而另一個(gè)“世界”“澄明”了,那是農(nóng)民的精神世界,這里的農(nóng)民已不再是布拉邦特的農(nóng)民,也不是德格魯特一家,而是任何一個(gè)有著相同精神世界的農(nóng)民。那種無(wú)奈、麻木、毫無(wú)生機(jī)的靈魂世界“敞開(kāi)”了。而當(dāng)這個(gè)世界被“敞開(kāi)”之后,作品的質(zhì)料——顏料并沒(méi)有消失,而是在作品的“世界”里敞開(kāi)了,我們看到了顏色的明暗對(duì)照、熏黑色的墻壁和沾著灰土的未剝皮的新鮮土豆的顏色都“澄明”了。正是因?yàn)檫@幅繪畫作品,開(kāi)啟了一個(gè)“吃土豆的農(nóng)民的世界”,作品的色彩顏料才以作品的存在而“敞開(kāi)”在那個(gè)“吃土豆的農(nóng)民的世界”里。只有當(dāng)作品成為作品存在的回歸之處——“大地”被敞開(kāi)時(shí),這幅《吃土豆的人》才稱得上是一幅藝術(shù)作品,這幅作品才可以作為藝術(shù)作品而存在。
《夜間咖啡館》是梵高在阿爾創(chuàng)作的。那個(gè)時(shí)期的梵高經(jīng)過(guò)了巴黎時(shí)期對(duì)色彩的探索,找到了屬于自己的獨(dú)特色彩,從暗色到暖色到夸張,這種強(qiáng)烈的色彩對(duì)比在這幅作品中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他在給弟弟的信中寫道:“我試圖表現(xiàn)出夜間咖啡館是一個(gè)場(chǎng)所,人在里面將會(huì)瘋狂,能做出犯罪的事來(lái);我通過(guò)柔和的粉紅色、血紅色、深紅的酒色和一種甜蜜的綠色、委羅奈斯綠相對(duì)照來(lái)達(dá)到目的。”[4]當(dāng)我們摒棄一切作品的說(shuō)明,將作品置于眼前,黃色的咖啡館的兩側(cè),稀稀散散的分布著三三兩兩的人,咖啡館內(nèi)冷清空蕩。老板獨(dú)自倚靠在偏離畫布中心的桌子邊,表情呆滯,而旁邊的客人,有的相并而坐、有的歪撐著頭趴在桌上或戴著帽子低著頭。一種令人躁動(dòng)不安的,刺激性的空氣,在咖啡館內(nèi)來(lái)回?cái)噭?dòng)。
梵高雖然描繪的是真實(shí)的夜間咖啡館的場(chǎng)景,但是他并沒(méi)有進(jìn)行單純的現(xiàn)實(shí)模仿,而是在他的繪畫中通過(guò)改變空間的結(jié)構(gòu)布局和顏色的搭配將一種熱烈、躁動(dòng)、危險(xiǎn)、不安、頹靡、陰森、瘋狂感覺(jué)暈染到了極致,將阿爾這座小城人民的精神世界“澄明”在我們眼前,而真實(shí)的咖啡館的場(chǎng)景被“遮蔽”了。觀者不會(huì)追問(wèn)這幅作品是否如實(shí)地描繪了當(dāng)時(shí)的場(chǎng)景,而是開(kāi)啟了一個(gè)情緒鮮明的精神世界,人們可以從這個(gè)被開(kāi)啟的世界去窺探那個(gè)整日遭受烈日酷曬、狂風(fēng)鞭撻的阿爾地區(qū)的人民的內(nèi)心世界,或者開(kāi)啟的根本就是梵高本人的內(nèi)心世界,人們甚至可以不去追問(wèn)這間咖啡館的所在,不去追問(wèn)這是誰(shuí)的世界,便被帶入了那個(gè)躁動(dòng)、瘋狂的世界。而被“遮蔽”了的色彩在這個(gè)世界被“澄明”之后也被我們捕捉到了,我們捕捉到了“紅色”的血腥與危險(xiǎn)、“黃色”的躁動(dòng)與不安、“綠色”的陰森恐怖,被隱現(xiàn)的色彩在這個(gè)被開(kāi)啟的精神世界里“敞開(kāi)”了。顏料熠熠發(fā)光,我們看到了色彩的力量。
《星夜》是梵高最為知名的繪畫作品之一,創(chuàng)作于圣雷米時(shí)期。整幅畫作以冷色調(diào)的深藍(lán)色和暖色調(diào)的明黃色為主要基色,這兩種劇烈對(duì)抗的顏色反復(fù)出現(xiàn)在梵高的繪畫作品中,且在這幅作品中得到極致展現(xiàn)。畫作的上方一個(gè)個(gè)明黃色的星辰環(huán)繞著深藍(lán)色的夜空漩渦,仿佛有種永恒的力量要把明黃的星辰吸進(jìn)那個(gè)夜空漩渦里。而畫作的右上角是一彎橙黃色的月亮,月亮的光亮和小村屋里的燈光是一切明黃色的來(lái)源,也是生命的來(lái)源。近處小村屋的黃色是村民居住的氣息、遠(yuǎn)處藍(lán)紫色小山上的黃色、上方星空中星辰的黃色、漩渦的黃色都象征著生命和希望。畫作的左邊是褐色的絲柏樹,粗線條描繪的樹枝一根根往上伸展,褐色的絲柏樹在黑夜里像一團(tuán)黑色的火焰,那一團(tuán)褐色里星星點(diǎn)點(diǎn)地點(diǎn)綴著許多明黃色的短線條,像火焰里炸出的花火,直竄星空,這是即將燃燒殆盡的花火擁有生命綻放的渴望。
當(dāng)人們面對(duì)這幅畫作,可能會(huì)建立一個(gè)恐懼不安的幻覺(jué)世界,也有可能會(huì)建立一個(gè)渴望生命的情感世界。當(dāng)這一個(gè)個(gè)世界被建立起來(lái)后,人們不會(huì)追問(wèn)畫中超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夜空漩渦、星辰、絲柏樹等造型的真實(shí)性,也不會(huì)去追問(wèn)畫中景象的色彩與真實(shí)景象的同一性,而是單純地建立一種或恐懼不安或渴望生命的感知世界。只有這個(gè)世界被建立起來(lái),被遮蔽的色彩才會(huì)“解蔽”,瞬間涌現(xiàn)出來(lái);代表寂靜與神秘的深藍(lán)色、象征恐懼與黑暗的深褐色、意蘊(yùn)光亮與生命的明黃色以及對(duì)這些色彩的構(gòu)圖搭配、線條融合、明暗處理等才會(huì)“敞開(kāi)”。這些色彩的質(zhì)料以及畫布的質(zhì)料才會(huì)褪去他們“自行鎖蔽”的本性而一一“澄明”,質(zhì)料的“物性”褪去,“美”自行置入,畫作不再是顏料堆積,而是真正的藝術(shù)作品。
三、結(jié)語(yǔ)
在梵高的作品里,我們看到他對(duì)色彩的敏感,我們可以通過(guò)色彩來(lái)捕捉他創(chuàng)作作品時(shí)的情感,而當(dāng)我們欣賞他的作品時(shí),我們被其打動(dòng)的卻并不是顏料、畫布或畫框,而是它所開(kāi)啟的世界。我們通過(guò)色彩將一個(gè)個(gè)世界“澄明”出來(lái),正是因?yàn)檫@一個(gè)個(gè)世界的“澄明”才讓我們認(rèn)識(shí)到色彩本身的存在,那個(gè)被“遮蔽”在作品世界后面的質(zhì)料才“敞開(kāi)”在我們眼前。我們?cè)谶@樣一個(gè)個(gè)“澄明”與“遮蔽”的爭(zhēng)執(zhí)間發(fā)現(xiàn)了“美”,這“美”不是色彩帶給我們的,也不是那個(gè)被開(kāi)啟的世界帶給我們的,而是那“爭(zhēng)執(zhí)”的保持帶給我們“美”,也讓梵高的作品得以永恒地以藝術(shù)作品的存在而存在。
參考文獻(xiàn):
[1]斯通.渴望生活:梵高傳[M].常濤,譯.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4:1.
[2]張海濤.澄明與遮蔽:海德格爾主體間性美學(xué)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海德格爾.林中路[M].孫周興,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
[4]文藝美學(xué)叢書編輯委員會(huì),編.宗白華美學(xué)文學(xué)譯文選[M].宗白華,譯.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82:228.
作者簡(jiǎn)介:王雅琪,復(fù)旦大學(xué)中文系博士研究生,豫章師范學(xué)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