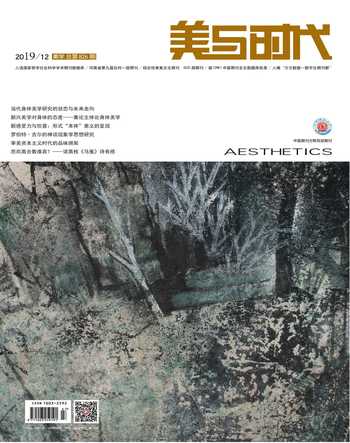劉勰對創作主體的重視
摘? 要:在文章創作方面,劉勰十分重視創作主體先天的“才”與后天的“學”。《事類》篇屬于《文心雕龍》創作論部分,主要關注創作主體各方面的條件對于文章寫作的影響。《事類》篇主要從四個方面論述對文章寫作的影響:劉勰眼中的創作主體與客體;創作主體的才學;對創作主體提出為文的原則,以及關注創作主體原因。
關鍵字:劉勰;創作主體;文心雕龍;事類
劉勰的《文心雕龍》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第一部具有嚴密體系的文學理論著作,同時也是一部寫作理論專著。林杉先生在《文心雕龍文體論今疏》中說道:“比較起來,‘作文法則’‘寫作指導’‘文章作法’之說似乎較為妥貼,而少有歧義。不過筆者意欲將‘作文法則’‘寫作指導’‘文章作法’合三為一,統稱之為‘寫作理論’,這不僅是‘名理相因’,有較強的概括性,而且也更符合《文心雕龍》實際內容和學術層次的高度。……《文心雕龍》是一部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典型的寫作理論專著。這個判斷和結論,沒有古今之分,也沒有廣義、狹義之別,一切類型的文章的體制、規格和源流,一切寫文章的規律、原則和方法,一切文章的風格、鑒賞和批評都包容于‘寫作理論’之中,似乎不再有顧此失彼、捉襟見肘之瑕了。”[1]16作為一部寫作理論著作,劉勰的《文心雕龍》在寫作過程中對于創作主體的重視值得關注。本文從《事類》篇出發,對劉勰關注創作主體方面進行分析。
一、劉勰眼中的文學創作主體與客體
在劉勰眼中,文學創作的主體是進行文學創作實在的人,而文學創作的客體是自然景物與社會生活。陸機在《文賦》中提到過創作主體與創作客體的關系,他認為文學創作的構思主要依據自然萬物的變化,即“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勁秋,喜柔條于芳春。心懔懔以懷霜,志眇眇而臨云”[2]20。劉勰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對創作主體與客體的關系進行了更深層的探討與闡述,在《物色》篇中寫到“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3]426—427他提出文學創作的基礎是感“物”,這里的“物”與《原道》篇的“無識之物”[3]28、《神思》篇的“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遁心”[3]271,都指的是自然景物或事物。至于文學創作主體與客體的關系,《物色》與《神思》篇都有所提及,“物色之動,心亦搖焉。”[3]426“物以貌求,心以理應”[3]278。劉勰認為人們的思想感情會隨著自然景物的變化而變化,人們帶著自己的感情去體會萬物,具有一定的主觀能動性,即“寫氣圖貌,既隨物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3]427劉勰在《神思》篇中寫道:“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3]272,強調人的生活閱歷,徹底觀察然后更好地運用文辭。由此可見,在劉勰的思想中,創作主體與創作客體是辯證統一的關系:“物”是基礎,但“人”卻是主導。
劉勰在文章中對“事類”做了明確的說明。“事類”這一稱謂很早就出現了。《韓非子·顯學》:“夫禍知盤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為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4]1077這里的“事類”指的是同類的事。劉勰在《文心雕龍·事類》開篇寫道:
“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書箕子之貞:斯略舉人事,以徵義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陳政典之訓;盤庚誥民,敘遲任之言:此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徵義舉乎人事,乃圣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3]355
在這里,劉勰對“事類”做出了明確的界定,其內涵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略舉人事”;一是“引乎成辭”。劉勰所說“人事”亦稱“古事”,并且對于所舉“人事”有一定的要求。創作主體在寫作時所引用的古代“人事”必須是真實發生的,虛構的故事不能算作“事類”之列。“成辭”亦稱“舊辭”,創作主體所引古書或者古人的言辭也必須是真實存在的,任何虛假言辭的引用也不能稱為“事類”。
之后,劉勰在《事類》篇中論述了創作主體“才”與“學”的關系,并對創作主體提出“博約精核”的用事要求,這都體現出劉勰對于創作主體的重視。
二、劉勰關注創作主體的“才”“學”
《文心雕龍·事類》:
夫桂因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有學飽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學貧者于事義,才餒者劬勞于辭情,此內外之殊分也。是以屬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為盟主,學為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狹,雖美少功。[3]357
劉勰認為“文”“才”是從人的先天本性生發出來的,就像生姜和牡桂生來就帶有辣味一樣,而學問是靠后天的積累和汲取。創作主體要想寫出“文采必霸”的文章,必須做到“才為盟主,學為輔佐”。缺少“文”“才”就會在言辭運用方面顯得力不從心,無法完全表達自己內心的感情;缺少學問,就會在引證事義方面感到困頓艱難。曹操評價張范的文章拙劣,就是因為他摘取崔骃、杜篤的話語成文,卻不知出處,以至于暴露出淺陋寡聞的缺點。總之,如果創作主體在“才”和“學”任何一個方面有偏頗,所寫的文章將會陷入“雖美少功”的境地。
劉勰在《風骨》篇中指出:“故魏文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強力而致。’”[3]287劉勰引用曹丕《典論·論文》的觀點,認為創作主體的氣質決定文章的氣質,這種氣質無論清濁、陽剛都是由作家先天稟賦所決定。
另外,關于“才”“學”在《體性》篇也有所論述:
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儁,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并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故辭理庸儁,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3]279
在這里劉勰提出了構成創作主體素養的四個要素,即“才、氣、學、習”。劉勰認識到文章的創作來源于創作主體內心的“情”和想要闡發的“理”。然而人的才能有平庸和杰出之分,氣質有剛強和柔弱之異,學識有淺薄和淵博之差,“習”尚有雅正和浮糜之別。這些都是由先天的性情所決定,并受到后天的陶冶感染。每個創作主體都按照自己的性情進行寫作,他們的文章就像他們的長相一樣各有特點。他又提到:“夫才有天資,學慎始習”[3]283“習亦凝真,功沿漸靡”[3]284。后天的學習在開始就要慎重,就像制作木器和印染絲綢,功效都是在最初顯現。后天的學習可以培養純正的氣質和文風,但是需要長時間的積累才能看到功效。
劉勰從創作主體出發,不僅關注他們先天的“才”和后天培養的“學”,還理性地探討了“才”“學”的辨證關系,以客觀的態度分析評價“才”“學”對于創作主體的重要意義。
劉勰對創作主體提出為文的原則。
劉勰在《文心雕龍·事類》中明確提出“用事”的原則:
是以綜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捃理須核,眾美幅輳,表里發揮。[3]359
劉勰明確提出“博,約,精,核”的“用事”原則。首先要做到“博”,“博”是“用事”的基礎。就像劉勰所說,僅一張狐皮制作不了一件溫暖的皮袍,要想用雞腳來填飽肚子恐怕需要幾千只。創作主體想要豐富自己的才力,寫出好文章,就要閱讀廣博,積累豐富的材料。創作主體從何處汲取養料呢?劉勰也為創作主體指明了方向——經史子集。《事類》:“夫經典沈深,載籍浩瀚,實群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皋也。”[3]359劉勰認為經書的內容深厚,書籍浩如煙海,是保存各家學說的寶庫,是展示各種才思的園地。創作主體從古代的文學典籍中汲取養料,根據自己的理解進行恰當的運用,為寫出好的文章打好基礎。另外,在《神思》篇中劉勰還提到了“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3]272,也強調了積累、博學的重要性。
如果說“博”是創作前的準備,那么“約”與“精”便是創作時的實施原則。劉劭《趙都賦》云:“公子之客,叱勁楚令歃盟;管庫隸臣,呵強秦使擊缶。”[3]359這短短兩句,便把毛遂迫使強大的秦國與趙國歃血為盟、藺相如迫使秦王為趙王擊缶的故事呈現在眼前。此處對事例的引用,既合理又抓住了要點,顯示出劉劭對趙都邯鄲的贊美與自豪之情,就像車軸上的鐵鍵,雖然體積小但是作用大。
“核”指的是創作主體采拾整理的材料必須翔實。《文心雕龍·事類》:“凡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謬,雖千載而為暇。”[3]360凡是引用典故得體,就與從作者自己口中說出來的話沒有什么兩樣;要是典故用錯了,雖然經過千年也還是毛病。就連曹植這樣的大家也有用錯典故的時候,他在《報孔璋書》中說;“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者因以蔑《韶》《夏》矣”。在《呂氏春秋·古樂》中記載:“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5]47。可見葛天氏的樂曲唱和的只有三人罷了。
劉勰不僅在《事類》篇中提出“用事”需“博約精核”,在“創作論”其它篇中也提出了一些創作主體為文的要求。《神思》云:“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3]272這是駕馭文章的首要方法,也是謀篇布局的要點。在《通變》篇提出規劃文章綱領要“宜宏大體”;在《定勢》篇中提到創作主體寫文章要“文辭盡情”;在《聲律》篇中談到創作文章感情應深遠、音律須淺近。劉勰認為文章的寫作不僅要靠作家的才學,也要遵循一定的寫作原則,這樣才能寫出文思靈敏的文章。
三、劉勰關注創作主體的原因
在《文心雕龍》的許多篇目中我們都能看到劉勰創作此書的目的。《序志》篇:
而去勝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離本彌甚,將遂訛濫。[3]464
夢境中的彩云和孔圣人使劉勰想到儒家經典的博大精深,想要領會圣人的智慧,就要對儒家經典進行注釋,而這些工作沒有比東漢的馬融和鄭玄做得更好的了。但是圣人的時代已經遠去,文章的體制遭到破壞,作家追新求奇,為了使創作主體寫作回到《尚書》所倡導的“貴乎體要”“宜乎于要”,避免“惡乎異端”,回到正道上來,劉勰開始了《文心雕龍》的寫作。
劉勰在其它篇中也對一些錯誤的文章進行了說明和批判。在《指瑕》篇中,他指出無論是工巧話語中的毛病,還是拙劣文辭中的問題都容易發現,且例子數不勝數,他略舉了四種:
陳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圣體浮輕”。“浮輕”有似于胡蝶,頗疑于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乎?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道若斯,余不足觀矣。潘岳為才,善于哀文,然悲內兄,則云感口澤,傷弱子,則云心如疑。
……
崔瑗之李公,比行于黃虞,向秀之賦嵇生,方罪于李斯……然高厚之詩,不類甚矣。[3]380
連陳思、左思、潘岳、崔瑗這樣的大家在使事用典時都不可避免的犯錯誤,更何況其它人。
另外在六朝時期,社會上興起使典用事的潮流,文人們推崇博聞強識。鐘嶸在《詩品·序》中說道:“故大明、泰始中,文章同書鈔。”“詞不貴奇,競須新事。而來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6]309黃侃在《文心雕龍札記·事類》中也說道:“漢代之文,幾無一篇不采錄成語者,觀《漢書》可見”[7]183。據此可知,當時的“用事”情景頗為壯觀。但是用事也有兩面性,運用得當則以古事抒今情;運用不當則謬誤叢生,千載而為暇。
劉勰在《原道》篇中指出:“惟人參之,性靈所鐘,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3]27可見劉勰把人放在天地核心的位置上。人具有主觀能動性,正確使事用典取決于創作主體的才學。所以劉勰關注創作主體,對他們提出為文要求,以期提高文章水平,改善求奇過甚的社會風氣。
總而言之,劉勰在《文心雕龍》中關注創作主體的研究方法具有巨大的前瞻性,他看到了創作主體各項素養對于寫作活動的決定性作用。在文章的寫作過程中,一切的行為活動都由創作主體來實施。因此,創作主體的才能、知識、氣質等素養都會決定著文章的質量,值得被關注和重視。這對于創作主體來說,無疑是更高的為文要求。
參考文獻:
[1]林杉.文心雕龍文體論今疏[M].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00.
[2]黃侃.文心雕龍札記[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4.
[3]劉勰.文心雕龍[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4]張覺.韓非子全譯[M].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
[5]張雙棣,等.呂氏春秋[M].北京:中華書局,2007.
[6]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第一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7]黃侃.文心雕龍札記[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作者簡介:張明月,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古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