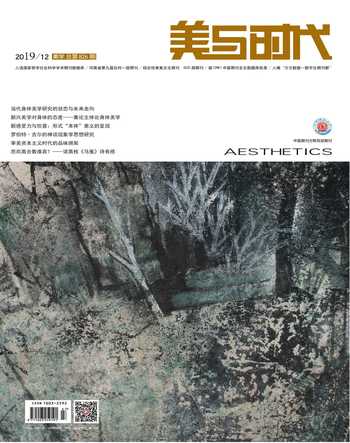《仿生人會(huì)夢(mèng)見電子羊嗎?》中的后人類情感困境探析
摘? 要:菲利普·K·迪克的科幻小說(shuō)是研究后人類不可忽視的文本。其小說(shuō)《仿生人會(huì)夢(mèng)見電子羊嗎?》講述被技術(shù)理性操控而有情感缺失癥的后人類“德卡德”和感性泛濫而有理智缺陷的后人類“伊西多爾”的故事,并通過(guò)貫穿全文的“默塞主義”和“墳?zāi)埂眱蓚€(gè)意象交織出他們的后人類情感困境,這種情感困境體現(xiàn)在身體、意識(shí)的錯(cuò)亂或不可控。
關(guān)鍵詞:后人類;情感;菲利普·K·迪克;仿生人會(huì)夢(mèng)見電子羊嗎
后人類論題發(fā)端于20世紀(jì)中后期,在“控制論”“信息論”等技術(shù)和理論的背景下,后人類“身體”“意識(shí)”以及“主體”等區(qū)別于人類中心主義。具有代表性的學(xué)者如凱瑟琳·海勒斯在其《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文學(xué)、信息科學(xué)和控制論中的虛擬身體》一書中探討了后人類的“具身性”問題,肯定后人類身體物質(zhì)性的重要性[1]。唐娜·哈拉維的《賽博格宣言——20世紀(jì)晚期的科學(xué)、技術(shù)和社會(huì)主義——女權(quán)主義》一文中提出的“賽博格”理論,展示了模糊了動(dòng)物——人類界限、動(dòng)物或人類(有機(jī)體)——機(jī)械的界限、物質(zhì)(身體)——非物質(zhì)身體的界限的后人類形象。后人類論題涉及哲學(xué)、文學(xué)理論、文化研究、電影研究、文學(xué)等領(lǐng)域。后人類研究與文學(xué)創(chuàng)作是共生的,文學(xué)現(xiàn)象中以科幻文學(xué)最為貼近后人類。美國(guó)著名的科幻文學(xué)作家菲利普·K·迪克的眾多作品也成為眾多學(xué)者研究后人類的文本,比如凱瑟琳·海勒斯就在其《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文學(xué)、信息科學(xué)和控制論中的虛擬身體》一書中分析過(guò)迪克的《仿生人會(huì)夢(mèng)見電子羊嗎?》《尤比克》等作品中的后人類身體界限。本文嘗試梳理小說(shuō)《仿生人會(huì)夢(mèng)見電子羊嗎?》中的“里克·德卡德”和“伊西多爾”兩個(gè)人物線索,分析其具有代表性的后人類情感困境,即身體、意識(shí)錯(cuò)亂或失控的后人類困境。其中,德卡德是被技術(shù)理性操控而有情感缺失癥的后人類代表,伊西多爾是感性泛濫而有理智缺陷的后人類代表,他們都處于身體、意識(shí)錯(cuò)亂或失控的情感困境。作者以“默塞主義”和“墳?zāi)埂眱煞N意象來(lái)形象化地展現(xiàn)這種后人類情感困境。
一、“默塞主義”與后人類身體、意識(shí)
后人類身體和意識(shí)的矛盾在迪克的小說(shuō)《仿生人會(huì)夢(mèng)見電子羊嗎?》中,首先體現(xiàn)在他所描述的“默塞主義”,“默塞主義”描繪了一個(gè)意識(shí)共享的世界。在仿生人身體與人類無(wú)異甚至更趨完美的狀態(tài)下,人類努力尋找區(qū)別于仿生人的特性——情感,并試圖掌控這種特性。但在身體與意識(shí)脫離的個(gè)體被消解的“意識(shí)共享”世界里,這種情感特性遭遇困境。
后人類研究理論關(guān)于后人類身體與意識(shí)的探討主要集中在兩個(gè)角度,一是人機(jī)結(jié)合的“賽博格”狀態(tài)下人類的身體與意識(shí)的變化;二是人工智能的身體和意識(shí)構(gòu)建。主要呈現(xiàn)出兩種態(tài)度,一種是積極的態(tài)度,認(rèn)為人類與人工智能的結(jié)合有助于對(duì)身體、意識(shí)的重塑,甚至形成“超人類”;一種是消極的態(tài)度,認(rèn)為無(wú)論是人機(jī)結(jié)合還是人工智能的身體和意識(shí)構(gòu)建都會(huì)削弱甚至消解人之為人的特質(zhì)。學(xué)者安迪·邁阿將“賽博格”稱為“機(jī)器人健將”,認(rèn)為人類四肢的移植、器官的再造、基因的轉(zhuǎn)換等技術(shù)“對(duì)歷史悠久的人——技術(shù)合作關(guān)系是有益的”。而澳洲學(xué)者邁文·伯德認(rèn)為電子人、遠(yuǎn)距離傳物僅僅是“后人類擺脫肉體和物質(zhì)的束縛并通過(guò)巨大的信息系統(tǒng)與每件事物和每個(gè)人‘在一起’的渴望,是當(dāng)代贖罪的基督徒的目標(biāo)的一個(gè)版本”[2]。美國(guó)學(xué)者福山在其著作《我們的后人類未來(lái)——生物技術(shù)革命的后果》中質(zhì)詢了人之為人的條件,認(rèn)為人類身體與意識(shí)是人類認(rèn)知區(qū)別于其他的重要組成條件。凱瑟琳·海勒在《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文學(xué)、信息科學(xué)和控制論中的虛擬身體》一書中追溯了信息是如何不斷失去“身體”而與物質(zhì)分離。總之,后人類身體與意識(shí)的糾葛成為了后人類時(shí)代的“一叢荊棘”。國(guó)內(nèi)學(xué)者關(guān)于后人類身體、意識(sh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duì)科幻電影的探討,比如黃鳴奮的《科幻電影創(chuàng)意——后人類視野中的身體美學(xué)》一文中,探討了科幻電影中意識(shí)脫離和被賦予作為軀殼的身體的不同狀態(tài),認(rèn)為其能豐富身體美學(xué)意義[3],但并未對(duì)意識(shí)與身體能否互相脫離做出回答;盧鑫鑫、徐明在《科幻電影中人工智能的“身體”與“意識(shí)”建構(gòu)》一文中認(rèn)為人工智能的“身體”素質(zhì)不斷增強(qiáng),“意識(shí)”不斷自主以后會(huì)影響人類的自由主體性[4]。
小說(shuō)《仿生人會(huì)夢(mèng)見電子羊嗎?》講述的是經(jīng)歷過(guò)核戰(zhàn)之后的地球,人類生產(chǎn)出了物質(zhì)身體與人類無(wú)異的仿生人。主人公德卡德便是專職追殺此類不受人類控制的仿生人的殺手。區(qū)別仿生人和人類的測(cè)試方式便是“移情測(cè)試”,它是“默塞主義”共鳴箱的延伸,共鳴箱是唯一一個(gè)能完全區(qū)別人類與仿生人的裝置,只有人類才能體會(huì)“默塞主義”的意識(shí)共享。它是一個(gè)帶把手的裝置,人類雙手扶住把手便完全沉浸于“默塞”的世界中,一種虛擬場(chǎng)景中的身體和意識(shí)的沉浸。“他不但肉體上與威爾伯·默塞合一,意識(shí)和精神也與默塞融為一體,就像其他每一個(gè)此刻握住了手柄的人,不管他在地球上還是那個(gè)殖民星球上。他體驗(yàn)到了所有人的思緒,聽到了熙熙攘攘的雜音。他們和他一樣,只關(guān)心一件事,意識(shí)的融合。”[5]132即使是人類中智力偏低下的人也有與“默塞”融合的能力,伊西多爾就是這樣一個(gè)智力低下的“雞頭”。他上班前在共鳴箱前與默塞融合,不同于殺手德卡德的極度理性的低情緒甚至無(wú)情緒,伊西多爾作為智力低下的人在打開共鳴箱的一瞬間“情緒已經(jīng)開始高漲”。對(duì)于伊西多爾來(lái)說(shuō),“默塞主義”才是他的“情緒調(diào)節(jié)器”,因?yàn)檫@是身體與意識(shí)的一次信仰的朝圣,仿佛他的智力缺陷在意識(shí)共享中得到了補(bǔ)償。當(dāng)然,“默塞主義”不僅對(duì)伊西多爾來(lái)說(shuō)是一種信仰,對(duì)于所有人類來(lái)說(shuō)都是一種信仰。德卡德的妻子伊蘭在德卡德工作一天“收入頗豐”之后認(rèn)為不跟默塞融合,不去感恩,是很不道德的。但是,這種身體與意識(shí)的融合,這種宗教式的感恩和祈禱卻是“西西弗斯”式的,凄涼、重復(fù)、總是令人痛苦的。“因?yàn)橥柌つ站瞄L(zhǎng)新。他是永生的。到了山頂,他會(huì)被打回山下,沉淪到墳?zāi)故澜纾罱K又會(huì)再爬上來(lái)。”[5]21
當(dāng)人類跟著默塞像“西西弗斯”那樣做永久的、重復(fù)的攀登時(shí),是一種痛苦,重復(fù)和永生本是仿生人的特質(zhì),也是消解人類情感的致命武器。人類在共鳴箱前與“默塞”融合,本就是以區(qū)別于仿生人為目的。但一次次的身體和意識(shí)的融合帶來(lái)的仍然是趨近于仿生人的重復(fù),這是人類身體與意識(shí)分離的噩夢(mèng)。
可以看到這種意識(shí)共享式的“默塞主義”,它帶來(lái)的情感體驗(yàn)是建立在身體與意識(shí)脫離的設(shè)想下的。
二、“墳?zāi)埂迸c后人類身體、意識(shí)
“墳?zāi)埂钡囊庀笤谛≌f(shuō)中多次出現(xiàn),在“默塞主義”世界的建構(gòu)幻象破滅后,“墳?zāi)埂笔澜缤宫F(xiàn)出來(lái),無(wú)論是德卡德還是伊西多爾都多次感受到各自的“墳?zāi)埂笔澜纭5峡藢?duì)“默塞主義”的處理極其矛盾,將“默塞主義”融合的體驗(yàn)描述得極其真實(shí)和重要。同時(shí),迪克又?jǐn)⑹隽恕袄嫌阉拱吞亍弊鳛橐粭l對(duì)立線以反對(duì)“默塞主義”。當(dāng)斯巴特揭露“默塞主義”騙局后,“默塞主義”破滅,此時(shí)在伊西多爾的感知中,吞噬所有物質(zhì)和秩序的“基皮”不斷生長(zhǎng),伊西多爾即將陷入“墳?zāi)故澜纭薄P瑟琳·海勒認(rèn)為迪克20世紀(jì)60年代中期的小說(shuō)中所出現(xiàn)的“墳?zāi)故澜纭笔菍?duì)精神分裂癥狀態(tài)的文學(xué)性/虛構(gòu)性的表現(xiàn),并且始終與內(nèi)部/外部界限的深刻混亂密切相關(guān)。其實(shí),無(wú)論是人類與機(jī)器界限的混亂,還是內(nèi)部/外部的界限混亂,都是一種“內(nèi)爆”。馬歇爾·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一書中對(duì)“內(nèi)爆”概念做過(guò)闡釋。內(nèi)爆指“意識(shí)延伸和消除所有界限的后現(xiàn)代過(guò)程”,是與“身體的延伸”相對(duì)立的“意識(shí)的延伸”,與默塞的融合是一種意識(shí)延伸的過(guò)程,一種脫離身體的意識(shí)共享,它帶來(lái)的后果是界限模糊。“內(nèi)爆”后產(chǎn)生的“墳?zāi)埂笔澜纾瓤梢灾敢环N意識(shí)游離而身體無(wú)所適從的與外界物質(zhì)的排斥感、距離感,也可以指一種身體無(wú)法突破界限的意識(shí)的無(wú)助、壓抑甚至是“死亡”狀態(tài)。這都是后人類情感困境的一種體現(xiàn)。
作為一個(gè)“理性”的仿生人殺手,德卡德一開始對(duì)自己的工作定位是清晰的。他上班前,會(huì)按日歷在情緒調(diào)節(jié)器上調(diào)節(jié)工作情緒,對(duì)自己的職業(yè)認(rèn)知非常清晰,他知道仿生人與人類的不同。他一開始認(rèn)為一個(gè)仿生人,不管智力上多么卓越,永遠(yuǎn)都理解不了默塞主義追隨者感受到的那種融合感。德卡德如此定義仿生人,因?yàn)檫@樣使他工作起來(lái)很愉快。“墳?zāi)埂笔澜绲谝淮纬霈F(xiàn)與德卡德的工作有關(guān),他形容上司的秘書“像侏羅紀(jì)沼澤里爬上來(lái)的上古野獸,或者是墳?zāi)故澜缋锟M繞不去的老妖怪,冰冷狡詐”[5]144。說(shuō)明從潛意識(shí)里,德卡德感受到的公司氛圍是像“墳?zāi)埂币粯拥摹9ぷ鏖_始后,德卡德一天內(nèi)已經(jīng)殺掉了三個(gè)仿生人,只是在殺仿生人歌手魯芭·勒夫特時(shí),開始對(duì)仿生人產(chǎn)生了同情,并且滿足了勒夫特的愿望給她買下了《青春期》畫作的復(fù)制品。也許是出于一絲愧疚,在殺掉她后,德卡德還將畫冊(cè)燒成了灰,仿佛是給仿生人的一個(gè)祭禮。德卡德甚至還追問“你覺得仿生人有靈魂嗎”,這時(shí)的德卡德對(duì)仿生人的認(rèn)識(shí)已經(jīng)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因此,當(dāng)他在給同行殺手菲爾·雷施做移情測(cè)試時(shí),“墳?zāi)埂币庀笤俅纬霈F(xiàn)了,“一直說(shuō)到墳?zāi)故澜缋锶グ桑搿V灰阆矚g。對(duì)我沒有影響。”[5]235“墳?zāi)埂闭娴膶?duì)德卡德沒有影響嗎?并不是的。為什么同行殺手對(duì)于此時(shí)的德卡德來(lái)說(shuō)也成了“墳?zāi)埂笔澜绲囊粏T呢?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卡德還沒有分清楚菲爾·雷施是人類還是仿生人身份而對(duì)他產(chǎn)生厭惡和排斥,實(shí)際上是德卡德已經(jīng)對(duì)“殺手”職業(yè)產(chǎn)生了懷疑。技術(shù)理性化的工作使得德卡德的身體行為與意識(shí)產(chǎn)生沖突,其實(shí)當(dāng)他在追問仿生人是否有靈魂時(shí),他已經(jīng)開始覺得定義人類的方式是極其殘忍的了。德卡德對(duì)仿生人產(chǎn)生了移情,他遭遇了情感困境。在與默塞融合時(shí),默塞告訴德卡德:“這是生命的基本條件,要求你違背自己認(rèn)同的身份……這是終極詛咒,那個(gè)吞噬所有生命的詛咒。整個(gè)宇宙都是這樣。”[5]164德卡德在對(duì)人類身份和仿生人身份產(chǎn)生困惑后,他潛意識(shí)里開始排斥殺手職業(yè),認(rèn)為自己可能消滅不了它們了,在追殺剩下三個(gè)仿生人之時(shí),德卡德甚至在內(nèi)心為仿生人逃回地球做辯解,設(shè)想仿生人也許也會(huì)做夢(mèng),它們也值得擁有自由的生活。自此,“墳?zāi)埂币庀蠓浅M怀觯瑢?duì)于德卡德來(lái)說(shuō),時(shí)間涌動(dòng)、生命循環(huán),都是不過(guò)“墳?zāi)故澜纭保罱K都是死亡的寂靜。
“墳?zāi)埂币庀笤谝廖鞫酄栠@個(gè)人物上被多次敘述。伊西多爾是特障人士,獨(dú)自居住在空蕩蕩的公寓樓里,這座沒有生命的公寓樓對(duì)于伊西多爾來(lái)說(shuō)便是“墳?zāi)故澜纭薄6?dāng)伊西多爾與默塞融合,進(jìn)入全人類身體和意識(shí)融合的世界時(shí),他還是陷入了”墳?zāi)故澜纭埃簿褪钦f(shuō)在“默塞主義”內(nèi),他與全人類一起陷入“墳?zāi)故澜纭薄4藭r(shí),仿生人普里斯為了逃命住進(jìn)公寓樓里,伊西多爾覺得自己“不再是一個(gè)人了”,他被拉出了“墳?zāi)故澜纭保驗(yàn)樽鳛楣陋?dú)的人類的他有了仿生人生命相伴,“基皮”開始褪去,“墳?zāi)故澜纭敝饾u遠(yuǎn)離。伊西多爾清楚自己是人類中智力低下被排斥的孤獨(dú)的一類人,但是他認(rèn)同有生命的、活物的群體。在他的感知世界里,并沒有對(duì)仿生人和人類進(jìn)行特別理性的區(qū)分。所以,在沒有生命的公寓樓里,伊西多爾仿佛進(jìn)入“墳?zāi)故澜纭保?dāng)仿生人生命到來(lái)時(shí),伊西多爾走出“墳?zāi)故澜纭保⑶医蛹{仿生人。伊西多爾不斷與“墳?zāi)故澜纭边M(jìn)行拉鋸戰(zhàn),當(dāng)生命遠(yuǎn)離他時(shí),“墳?zāi)故澜纭本徒艘徊?當(dāng)生命群體靠近他時(shí),“墳?zāi)故澜纭本瓦h(yuǎn)了一步。并且這個(gè)生命并不是孤獨(dú)的人類生命,它包括仿生人生命,包括動(dòng)物生命,甚至包括假動(dòng)物的生命,伊西多爾對(duì)生命群體的感知是包容的。因此,當(dāng)客戶交給伊西多爾修理的病貓死掉時(shí),伊西多爾為此感到非常痛苦,他感受到自己正沉淪到“墳?zāi)故澜纭钡奶卣先四嗾永铩K刻鞊p失一點(diǎn)聰明、一點(diǎn)干勁,最終會(huì)和地球上成千上萬(wàn)的特障人一樣,慢慢地灰飛煙滅,成為“墳?zāi)埂钡囊徊糠帧?/p>
德卡德陷入“墳?zāi)故澜纭笔怯捎谒臉O度理性化,甚至需要情緒調(diào)節(jié)器調(diào)節(jié)自己的情緒和工作狀態(tài)。即使在對(duì)仿生人有不同認(rèn)知后,對(duì)自己的殺手職業(yè)產(chǎn)生懷疑時(shí),他還是理性地選擇以購(gòu)買山羊承擔(dān)巨額欠款的方式來(lái)刺激自己的工作欲望,如此工具理性化使得他在殺掉6個(gè)仿生人后陷入“墳?zāi)埂笔澜纭5驴ǖ率鞘芗夹g(shù)理性支配的后人類。
伊西多爾陷入“墳?zāi)故澜纭眲t是因?yàn)橹橇Φ拖隆⒗硇哉系K但情感泛濫。伊西多爾對(duì)仿生人、對(duì)蜘蛛投入的過(guò)渡泛濫的情感成為他陷入墳?zāi)故澜绲闹屏Α.?dāng)仿生人普里斯向伊西多爾解釋賞金獵人的工作時(shí),伊西多爾表示不理解并堅(jiān)信“所有生命都是一體的”,而當(dāng)普里斯殘忍地割掉一條條蜘蛛的腿時(shí),伊西多爾無(wú)法自控的情緒將他推入“墳?zāi)故澜纭薄7律颂踊氐厍虻穆芬彩且粭l踏入“墳?zāi)故澜纭钡牡缆罚驗(yàn)檎缙绽锼顾f(shuō),他們都是精神分裂癥患者,沒有正常情感——所謂的情感缺失癥。“默塞主義”的幻滅導(dǎo)致的是“墳?zāi)埂笔澜绲耐癸@,默塞主義在某種程度上也成為了一個(gè)“墳?zāi)故澜纭保缫廖鞫酄柵c默塞融合時(shí)所感受到的,因?yàn)樗笊眢w與意識(shí)分離、虛擬身體的融合與意識(shí)共享。陷入“墳?zāi)故澜纭睍r(shí)是無(wú)助的、被動(dòng)的、感知和意識(shí)無(wú)法自控的、無(wú)法自主行動(dòng)的。正如人類與默塞融合時(shí)的體驗(yàn),身體與年老的默塞的身體融合且不斷被未知的敵人投來(lái)的石塊所傷害,這種無(wú)助、無(wú)法行動(dòng)的感知體驗(yàn)是身體與意識(shí)失控的后果。
“墳?zāi)故澜纭贝碇环N凄涼、死寂、絕望的狀態(tài),是時(shí)間停滯、被動(dòng)等待、內(nèi)心死亡的的狀態(tài)。“墳?zāi)故澜纭笨赡艹蔀榈驴ǖ逻@樣極度理性的后人類的結(jié)局,也可能成為伊西多爾這樣的情感豐富而智力低下的后人類的結(jié)局,更有可能成為普里斯、羅伊這樣的智力完美而有“情感缺失癥”的仿生人的結(jié)局。總之,它似乎是一種無(wú)助、無(wú)法行動(dòng)的感知體驗(yàn),是身體與意識(shí)失控的后果。
三、結(jié)語(yǔ)
人類情感依托于身體和意識(shí)的協(xié)調(diào),是理性與感性的共同作用。在后人類語(yǔ)境下,賽博空間延伸了人類的身體感官體驗(yàn),通過(guò)虛擬技術(shù)能使人的感官得以運(yùn)作。生物技術(shù)、基因工程等科學(xué)的發(fā)展為人類的身體帶來(lái)了改變,它也許可以達(dá)到超人類主義學(xué)者所說(shuō)的“超人類健將”的效果。唐娜·哈拉維的“賽博格”展示了一種人體與機(jī)器拼接體的后人類,后人類的身體的變化無(wú)疑會(huì)帶來(lái)一些與身體相關(guān)的哲學(xué)的、倫理的等等疑惑。身體在科學(xué)技術(shù)的幫助下帶來(lái)的延展是否可控?凱瑟琳·海勒斯震驚于一種身體可以轉(zhuǎn)變?yōu)樾畔⒍粋魉偷暮笕祟愒O(shè)想,她開始思考“物質(zhì)”對(duì)于后人類的意義。福山在其著作《我們的后人類未來(lái)——生物技術(shù)革命的后果》中質(zhì)詢了后人類之“人性”,認(rèn)為人類身體與意識(shí)是人類感知體驗(yàn)的重要組成條件,也是人之為人的特點(diǎn)[6]。迪克小說(shuō)中的人物德卡德和伊西多爾,一個(gè)被技術(shù)理性操控而有情感官能缺失癥;一個(gè)感性泛濫因核戰(zhàn)傷害而有理智缺陷,他們都是典型的后人類代表。理性與感性的不協(xié)調(diào)、身體與意識(shí)的失控狀態(tài)令后人類陷入情感困境。
參考文獻(xiàn):
[1]海勒.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文學(xué)、信息科學(xué)和控制論中的虛擬身體[M]劉宇清,譯.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7.
[2]曹榮湘,選編.人類文化[C]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4.
[3]黃鳴奮.科幻電影創(chuàng)意:后人類視野中的身體美學(xué)[J]東南學(xué)術(shù),2019(1):170-185+247.
[4]盧鑫鑫,徐明.科幻電影中人工智能的“身體”與“意識(shí)”建構(gòu)[J]電影文學(xué),2018(23):46-50.
[5]迪克.仿生人會(huì)夢(mèng)見電子羊嗎?[M]宋根成,譯.鄭州:河南大學(xué)出版社, 2004年.
[6]福山.我們的后人類未來(lái)——生物技術(shù)革命的后果[M]黃立志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7.
作者簡(jiǎn)介:李莎,西南大學(xué)文學(xué)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藝?yán)碚摗?/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