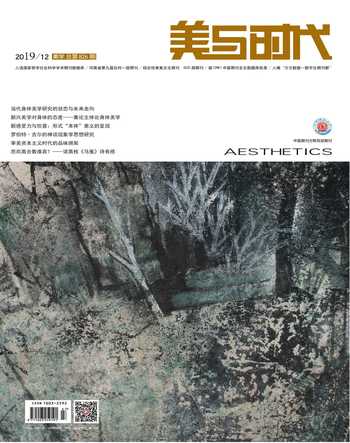試論文學期刊與文學觀念之關系
摘? 要:從十月革命后爆發的對譯介俄蘇文學的極度熱情,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在“中國該走什么道路”和“中國文學該走什么道路”兩個問題上的探索,當時的報刊雜志,無論何種傾向,都無一例外地投身于譯介俄蘇文學的狂熱浪潮中。以俄蘇文學為代表的西方文學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產生過的這種“形成性”的影響,即使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者們也從不諱言。
關鍵詞:小說月報;俄蘇文學;文學期刊;文學觀念;譯介;揚棄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形成的過程中,西方文學思潮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新文學運動中成立最早、影響最大的文學社團之一的文學研究會就以“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作為其宗旨,而作為文學研究會代用機關刊物發行的革新后的《小說月報》則身體力行地全面貫徹了這一宗旨。在正式接手主編《小說月報》的前一期,即1920年第11卷第12號,沈雁冰就在《本月刊特別啟事一》中宣稱:
近年以來,新思想東漸,新文學已過其建設之第一幕而方謀充量發展,本月刊鑒于時機之既至,亦愿本介紹西洋文學之素志,勉為新文學前途盡提倡鼓吹之一分天職。自明年十二卷第一期起,本月刊將盡其能力,介紹西洋之新文學,并輸進研究新文學應有之常識。[1]
而在1922年第12卷第1號的《改革宣言》中更是重申:小說月報行世以來,已11年矣,今當第20年之始,謀更新而擴充之,將于譯述西洋名家小說而外,兼介紹世界文學界潮流之趨向,討論中國文學革進之方法。[2]
本文即以《小說月報》對俄蘇文學的譯介為切入點,探討其是如何對中國現當代文學觀念產生影響的。
一、俄蘇文學譯介概況
追述我國俄蘇文學的譯介史,可以明顯地看到以俄國十月革命為界的“前冷后熱”的分期。如果說十月革命之前的俄蘇文學譯介只能說是在整個外國文學譯介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話,十月革命之后的俄蘇文學譯介則進入了獨領風騷的輝煌時期。具體到《小說月報》對俄蘇文學的譯介同樣呈現出這樣的鮮明對比。
前期《小說月報》的外國文學譯介以英國作品占比最大,其次為法國、美國、俄國和日本,其中譯介的俄國文學作品總共25篇,按文體分類為:小說19篇,戲劇1篇,新體詩1篇和介紹性的文章4篇[3]。作家選擇則集中在托爾斯泰和契訶夫兩位經典作家,占了譯介作品的七成以上,翻譯形式多數為轉譯、意譯,且以文言行文,在作品選擇上也較隨機無序,雖選名家卻非名篇,可以說影響有限。
革新后的《小說月報》明顯加大了對外國文學的譯介力度,在革新當年即推出了革新后的第一個專號——《俄國文學研究》,對俄蘇文學的關注從此貫穿整個辦刊史。11年中總共譯介俄蘇文學227篇,占同期外國文學譯介的近三分之一,其中翻譯作家作品104篇,評論介紹性文章123篇,涉及的俄國作家、文學流派、不同題材以及譯者隊伍都空前地廣泛和優秀。可以說,通過《小說月報》這一時期的譯介,較為系統地、深入地描繪出了現代俄蘇文學的整體面貌。
二、對俄蘇文學的揚棄
從十月革命后爆發的對譯介俄蘇文學的極度熱情,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在“中國該走什么道路”和“中國文學該走什么道路”兩個問題上的探索,當時的報刊雜志,無論何種傾向,都無一例外地投身于譯介俄蘇文學的狂熱浪潮中。以俄蘇文學為代表的西方文學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產生過的這種“形成性”的影響,即使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者們也從不諱言。魯迅先生在談到他的小說誕生的時候,就曾經認真地說過:“我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此外的準備,一點也沒有”[4]。可以說先生的文學創作和批評理論都深深打上了俄國批判現實主義的烙印,比如其代表作品《狂人日記》即受果戈理同名小說的啟示。俄國文學“為社會、為人生”的文學觀被中國學人普遍接受和深入闡釋,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成為了中國新文學學習的典范,然而當我們仔細品讀革新后的《小說月報》的若干文章以及將《小說月報》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的時候,我們仍然能在為俄蘇文學搖旗吶喊的主旋律之下聽到一絲異響。
(一)中俄迥異的國民性
周作人先生的《文學上的俄國與中國》一文系其1920年兩次演講的整理稿,最先發表于《晨報·副刊》(1920.11.15-11.16,當時尚未獨立發行),1921年又在《新青年》(第8卷第5號,1921.1.1)刊出,后被轉錄在《小說月報》第12卷號外《俄國文學研究》,被視為中俄文學比較研究開山之作。文中周作人通過梳理俄國近代文學的發展脈絡指出俄國文學的特色是“社會的、人生的”,進而感慨道:
中國的特別國情與西歐稍異,與俄國卻多相同的地方,所以我們相信中國將來的新興文學,當然的有自然的也是社會的、人生的文學。
然而接下來,作者卻筆鋒一轉,稱:
就表面上看來,我們固然可以速斷一句,說中俄兩國的文學有共同的趨勢,但因了這特別國情而發生的國民的精神,很有點不同,所以這其間便要有許多差異[5]。
接著文章從宗教、政治、地勢、生活、特殊精神六個角度論述了中俄國民精神的具體差異所在。文中描述的俄國國民精神可大致歸納為:具備人道主義思想基礎、勞眾思想的去官僚化、博大與極端并存、崇高的悲劇氣象和富于懺悔精神等。而我國的國民精神則呈現出另一番景象:缺乏人道主義思想基礎、官僚思想普及、多講非戰妥協、玩世與怨恨并存、缺乏自我譴責意識等。撇開周氏的論述是否客觀、全面不談,中俄國民精神上的顯著差別甚至是對立是顯而易見的。
俄國最具世界性影響力的哲學家之一別爾嘉耶夫曾在自己的代表作《俄羅斯的命運》中提出“俄羅斯是矛盾的,是二律背反的”[6],而在他的另一部代表作《俄羅斯的思想》中則進一步闡釋“俄羅斯民族是最兩極化的民族,它是對立面的融合”[7]2“俄羅斯人既是爭強好勝的運動員,又是強盜,同時,又是上帝正義的朝圣者”[7]6。正是基于這樣的國民性,在俄國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品中才會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陷于迷狂、激昂亢奮、崩潰邊緣的斯塔夫羅金;果戈理作品中“被深刻的悲哀和憂郁所壓倒”的“含淚的微笑”(別林斯基語);托爾斯泰文中時刻流露出的悲天憫人、參悟靈肉、解析生死的苦悶追尋。俄國文學內在的悲愴美是它區別于歐洲其他地區文學和屹立于世界文學的精神內質。
而面對這樣與我國國民性迥異的民族,在普遍的接受和傳播其“為社會、為人生”的文學觀念的同時,中國學人也時刻把持著“為中國”的標尺,俄蘇文學為代表的外國文學的譯介固然能為中國新文學的產生輸入新鮮血液,但新文學的基礎更應建立在“外國舊文學與國故的混合物”上,鄭振鐸接手《小說月報》后發起的整理國故也印證了這種觀念的轉變。
(二)中國缺失的宗教性
當我們把革新后的《小說月報》對俄蘇文學的譯介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的時候,在這104篇作品翻譯和123篇評介文章中,會發現一種奇怪的倒置現象,即對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這兩位俄國重量級經典作家的“輕譯重介”,對刊登其評介性的文章的熱情明顯高于對其作品的翻譯,似乎他們僅僅存在于文學史和后人的評介中,要想窺探廬山真面目變得似乎有些困難。
我們看到單是《俄國文學研究》專號一期就有3篇論及托爾斯泰的評介性文章——一篇《俄國四大文學家合傳》(果戈理、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兩篇專論托爾斯泰的文章《俄羅斯文學里托爾斯泰底地位》《托爾斯泰的藝術觀》,文中充滿了對托翁的高度肯定和極力推崇:
托爾斯泰富有偉大之天才,志高之獨創性,不為舊學慣例所拘,運用其高超之哲學思想于文學作品中,以灌輸于一般人民。他是俄國的國魂,他是俄國人的代表,從他起我們才實認俄國文學是人生的文學,是世界的文學。[8]
而革新后的《小說月報》更是有10篇有關托翁的各方面的介紹、論述,甚至不乏《托爾斯泰孫女回憶錄》《托爾斯泰的秘密日記》《托爾斯泰的情史——幾封致女友的書信》這樣深入托翁生活中細節的文章,對托翁的評介可謂既有對其藝術價值、文學地位的認同,又深入到其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與這種評介熱情形成鮮明對比的卻是對托翁作品的冷淡甚至漠視,革新后的《小說月報》僅刊登了寥寥4篇,在《俄國文學研究專號》中甚至沒有,與刊登的契訶夫翻譯作品21篇、屠格涅夫19篇形成了鮮明對比,這樣的托爾斯泰被研究者稱為“被懸置的托爾斯泰”[9]。
遭遇同樣對待的還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說月報》第13卷第1期上刊登了四位作家從不同角度對陀氏的評介文章,分別是:沈雁冰的《陀思妥以夫斯基的思想》、小航的《陀思妥以夫斯基略傳》、郎損的《陀思妥以夫斯基在俄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和一篇《關于陀思妥以夫斯基的英文書》的新聞報道,而在同一期上卻未看到陀氏的譯作刊登,陀思妥耶夫斯基專輯全由譯介文章組成,不免讓人奇怪,當然這些文章中并不吝溢美之詞,文中盛贊陀氏:
陀思妥以夫斯基偉大的表現力與深刻的觀察,使他成為俄國文學史上偉大的人物。他一定不易地是俄國的第一流作家,而且是全世界的第一流作家。[10]
然而對于這樣的“俄國的國魂”“全世界的第一流作家”,卻只能從國人對他們的譯介中知其一二,這讓我們不禁推斷:如此的“輕譯重介”難道是《小說月報》偏愛的譯介方式么?當看到第17卷第10期契訶夫專輯的“6篇譯作+0篇評介”的推介模式,似乎并非如此;那么是因為這兩位作家的作品多有長篇而不便在期刊上長時間連載么?再看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獵人日記》從第12卷第3期連載至第15卷第11期,歷時三年半有余,跨越24期,甚至跨越了兩位不同主編的時期,看來這也不是原因;再退一步,是不是當時已有兩位作家的作品單行本問世而不必刊載在期刊上呢?畢竟我國對托翁的譯介由來已久,數量也巨大,然而答案同樣是否定的。盡管對托翁的譯介甚至可以追述到“1902年的《新小說》創刊號季刊‘俄國大小說家托爾斯泰’像,其后不斷有文章談及,也陸續有譯著出版”[11],林譯俄文作品也幾乎集中在托爾斯泰一人身上,但其重要的長篇作品《安娜·卡列尼娜》《戰爭與和平》等,都是三四十年代才翻譯出版的,對陀氏作品的大規模翻譯出版亦在這一時期[12]。在一個個否定了如上的猜測之后,我們最終只能去兩位作家本身和其作品的內部去尋找答案,究竟他們寫了什么奠定了其各自在俄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的崇高地位,又因為什么而在《小說月報》上總以猶抱琵琶半遮面示人。
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窮其一生在思考、探索人生和俄羅斯道路的作家,他們深受俄國東正教宗教思想的浸潤,思想復雜、深刻而富有變動,對形而上的問題求索極深,在以作家為人們熟知的同時,更是思想家、哲學家,甚至宗教哲學家,托爾斯泰主張博愛、寬恕的宗教理念,提出“勿以暴力抗惡”;陀思妥耶夫斯基則宣揚基督式的仁愛、犧牲,主張自我懺悔、自我救贖和自我懲罰。二者身上濃厚的宗教氣息和深刻的思考結果無不滲入到他們的文學創作中。對于這樣的作品,不僅當時的普通大眾在理解上會形成諸多障礙,甚至在我們今日讀起來都會頗感晦澀,即使對表面的文字和小說的情節有了足夠的認知,也很難深入到人物的思想內部,對人物的行為和作品的構思有時難于深入理解,如此既不能滿足當時讀者對于外國文學獵奇的需求,亦不能發揮文學作品教化社會的功能,故而對這兩位繞不開的俄國經典作家也就只能采取“輕譯重介”的處理方式了。
基于對中俄迥異國民性和中國宗教性缺失的考量,中國學人在大力“提倡鼓吹”俄蘇文學的“為社會、為人生”之時,心中始終銘記著“為中國”的標尺,然而這種對俄蘇文學有意識的揚棄,亦不能只被看作是《小說月報》為迎合讀者需求而進行的商業運作,甚至不能把它全部歸因于與中國當時社會狀況的不合時宜,而是應該做更深刻、更長遠的考慮。當時的中國學人或許一早就意識到了反映如此迥異國民性的中俄兩國文學或許會呈現出某種不同的面貌,而深受宗教意識浸潤的文學創作也無法輕易在缺乏宗教傳統的中國大地上落地生根,故而在樹立中國新文學觀念的風向標時對其暫且擱置,以期后來人能對他們和他們的作品做出更好的解讀和接受。
參考文獻:
[1]沈雁冰.本月刊特別啟事一[J].小說月報第11卷第12號,1920.
[2]沈雁冰.改革宣言小說月報第12卷第1號,1921.
[3]甘樂樂.小說月報(1921-1931)俄國文學譯介研究[D].廣州:暨南大學,2010.
[4]樂黛云.比較文學簡明教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5]周作人.文學上的俄國與中國[J].小說月報第12卷號外俄國文學研究,1921.
[6]別爾嘉耶夫.俄羅斯的命運[M].汪劍釗,譯.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3.
[7]別爾嘉耶夫.俄羅斯思想[M].雷永生,邱守娟,譯.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2004.
[8]濟之.俄國四大文學家合傳[J].小說月報第12卷號外俄國文學研究,1921.
[9]董麗敏.想象的現代性:革新時期的《小說月報》研究[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10]沈雁冰.陀思妥以夫斯基在俄國文學史上的地位[J].小說月報第13卷第1號,1922.
[11]陳平原.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清末明初小說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57.
[12]高志強.小說月報(1921-1931)翻譯文學初探[D].北京:北京語言大學,2007.
作者簡介:李葆華,上海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中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