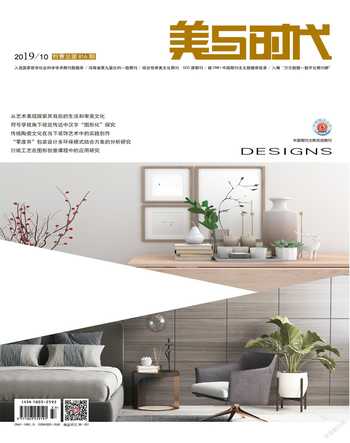清末民初女子美術教育的嬗變
摘? 要:中國近代女性崛起的主要特征是女性現代教育模式的制度化和規范化,而探索新女性畫家在近代教育模式下的藝術創作和思想觀念的轉變,則須先探討其與女性美術教育之間的關聯。清末民初下的中國近代女子美術教育是在“救亡圖存”“實業救國”的強烈呼聲中蹣跚起步,又在辛亥革命的民主浪潮中汲取現代西方先進的女子教育模式。對中國近代女子美術教育的歷史考察,能夠厘清中國女性美術教育在近代的發展脈絡,進而明晰女子美術教育從清末到民國,再到西方美術教育的移植的發展軌跡。而中國近代女子美術教育的逐漸完善,則是促進中國近代新女性畫家崛起的第一步。
關鍵詞:清末民初;女性藝術;女子美術教育;嬗變
中國近代女性崛起的主要特征是女性現代教育模式的制度化和規范化,而探索新女性畫家在近代教育模式下的藝術創作和思想觀念的轉變,則須先探討其與女性美術教育之間的關聯,意味著厘清近代中國女子美術教育從男權制下的女子家庭美術教育到女子專業美術教育的轉變軌跡。
一
清末民初下的中國近代女子美術教育是在“救亡圖存”“實業救國”的強烈呼聲中蹣跚起步,又在辛亥革命的民主浪潮中汲取現代西方先進的女子教育模式。
在古代父權制下的女子家庭美術教育是一直存在的,琴、棋、書、畫不僅是名門閨秀修身的才藝,也是她們怡心養性的閨閣情趣。首先,閨閣女子都以繪畫為專長,或是父子相繼,或是夫妻相傳,或是姐妹相娛,形成了以家族為單位的繪畫群體,并隨著家族人口的自然增長而擴展和蔓延。這是一個不自覺的過程,每個家族成員都在耳濡目染中被卷入這種文化的傳承體系之中。而閨閣畫家正是在這些文化世家中起步、成長起來的一種女性畫家類型。其次,在古代,身居社會高層家庭中的女子,都把書畫作為提高品性修養的一種手段。深閨之中擅畫者絕不為少數,如文從簡之女文俶、王寵之女王采、仇英之女仇珠、徐季恒之女徐安生等。但是受到“女子無才便是德”“男尊女卑”“三從四德”等封建思想的侵害,加之又怕與風塵女子并論,“故不以女子擅畫為能事”“畫畢多手裂之,不以示人”。這也是為何古代女性畫家遺留存世之作甚為罕見的原因之一。
而古代父權制下的女子家庭美術教育,在近代西方美術教育體制以及近代美術留學生群體的廣泛傳播中瀕臨崩塌,清政府也于維新變法之后,在“男女平等”的社會浪潮中,被迫構建了中國近代新式女子美術教育體系。1904年清政府頒布的《奏定學堂章程》(又稱《癸卯學制》)中規定:“格致(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圖畫、手工,皆當視為重要科目”,中、高等工業學堂須開設“圖稿繪畫科”;同時,章程中規定了初級小學堂的圖畫教學目的為“圖畫之要義在練習手眼,以養成其見物留心,記其實象之性情,但當示于簡易之形體,不可涉復雜”;高級小學堂的圖畫教學目的則為“圖畫要義在使觀察實物之形體及臨本,由教員指授畫之,練成可應用之技能,并令其心思于精細,助其愉悅”;中學堂則為“習畫者,當就實物模型圖譜,教自在畫,俾得練習意匠,兼進用器畫之大要,以備他日繪地圖、機器圖及講求各項實業之基礎。”[1]1907年,學部頒布《奏定女子師范學堂章程》(三十六條)、《奏定女子小學堂章程》(二十六條),作為對癸卯學制的補充,確認了女子與男子一樣擁有受教育的權利,這是近代第一部官方頒布的女子教育章程,其中對圖畫科要旨也作了簡要的注釋。《女子師范學堂章程》“立學”第一章云:“女子師范學堂,以養成女子小學堂練習,并講習保育幼兒方法,期于裨助家計,有益家庭教育為宗旨。”《女子師范學堂章程》“學科程度”第二章第三節云:“中國女德,歷代崇重,凡為女為婦為母之道,征諸經典史冊,先儒著述,歷歷可據。今教女子師范生,首宜注重于此。務時勉以貞靜、順良、慈淑、端儉諸美德,總期不背中國向來之禮教,與懿?之風俗。其一切放縱自由之僻說,務須嚴切屏除,以維風化。”[2]42在《女子師范學堂章程》第四節“圖畫科要旨程度”中解釋,圖畫“其要旨在使精密觀察物體,隨肖其形象神情,兼養成其尚美之心性。其教課程度,授寫生畫,隨加授臨本畫,且使時以己意畫之;更進授幾何畫之初步,并授以教授圖畫之次序法則。”在清政府學部制定的章程中,強調了女子學習圖畫需注重臨摹與寫生并重,需養成精細觀察實物之能力,需準確再現物象形神關系,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的女子美術教育已初步具有中西融合的藝術特征。雖然此時清政府正式準允女學的開辦,但是仍然以“女德”掛帥。雖然以上這些女學章程的規定中仍然具有傳統封建思想的性質,卻是首次以國家法制形式正式承認了女子教育的合法存在,其中對于女子美術教育作了明確的規定,不僅促進了清末民初新式女子教育的發展,而且逐漸形成了近代女子美術教育的雛形,同時,這也是近代中國女子教育轉變的開端。
如果說古代閨閣女子學習繪畫的目的是出于以畫抒情的創作旨趣,那么隨著民國女性受教育權利的逐漸解放,女子學習繪畫由過去家庭教育的單一模式轉變成為學校教育模式與家庭教育模式并行,逐漸從以重“情”的家學轉變為“技”與“藝”結合的系統化美術教育。中華民國成立伊始,孫中山先生不僅主張“四萬萬之人皆應受教育”,而且認為“中國女子雖有二萬萬,惟于教育一道,向來多不注意”,因此,“處于今日,自應以提倡女子教育為最要之事”,只有女子教育普及,“然后男女可望平權。女界平權,然后可成此共和民國”[3]。1912年1月19日,蔡元培為改革舊制,發布《普通教育暫行辦法通令》,提出“初等小學,可以男女同校”。之后,3月12日公布實施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以下簡稱《臨時約法》)中并沒有履行婦女參政的承諾,刪除同盟會政綱中有關男女平權的條文,但是,知識分子們利用《臨時約法》中規定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紛紛組織社團和創辦報刊,大量引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美術思想觀念和美術作品。9月3日,中華民國第一個《學校系統令》公布,史稱“壬子學制”。“壬子學制”在女子教育方面較之“癸卯學制”有了長足的進步:首先,在小學校的課程設置中,初等小學校及高等小學校均設置了圖畫課,女子學員另加課縫紉;在中學校中將專教女子的中學校稱為女子中學校,開設圖畫課,另加課家事、園藝、縫紉。其次,教育部公布《公立私立專門學校規程》,允許設立美術專門學校,依所屬性質可分為由教育部直接管轄的美術國立專門學校,由地方政府管轄的美術公立專門學校,以及由私人或私法人創辦的美術私立專門學校。“壬子學制”的設立既為美術領域輸送了源源不斷的女性學員,也為民國女子美術教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民國男女都有平等受教育的權利。最后,“壬子學制”以民主主義精神蕩滌了封建專制主義和科舉教育遺毒,破除了男尊女卑的封建觀念。但“壬子學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為“壬子學制”是以“癸卯學制”為藍本,并不是對清末學制的全盤否定,而是繼承和發展了它的合理性,并在辛亥革命以及民主思想的影響下,批判和改造了它的不合理性。但是“壬子學制”中仍然遺留著封建社會的傳統思想,女子在接受新式教育的同時,仍然要學習家事、縫紉等女作,并沒有在思想和課程上完全實行男女平權。1912年1月4日,蔡元培先生就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通過譯介西方美學著作,廣布康德美學思想,開創中國美育教育的新局面。其美育思想既在中國傳統美學精神的基礎之上繼承了傳統美學中“完善人格”的思想,同時還吸收德國哲學家康德、叔本華的美學思想,把美感教育列入民國初期教育方針五項內容之一,最終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美育理念,并且對于啟發近代女性“完美人格”的構建具有很好的啟示和指導意義。他認為美育的功效在于:“陶養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純潔之習慣,而使人我之見、利己損人之思念,以漸消沮者也”[4]。其次,蔡元培還通過開設美學課程,推行其教育理念,傳播美學思想。1918年,蔡元培在北大成立畫法研究會,聘請著名畫家陳師曾、徐悲鴻、劉海粟來校講課并指導傳習,進一步豐富了美育實踐活動。同時在這些畫家的培養下,也出現了一大批融合中西方藝術思想且具有現代女性觀的新女性畫家。
二
在中國近代美術教育體系的建設中,留日和留法學生群體對西方美術教育體系的移植和轉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自戊戌維新以來,女子留學蔚然成風。日本是中國女子學習美術的首選之地,原因有三:(一)甲午戰爭之后,先進的知識分子希望將日本當時先進的文化和技術引入中國,祈求改變中國的現狀。同時,來自清政府的經濟支持和政策扶持使日本成了當時知識分子們出國學習的首選之地。(二)日本與中國相鄰,文化和教育具有相似性,便于盡快投入學習,節省時間。(三)日本政府對于中國留學生的寬松政策:留學不受身份的限制,不重考試,并且在中國開辦預科學校,如1904年底,日本實踐女校設立清國留日女子師范工藝速成科,為來日本學習美術的留學生們創造了有利條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女子美術教育之所以能在民國時期迅速實現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中國女性畫家之所以在民國時期融入世界藝術潮流之中,成為新時代的新女性畫家,具有海外留學經歷的女性畫家和美術留學生群體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日本近代美術教育有兩個特點:其一,19世紀70年代以后,日本在大工業生產背景下,美術教育主要為實業教育服務,這種實利主義的教育與歐洲實用功利美術教育的背景是一致的[5];其二,19世紀末,日本對西方美術教育模式的引入,在教學內容及模式上兼顧日本傳統藝術教育和西方現代藝術教育。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日本美術教育對中國近代美術教育,包括女子美術教育的興起和轉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中國女子留學最早是以伴讀身份出現的,她們以臨時留學生的身份跟隨父兄或夫婿出國就讀,如廣東籍女畫家何香凝在丈夫赴日兩個月后東渡日本留學。中國女留學生去日本學習美術多以日本女子美術學校、高等圭文美術學校、實踐美術學校圖畫科為主,這幾所美術院校均為當時日本國內頂尖的女子美術學校,說明中國女留學生們不僅勤奮刻苦,而且有著深厚的文化素養及藝術涵養,能夠快速適應在日本的生活及學校教育。1906年至1911年留日女學生中,在實踐女子學校工藝課學習的女留學生有王詩、胡懿瓊、徐秀榮、吳汝震、陶淑貞、耿桂英、禧扈云、張執、郭珊、束靜涵、陶淑仙、金振聲、王葆芬;在日本女子美術學校圖畫科的有何香凝,西洋畫科的有馬淑和、馮擷英。這些留學日本的中國女性畫家歸國后有相當一部分人從事美術教育工作或出版翻譯工作。她們仿照日本教育模式教學,使用的教材也大都是由留學生翻譯而來的日本美術書籍,甚至有的人直接采用日本教材。“美術”和“美術教育”的詞語和概念也在這時期,由中國留日學生引入中國。通過她們的努力,改變了中國女子重“德”的傳統美術教育模式,逐漸形成了較為完善的教育體系,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新式女子美術教育的發展。
近代中國美術教育體系前期以效仿日本美術教育體系為主,后期開始轉向法國美術教育體系。姜丹書在回憶20世紀的中國美術教育時曾說:“若以吸收外來的要素而論,先受日本影響最大,后受法國影響最大。”[6]在中國美術教育領域無形中形成了歐洲派與日本派的對峙。進入30年代后,整個中國藝術教育體系完全趨向于法國體系。潘玉良、蔡威廉、王靜遠、何玉蓮、方召麐、蕭淑芳、方君璧、鄒紫溟、李自新、蕭淑良、范新群、李志新、唐蘊玉、袁樞真、張荔英、楊化光、榮君立、陸傳紋、張悟真等留法女學生,主要集中在法國里昂國立美術學校、法國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比利時布魯塞爾美術學院、法國波爾多美術學校學習西方古典主義或現代主義繪畫,歸國后多任教于各美術學校。在教學過程中既注重基礎又強調理論學習,在專業上尤其強調技法的表現,并且鼓勵女學生積極參與社團活動和美術展覽,并常在雜志中發表她們的藝術觀點或是介紹西方藝術作品和藝術家,她們在法國教育體系的傳播和構建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
三
隨著民國時期女子美術教育體系的日趨完善,進而顯現出三種特性:其一,受到日本及歐美教育體系的影響,造成了中國近代女子美術教育的復雜性;其二,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造成了女子美術教育模式的多元性,民國時期的女子美術教育模式混合了家庭女子美術教育、女子美術職業教育以及女子師范美術教育三種模式;其三,女子美術教育的狹隘性。正如陶行知所言,中國近代女子教育簡直是“小姐教育”“少奶奶教育”“姨太太教育”的綜合教育。但是,對比民國以前的女子美術教育,可以說民國時期的女子美術教育以及女性的社會地位都實現了跨越式的進步,從而促進了中國近代新女性畫家崛起的第一步。
參考文獻:
[1]陳學恂.中國近代教育大事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69-72.
[2]肖海英.“賢妻良母”:近代中國女子教育主流[J].社會科學家,2011(8):41-43+47.
[3]史暉.轉型與重構:中國近代課程制度變遷研究[D].南京:南京師范大學,2011.
[4]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說[A]//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
[5]張楠木.徐悲鴻早期美術教育思想中的日本近代美術嬗變因素[J].美術研究,2017(2):83-88+97.
[6]姜丹書.我國五十年來藝朮教育史料之一頁[J].美術研究,1959(1):33-36.
作者簡介:周宇超,山東大學(威海)藝術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美術思潮、民國女性美術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