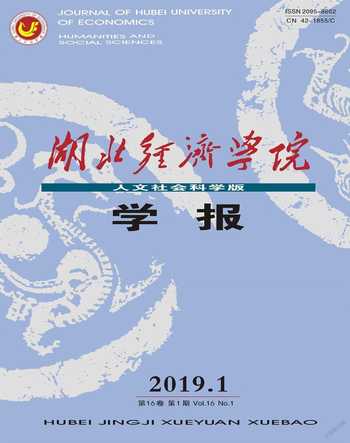淺析約翰·斯梅爾的階級形成理論
胡玲
摘要:約翰·斯梅爾教授主要研究英國近代史,所著《中產階級文化的起源》以17-18世紀約克郡的哈利法克斯為研究個案,再現了該教區的中等階層在經歷經濟、社會和文化變遷之后,如何具備中產階級意識,形成獨特的中產階級文化。在斯梅爾的中產階級研究中,他創造性地提出了“階級形成的文化理論”,還重視階級研究的地方性視角、階級的社會關系本質、性別關系在階級形成中的重要性等。斯梅爾的研究或將有助于推動我們對階級形成問題的研究。
關鍵詞:約翰·斯梅爾;中產階級;階級形成的文化理論;E.P湯普森
當代美國歷史學家約翰·斯梅爾是北卡羅萊納大學教授,主要研究英國近代史,尤其關注18世紀英國社會史。斯梅爾教授的專著《中產階級文化的起源》由武漢大學的陳勇教授翻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至今已經十余年。該書是國內第一部研究近代英國中產階級形成方面的譯著,它以17-18世紀約克郡的哈利法克斯為研究個案,再現了該教區的中等階層在經歷經濟、社會和文化變遷之后,如何具備中產階級意識,形成獨特的中產階級文化。本文將從“階級形成的文化理論”、階級研究的地方性視角、階級的社會關系本質、性別關系在階級形成中的重要性等方面分析斯梅爾教授的階級形成理論,希望有助于推動我們對階級形成問題的研究。
一、“階級形成的文化理論”
斯梅爾有關近代英國中產階級的研究中,著力思考了馬克思主義與后結構主義在階級問題上的矛盾,借鑒了皮埃爾·布迪厄、安東尼·吉登斯、馬歇爾·薩林斯、克利福德·格爾茲的理論,提出了富有見地的“階級形成的文化理論”。該理論解決了這樣一對矛盾,即“階級是社會經濟實際的反映”與“階級是社會建構”。[1]7斯梅爾認為,階級也是一種文化,這種文化既是社會經濟實踐的反映,也不斷地被社會經濟實踐所重建,兩者是相互作用的關系,即“文化既建構實踐同時又被實踐所建構”[1]53。斯梅爾在工場主一工人關系方面的論述是這一理論的極好例證。
18世紀哈利法克斯的毛紡織業發展很快,一方面表現為家內制的擴張,更重要的是結構變化,即出現了工場制造業,出現了工場主或商人一工場主。17世紀晚期,已經有工場出現,但當時工場主很少。到18世紀中葉,工場主的數量和經營規模都已十分龐大。由于工場主既是生產者也是銷售者,他們與市場聯系緊密,比家內制的工匠更能洞悉市場需求信息,由此也更注重對生產過程和產品質量的把控,還可以進行大膽創新以滿足新時尚。
斯梅爾認為,與上述經濟轉型相并列的是文化轉型.它改變了這個集團對自己經濟實踐的認識。18世紀上半葉,哈利法克斯的商業精英在對待他們的事業方面形成了一種更富于企業家精神的觀念,在對待他們雇用的工人方面形成了一種比較冷漠和客觀的關系。這些文化變遷與經濟發展過程存在著雙向互動聯系。
斯梅爾研究了喬納森·鮑姆福斯,他是1700年前后的富裕工場主,曾留下兩份遺囑。他的經濟實踐與18世紀中葉的工場主相似,雖然鮑姆福斯已經是富裕的工場主,但依然認為自己是約曼農,尊重手下工人和貧困鄉鄰,說明新的經濟實踐可以在舊的文化體系中發展。但鮑姆福斯及早期工場主們也在不知不覺中創造一種新的商業文化。他們把工商業活動視為一種投資,采用精確的簿記方法來計算成本與利潤,發展出新的謀利觀,勇于競爭等等。在市場競爭和壓力之下,工場主與制造者之間的關系發生了變化,制造者的獨立性逐漸喪失,“他被異化為獲取利潤的許多生產要素中的一個要素”[1]87,“轉化為必須受控制和管理的勞動供給者”。[1]89所以,工場主和制造者之間關系的個人色彩越來越淡薄,取而代之的是父權制的管理,原來的獨立工匠成為依附工人。
從上可以看出,斯梅爾的“階級形成的文化理論”強調“共時性”,社會經濟實踐既有助于新的階級文化的產生,又被新的階級文化所推動,它們之間是一種互動關系。在書中,斯梅爾指出自己與E·P·湯普森觀念的差異。湯普森在研究英國工人階級形成問題時,不像過去的史家那樣過于強調經濟因素,也沒有把工人階級看成是機器和工廠制度的產物,而是認為階級的形成既要有共同的經歷,又要形成主觀意識上的階級認同。斯梅爾分別用“長時段”、“短時段”對應于湯普森的“階級經歷”、“階級意識”,并引用湯普森的經典論述:“當一批人從共同的經歷(不管這種經歷是從前輩那里得來還是親身體驗)中得出結論,感到并明確說出他們之間有共同利益,他們的利益與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對立)時,階級就產生了”。[2](前言1-2)也就是說,階級經歷是長時段里慢慢積累的,或繼承自前輩,或體驗于自身.而階級意識則是短時段里表達出來的。斯梅爾沒有強調兩者的先后關系,正如上文提到的工場主一工人關系問題,這種個人經濟關系向非個人經濟關系的轉變、工人的生產要素化并非社會經濟實踐的一個最終結果,而是在經濟實踐過程中,應對市場需求、競爭壓力的自然轉變,這種轉變又反過來強化經濟發展趨向。階級既包括經歷也包括意識,它是一種文化,“是一種過程的結果,一個集團在此過程中理解自身的世界……即造就其成員看待和理解自身和他人行為的意義網絡。”在這種互動中,集團成員逐漸固定了自己在社會階級結構中的位置,產生了階級認同。所以,斯梅爾并不否認階級經歷和階級意識具有不同的時間框架,但他認為不應該“強調一種時間框架的時候忽視了另一種時間框架”[1]10。
二、階級研究的地方性視角
斯梅爾在其著作的“理論與方法”部分非常明確地指出,“我認為,中產階級文化起源于地方而非全國性的情境之中。”[1]16他選擇約克郡的哈利法克斯教區作為地方史個案,其著作的全稱非常能體現這一研究視角,即《中產階級文化的起源:1660-1780年約克郡的哈利法克斯》(該著作的完整英文標題是:The Origins of Middle-Class Culture:Halifax,Yorkshire,1660-1780),只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隱去了副標題。這個教區從自然地理條件上來說不適于農耕,從畜牧業所得收入也不豐裕,到17世紀后期,紡織業成為哈利法克斯經濟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當地居民收入的重要來源。因此,在該教區的社會結構中缺少占支配地位的地主或地主集團,以約曼農、手工工匠為主的中等階層居于突出地位。這時的哈利法克斯約有居民1.9萬[1]24,斯梅爾潛心收集了當時人留下的日記、信件、遺囑、財產清單、法庭檔案、教區登記薄、賬冊、壁爐稅及其它稅收記錄等,在這些一手資料的基礎上,非常細致地研究了以后一個多世紀里該教區中等階層經歷的社會經濟變遷。在斯梅爾研究的起始階段,中等階層仍以等級制的觀點看待他們的世界,對地方鄉紳有順從的一面。但是,紡織業使中等階層在經濟上較為獨立,他們也能夠對鄉紳的權威提出挑戰,從而表現出較強的獨立意識。另外,“中等階層是一個包容性廣泛的集團,其內部的社會關系是相對平等主義的關系。”[1]32斯梅爾正是在深入分析哈利法克斯教區這一地方特色的基礎上,探討該地中產階級文化的起源、階級意識的形成。
在斯梅爾的研究中,我們必須牢記他的兩點提醒:第一,雖然哈利法克斯的中產階級文化起源于地方,但不能忽視全國性文化對哈利法克斯中產階級文化形成的影響。例如斯梅爾在分析該教區貨幣市場的發展時提到,17世紀后期信貸對于哈利法克斯教區經濟的日常運行是必不可少的,但大量交易都是依靠教區內的私人借貸網絡,匯票的使用并不普遍。18世紀,隨著貿易活動越來越頻繁、規模越來越大、空間跨度越來越遙遠,哈利法克斯商人和工場主對匯票的依賴度增加,到18世紀30年代,匯票已廣泛應用于商人和工場主的各類交易中,甚至還擴大到其它領域。哈利法克斯貨幣市場的發展既是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也是對逐步完善的全國性金融網絡系統的積極回應。
第二,哈利法克斯中產階級文化起源的模式不能簡單地放大到全國范圍,如斯梅爾所說,“地方史并不能作為一種分析的樣本.而應該作為一種分析模式”[1]16。哈利法克斯與利茲、布拉德福德、蘭開夏、謝菲爾德、伯明翰、倫敦的經濟文化發展存在很大差異,各地的中等階層都與自身的經歷產生共鳴,碰撞出各具特色的中產階級文化。所以,“在18世紀,并不存在一種單一的中產階級文化。更確切地說是形成了多種多樣的地方文化,每一種文化都是當地情境的特殊回應,特別是當地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產生方式的特殊回應。”[1]I8
那么,地方性中產階級文化如何成長為全國性的中產階級文化?斯梅爾認為這需要很長時間,在這一過程中,工業革命的發展與中產階級的成長互相推進,互為因果。哈利法克斯的商業和專業精英們在社會經濟實踐中發展出新的價值觀念,這些新觀念反過來又推動了工業革命的進程,最終,地方性的中產階級文化在更廣闊的范圍獲得認同,抽象為全國性的中產階級文化。斯梅爾認為,到18世紀末,英國才出現高度一致的中產階級文化。
三、階級的社會關系本質
階級是一個異常復雜、難以定義的概念,階級的形成過程也遠非人們想象的那么簡單。著名的E.P湯普森用75萬字的篇幅論述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當我們仔細閱讀其著作《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時,所能看到的只是工人的日常生活、家庭教育、叻會組織、閑暇、人際關系、政治運動等等。所以,階級應放在與其它階級的關系網中進行認識。“階級是一種關系”[2](前言3)。“我強調階級是一種歷史現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種‘結構’,更不是一個‘范疇’,我把它看成是在人與人的相互關系中確定發生(而且可以證明已經發生)的某種東西。”[2](前言1)在方便研究與操作的三分社會階級結構中,工人階級處于底層,其外部關系都是“下對上”的問題,而中產階級作為社會的中間層,向上,要區別于貴族,向下,要區別于工人階級。“中產階級認同感的產生必然與工人階級的情況不同,它不僅僅與.個集團有關,而是與兩個集團——仁層階級和工人階級都有關系。”[1](前言)所以,在研究的過程中,斯梅爾更兼顧了兩組重要關系,并分別用簡明的“節儉”和“文雅”來概括其特征。
在斯梅爾看來,形成中的中產階級對待土地貴族的態度比較復雜。在批判土地貴族方面,中產階級“挪用”了“品德良好的鄉紳對腐敗的宮廷貴族的批判”,然后根據自己的社會經濟實踐加以利用,最終“將自己對于政府政策的批判建立在商人美德的基礎之上”[1]231-235。他們認為自己的勤奮、節欲、節儉、審慎,與貴族的懶散、縱欲、揮霍、輕率形成了強烈對比,所以具有道德上的優勢,即自己高尚的生活方式相比于富人游手好閑等惡習所具有的優勢。斯梅爾在總結中產階級區別于貴族的特征時用“節儉”一詞加以概括。另一方面,中產階級與土地貴族之間又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滑動”,界限有時模糊不清,比如哈利法克斯商界精英和專業人士購買莊園、采用鄉紳分配地產的長子繼承制、與土地所有者通婚等,這說明新興的中產階級文化中存在著一定的矛盾因素。
與中產階級對土地貴族態度矛盾、界限不清的情況相反,中產階級與下層工人階級則容易區分得多,斯梅爾以“文雅”一詞概括兩者的區別。18世紀中葉,雖然公共和私人領域的界限還不明確,但逐漸形成的私人領域仍極大地幫助哈利法克斯的中產階級同他們之下的群體區分開來。這些商業精英、專業人士的家庭,妻子退出勞動領域,專事家庭、子女教育及社交活動,她們可以成為某個組織或社團的成員,如斯梅爾提到哈利法克斯的流通圖書館。要成為流通圖書館的會員必須捐助1基尼并交納每年5先令會員費,這一限制就將教區大多數人口排斥在外[1]168。此外,我們還應該考慮到文化水平、閑暇時間,這些都使他們與普通工人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在明確階級間界限的同時,也深化了他們內部的階級認同感。
四、性別關系在階級形成中的重要性
斯梅爾在闡述其理論基礎時寫道:“私人領域里中產階級的認同感產生的核心問題是性別,因為就中產階級形成所必需的社會分化過程而言,一系列新的性別關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1]20可見確立一套新的性別關系在中產階級形成過程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如上文所述,18世紀中葉哈利法克斯的商人、工場主和專業精英世界已經出現了公共和私人領域的分離,男人們逐漸主場商業、政治事務,女性則退出勞動力領域,其活動集中在比較確定的私人領域。這樣一套新的性別關系首先彰顯了成長中的哈利法克斯中產階級的經濟實力,有利于他們內部的階級認同,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把他們與之下的集團區分開來。
在這套新的性別關系形成的過程中,婦女的“有閑”成為重要的條件和標志。原來的中等階層家庭中,勞動和生活無法明確區分,勞動場地和生活住所合二為一,婦女是社會經濟活動的重要參與者。而成功的哈利法克斯商業精英和專業人士,有實力讓妻子們過一種有閑生活,以享受閑暇這種奢侈品來標志自己的社會地位。斯梅爾以17世紀末的蘇珊娜·賴利和1760年的蘇珊娜·利斯為例進行對比,前者作為寡婦從丈夫那里繼承產業并潛心經營,而后者成為寡婦時,其丈夫在遺囑中強調,她不能參與丈夫塞繆爾制造業的任何繼承事宜,她每年將獲得40英鎊的年金,只要她不再嫁他人,就可以住在原來的宅邸。斯梅爾提出,涉及這兩名婦女的遺產處理上的變化,本質上是“一種文化變遷”,即利斯及其丈夫認同婦女不參與生產勞動。到18世紀中期,這種認同已經遍及哈利法克斯的精英集團。該集團的婦女們的主要職責在于營造溫馨的家庭、教育子女、參與各種非政治性聚會、家庭間互訪等等,她們從“生意婦女”變成了“全職母親”、社交能手。雅致的客廳、精美的茶具、有會員資格限制的社團、互贈禮品的拜訪.這種無工作的生活方式展示了等級,[3]86拉大了與下層集團的距離。
對于階級形成問題的研究,國內學界非常熟悉的歷史學家當數E.P湯普森,他半個世紀前的巨著《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被譽為研究近代英國工人階級的經典。工人階級與中產階級同為近代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新興階級,兩位學者的研究必有相通之處,如他們都非常重視文化在階級形成中的作用、關注階級的社會關系本質。但是,兩者之間的差異也非常明顯。作為工業革命中逐漸富裕、政治成熟、價值自信的階級,斯梅爾從地方性視角研究中產階級文化的形成,可以說,中產階級是自帶思想家和組織者的,他們在地方性范圍內就聯系密切,易于形成區域性的中產階級文化,經過時間的積累,進而抽象為全國統一的中產階級文化。而工人階級在這方面經歷了更長的時間。再者,豐厚的經濟基礎也使中產階級的女性擺脫了體力勞動,她們的職責就是“代理消費”,通過她們的各類消費、會員身份等來彰顯本階級的地位。因此,他們研究方法和側重點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研究對象的特殊性決定的。更深入地探究兩位學者階級研究的異同,雖然對于推進階級問題研究大有裨益,但非筆者能力所及,希望本文有拋磚引玉之用,也正契合我們學術界近些年來的中產階級研究熱。
參考文獻:
[1][美]約翰·斯梅爾中產階級文化的形成[M].陳勇,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英]E.P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上)[M].錢乘旦,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
[3]Leonore Davidoff and Catherine Hall,Family Fortunes:Men andWomen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1780-1850,London andNew York:Routledge,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