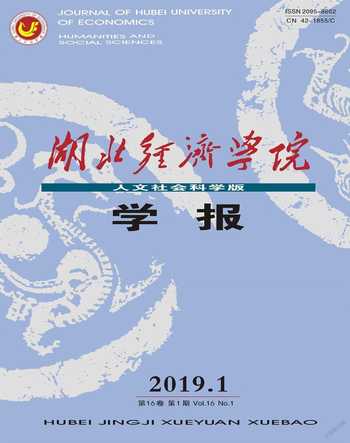從廢名小說的敘事視角談廢名“詩化小說”的構(gòu)建
賴寒梅
摘要:廢名被認為是現(xiàn)代文學中詩化小說的鼻祖,字面上“詩化小說”除了在內(nèi)容上多作者的自我抒情性、田園牧歌式表達以外,更多是文體上的敘事形式的革新,廢名用新詩手法作小說,在形式化了的散文筆法的統(tǒng)籌下兼用詩歌與小說兩種文體敘事視角。雖然不可避免的使其敘事文本呈現(xiàn)簡潔卻晦澀的特質(zhì),但最終完成了其詩化小說文體革新,更是滿足了廢名“合內(nèi)外”的夢的意識寫作要求。
關鍵詞:敘事視角;詩化小說;廢名;夢的意識
一、“我用我的形式寫我的內(nèi)容”——廢名的新詩觀
作為非韻文的散文和和韻文的詩歌是傳統(tǒng)文學體裁劃分,而五四新文學以來,詩歌、小說、散文與戲劇一起并列為新文學的主要四種體裁。就小說和散文的關系而言,二者本來就有屬于非韻文的廣義的“散文”性質(zhì),用現(xiàn)代漢語創(chuàng)作的新詩具有散文化傾向。但是這些文體之間外在敘事形式形態(tài)的固有的關聯(lián)性并不意味著廢名具有詩化性質(zhì)和散文化傾向的詩化小說創(chuàng)作僅是時代必然所致,而沒有個人獨特的創(chuàng)造性。相反,通過對廢名的新詩觀念的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的是廢名后來的詩化小說的敘事策略是基于他作為一個詩人的個人性獨特創(chuàng)造。
廢名認為“舊詩的內(nèi)容是散文的,其詩的價值正因為是散文的。新詩的內(nèi)容則要是詩的,若同舊詩一樣是散文的內(nèi)容,徒徒用白話來寫,名之曰新詩,反不成其為詩。”叼聽謂新詩的內(nèi)容是“詩的內(nèi)容”,也就是詩人個人的“詩的情緒”,“等到他覺得他有一首詩要寫,這首詩便不寫也成功了,因為這個詩的情緒已自己完成。”“詩之來是忽然而來的,即使不寫到紙上而詩也已成功了。”相反舊詩的內(nèi)容則是“散文的內(nèi)容”,舊詩是在人與外在世界之間“情生文,文生情”的觸發(fā)下形成與現(xiàn)實生活整體性一致的散文式內(nèi)容。因此舊詩的文學性本質(zhì)不在詩的內(nèi)容,而在詩的格律化形式。所以‘他們寫詩自然也有所觸發(fā),單把觸發(fā)的一點寫出來未必能成為一首詩,他們的詩要寫出來以后才能成其為詩。”也就是說,就詩歌與散文兩種文體而言,舊詩在內(nèi)容上與散文一致,舊詩的感情都可以用散文來表現(xiàn),可以鋪開成一篇散文“一篇詩便一篇散文,,@,而沒有固定寫作形式的新詩在形式上則與散文一致。所以,在文體的敘事形式上并沒有外在關聯(lián)的新文學中的詩與散文這兩種體裁便能在小說創(chuàng)作這一的敘事實踐中同時運用,使得小說兼有詩歌和散文兩種文體因子。
可以說,廢名的新詩觀念中“散文形式”一說并非僅僅只是為了對舊詩中格律形式進行反抗而提出來的,這種不受束縛的散文式文字更是在五四思想解放的語境下與人的個體性的覺醒相適應的,所以,進入人自我的個體性自由想象便是新詩的內(nèi)容,因為想象本身就是個體不被外在束縛的自由的表現(xiàn),是一個開始,一開始便已是必然了的完整的東西。若以“自由”作為詩歌的核心,廢名認為新詩的“自由”大體上就是詩人個體性的詩情,因此,舊詩在詩歌內(nèi)容上是不自由的,因為。舊詩的“自由”只能是符合舊詩的格律文法的行云流水的形式自由,所以,在本質(zhì)上,舊詩“行云流水仍是隨處糾葛”,又是不自由的。但另一方面,舊詩中卻又存在符合新詩在內(nèi)容上表達個體的自由想象的部分,即舊詩中用來表達散文內(nèi)容的辭章形式中所呈現(xiàn)的審美性的圖畫式鋪排。因此廢名不把舊詩中的鋪排的文采僅看作是詩歌的形式,即服務于散文式內(nèi)容表達技巧部分,而是一種基于詩人個體想象的自由的體現(xiàn),是形式更是內(nèi)容,“鋪排的地方乃是詩的文采,乃是詩人的感情。”但這只屬于“新詩”內(nèi)容,因為“舊詩不能把天上的一顆星寫下這許多行的句來。”所以,廢名認為就新詩與舊詩的關系來看,二者具有一定的承繼關系,雖然舊詩的內(nèi)容是“文生情情生文”觸發(fā)下的散文,但更準確的說,其中含有新文學中“新詩”和“散文”兩種體裁的內(nèi)容“舊詩絕句有因一事的觸發(fā)當下便成為詩的,這首詩的內(nèi)容又正是新詩的內(nèi)容。”新詩的形成可以從舊詩中尋得其漢語文學傳統(tǒng),即溫李的詩詞創(chuàng)作。“溫詞無論一句里的一個字,一篇里的一兩句,都不是上下文相生的,都是一個幻想,上天下地,東跳西跳,而他卻寫的文從字順,最合墨繩不過。”也就是說廢名認為與一般的舊詩不同的是,溫李的詩詞在辭章創(chuàng)作上的圖畫式鋪排并非“文生情情生文的”散文式的抒情,而是詩人馳騁個人幻想的自由的表現(xiàn),是詩人個性與理想。”釗園此,廢名的關于新詩的創(chuàng)作理念上,認為“新詩將是李溫一派的發(fā)展,因為這里無形式,意像必能自己完全,形式又是還是一個障礙。”因此,新詩既要突破李溫詩詞本質(zhì)上作為舊詩的形式束縛,新詩是“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有什么題目,做什么詩;詩該怎么做,就怎么做。”用散文的文字,同時也要用審美性的此辭章來鋪寫詩人個體性的神秘的卻完整的“詩情”,因此他認為卞之琳的《車站》一詩是最美麗最新鮮而且最具體的詩,“詩情是無我的,是美麗的……你就是釘一只蝴蝶在墻上,雖然無聊、雖然著急,還是美麗,即是詩情美麗。”侶詩情的“無我”是作為個體的我馳騁于自由境地的狀態(tài),是情感的切實,也是詩之空靈之處。而釘在墻上的美麗的蝴蝶也就是用辭章鋪排成的像夢一般的美的圖畫。所以總的來說,廢名關于新詩的“詩的內(nèi)容,散文的形式”的提法,“不僅有對于早期白話文理論進行修正的功能,同時通過發(fā)掘了漢字的審美性的規(guī)律。”
總的來說,基于廢名的新詩觀念,廢名后來在小說創(chuàng)作上的詩性特質(zhì)和散文化傾向就不言而喻了。即廢名這種有意識的文體形式革新的基點并非為了形式本身而革新,而是為了表達內(nèi)容而進行的形式創(chuàng)造。
二、小說創(chuàng)作的詩化和散文化傾向——“詩化小說”
根據(jù)托多羅夫的敘事詩學理論,敘事視角層面是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構(gòu)建敘事文本的構(gòu)成要素之一,“在閱讀文本的過程中構(gòu)建一個想像的世界,該文首先必須是指稱性的;讀完文本……想象力工作起來,并借助……的信息:對這個世界的描繪在何種程度上是忠實的(語式層面)?事件是按什么順序展開的(事件層面)?應該在何種程度上考慮敘事的反射器帶來的變形(視角層面)?”互也就是說,文學文本的敘事形式影響讀者對文學文本的想像性構(gòu)建進而促使該文學文本的風格的判斷和形成,因為在敘事文本中,事件敘事“視角”決定著(敘事文本的)構(gòu)建工作,所以,就對廢名“詩化小說”的創(chuàng)作風格的解讀而言,對其文體形式的敘事視角來解讀就有必要性。
廢名說自己借唐人絕句做小說,在這里唐人絕句并非古典詩歌意義上唐人絕句,而是在新文學運動的語境下被作者認同為是新文學形成的漢語文學資源概念上上唐人絕句。非但唐人絕句,溫李的詩作更是對廢名進行新小說創(chuàng)作的敘事資源。因為在廢名看來新詩(文學)與舊詩(文學)之間本來就有一定的承繼關系。所以說,與其說是廢名用古典詩歌技法做小說,還不如說是用新詩手法做小說,才是廢名進行其“詩化小說”敘事形式探索的關鍵。
敘事形式的運用和探索在廢名個人的寫作歷程中尤其階段性特點,名最早是進行新詩創(chuàng)作的,到后來,其寫進行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逐漸向以寫新詩的手法進行小說創(chuàng)作。本來,在廢名的文體觀念中,散文、詩歌和小說三者之間的關系充滿了暖昧,所以在創(chuàng)作上特別是《桃園》以后的小說創(chuàng)作中,以《橋》為代表,其跨文體的敘事形式特質(zhì)愈加明顯。早期的小說創(chuàng)作中,是按照傳統(tǒng)的敘事手法,即或是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稱敘事視角,也或者,以“我”作為第一人稱的內(nèi)在聚焦方式,雖是內(nèi)聚焦敘事,但“我”是故事的參與者,并按照與現(xiàn)實生活同步的時間順序進行在逐漸的故事參與中推動故事的向前發(fā)展,且在語式層面和時間層面都是認知性的,指向性的,以滿足對故事的認知為主要目標。如果說,早期小說敘事在敘事視角上多用全知全能的視角,那么說,在后來的傾向用新詩手法進行小說創(chuàng)作的敘事形式的創(chuàng)造性之處就在于限制性敘事視角的運用。在廢名的文體意識中,詩歌和小說作為兩種皆然不同的小說體裁,二者的不同之處就在于敘事視角的差異。“詩與小說恐怕實在兩種體裁,一個好比一位千金小姐,不出門一步,自己驕傲自己的天資國色,一心要打扮得好看,結(jié)果也真實個絕代好看,……,然而女子當她臨妝對鏡時注意自己的意思多注意旁人的意思少,這就好比詩;又如一位大架子的妓女,閱歷多了,什么都見過,對鏡自照的意思卻甚輕,然而打扮的本領非常之大,隨手都是巧妙,隨人都可親近之感,然而她生來是一個大方之家,誰也不敢狎而玩之,這就好比是是一種小說,做到深入淺出。”也就是說,就詩歌和小說兩種不同體裁的敘事形式中的視角層面而言,詩歌的敘事視角是限制在故事人物個人的局限性視角的,即“注意自己的意思多”,而小說的敘事視角層面則是全知全能的,是多注意旁人的意思而少“對鏡自照”。
與同時期的短篇小說中的主要的全知全能敘事視角相比,小說《桃》中有一段較為獨特的聚焦在人物的限制性視角的描述,“窗孔里射進來月亮月光,王老大不知怎么的又不平!月光居然會移動,他的酒瓶放在一角,居然會亮了起來!王老大怒目而視。”坷以看到,雖然在敘事文本的中依然運用第三人稱的指稱方式,但在外在的客觀場景中描繪中更強調(diào)故事人物的個人性視角,即在所描述場面或故事后面有另外一個故事的旁觀者在“觀看”,而且這種旁邊人物的“觀看”行為更成為建構(gòu)敘事文本的主要部分。也就是說在限制性視角下的敘事“文本變得更加重視時,我們會考慮到A轉(zhuǎn)述的事件,B.‘看待’這個事件的人的態(tài)度。”魚堿予了敘事文本的暗示性含義和隱喻性。所以在聚焦于人物個人的限制性敘事視角中,文本風格雖表面上簡潔但實質(zhì)上依然晦澀。也就是說雖然敘事上只是一段看似直白簡單的描述,但是由于所用的限制性視角依然可以看到直白性描述背后的故事人物的參與。這種視角運用的方式實際是作者有意的對故事的獨特性建構(gòu)。留下的許許多留白供讀者在閱讀時進行建構(gòu),也能讓故事的講述本身充滿內(nèi)在張力,而且往往會因為過于簡潔的敘事產(chǎn)生晦澀難解之感。讀者在建構(gòu)閱讀文本的時候“必須與作者處于同一個基調(diào)上面,閱讀才有可能,……讀者要時時想著與北大講師處于同一個基調(diào),而且還要時時顧及到他那飄忽不定、幽深曲折的心思,實在有些苦惱了。”雖然廢名用其詩性思維及手法進行小說創(chuàng)作,所以無論就敘事文本的時間層面還是語式層面都有表現(xiàn)其作為詩人的獨特的個體性之處,而且顯得晦澀難懂。同樣的在文本敘事的視角層面亦如此。以解讀以下一段為例:
“說實在他自己也不知道站在那里看什么,過去的靈魂愈望愈渺茫,當時的兩幅后影也隨著帶遠了,很像一個夢境。顏色還是橋上的顏色。細竹一回頭,非常之驚異于這一面了‘橋下流水鳴咽”仿佛立刻聽見水響,望她而一笑,從此這個橋就以中間為彼岸,細竹在那里站住了,永瞻風采,一空依傍。”
……
“這個橋我并沒有過”
說得有一點感傷。
“那一棵樹還是同我隔了這一橋。”
接著把兒時這段事實告訴她們聽。
“我的靈魂還永遠是站在這一個地方,——看你們過橋。”
這段被認為是確立小說以“橋”為中心意象的重要描寫,在時間層面上,這是一段由小林在跟細竹聊天時回憶起看小琴和細竹過橋的一段,而在語式層面上,“我的靈魂還永遠是站在這一地方”,飽含了遁迷于個體無我狀態(tài)的詩情意蘊。而作為小說的敘事文本,其中最精彩之處是在小林限制性視角下看到的細竹站在橋中間回頭的圖像式描繪。這段描寫并非全知全能式的對細竹站在橋中間的純客觀化描寫,而是在小林“他”的限制性視角下的描寫,所以能夠很好的將故事的另一主人公又是這一圖景的觀看者的小林的真切情感融入,“‘橋下流水鳴咽”仿佛立刻聽見水響,”是小林的想像與幻覺,簡潔的描繪卻像“一個夢境”顯得晦澀,另讀者難以捉摸又能真切的感知其“味”。正好印了那句“敘述所描繪,不是書自身的世界,而是位于每個人心理改造過的世界。”大概,這也是在中后期的廢名小說創(chuàng)作中大量運用限制性視角的意義所在。雖然限制性敘事視角有其文本建構(gòu)意義,但是并不是小說創(chuàng)作畢竟不是做詩,所以聚焦于人物個人的限制性視角與全知全能的小說傳統(tǒng)敘事視角在廢名的詩化小說的過渡和切換中又是依循作家個人的自由意趣而呈現(xiàn)出散文化傾向。比如短篇小說《桃》:
“窗孔里射進來月亮月光,王老大不知怎么的又不平!月光居然會移動,他的酒瓶放在一角,居然會亮了起來!王老大怒目而視。,,@
前兩句是全知全能的敘事視角,而“月光居然會移動,他的酒瓶放在一角,居然會亮了起來”則是人物的限制性視角,接著又轉(zhuǎn)換成原來的視角。除了兩種敘事視角,在廢名詩化小說創(chuàng)作中的敘事者聲音與作者聲音的分離,作者聲音直接進人小說敘事文本亦是小說文體創(chuàng)作的散文化的表現(xiàn)。但是,反過來使得散文式的表達方式形式化,前面提到過,“散文的形式”是廢名對新詩的形式規(guī)定,也就是說相對于舊詩的格律文法形式來說,新文學中包括詩歌和其他文體的散文化傾向是在辭章文法上是“非形式”的,但這種散文化的辭章文法是建立在作者個人性體驗基礎上的,所以在本質(zhì)上又是詩性的,是形式化文體化了的。而將形式化文體化的散文的表達植人小說文體創(chuàng)作卻是屬于廢名個人的獨特性文體創(chuàng)造了。比如下面一處:
“何家小姑娘導引細竹進來,他正在桃畦之間,好像已經(jīng)學道成功的人,凡事不足以隨便驚喜,雷聲而淵默,——哀哉,桃李下自成蹊,人來無非相見,意中人則反而意外了,證天地之不幻,枝枝果果畫了這一個人的形容。看官,這絕不是誑言,大塊文章,是可以奏成人的音樂。只可惜落在我的紙上未必若是其推波助瀾耳。”
用“枝枝果果畫了這一個人的形容”的桃園畫面小林意外看到同在桃園的細竹之時所“視”,更是“視”者小林淵默的內(nèi)心中像雷聲一樣“意外”之驚的詩意表達。“枝枝果果”的桃園畫面是小林當時的心理狀態(tài)的象征,不是“文生情情生于文”的散文式內(nèi)容而是幻想的畫面,是一幅夢一般的美的的畫面。同時,字與字之間、詞組之間、語音之間是用無格律無形式的散文式書寫,是“散文的形式和詩的內(nèi)容”的新詩的本質(zhì)。最后直接跳出作者的聲音來引導讀者的閱讀更是作家個人自由隨意感發(fā)、落筆的散文筆法。即擺脫做小說亦以故事情節(jié)的戲劇沖突和人物的形象塑造為中心作為其小說形式的束縛,作者本人的敘事亦不具絕對權威性,而只是參與到文本建構(gòu)中的其中一種聲音。
三、夢的意識寫作與文體形式的革新
小說《橋》明顯是受到禪宗思想影響創(chuàng)作的,而且禪的思想不僅在內(nèi)容上增加創(chuàng)作的空靈唯美處,也在文體形式的革新上起到作用。比如喜歡沉默、冥想的小林就常表現(xiàn)出其個人獨特的想象性世界的來,像夢般“我常常觀察自己的思想,可以說同畫幾何差不多,一點也不能含糊。我感不到人生如夢的真實,但感到夢的真實與美。”“夢乃安眠之上隨喜繪了一個圖。”在廢名的讀禪著作《阿賴耶識論》中,廢名認為提及“夢與記憶是第六識即意識作用,第六識是心的一件,猶如花或葉是樹的一件,……是可經(jīng)驗的。”第六識是對五官識相的超越,是“心”是合內(nèi)外,其經(jīng)驗對象不再“外”。“所謂內(nèi)外之分,是世俗的習慣。見必要色,聞必要聲,是一件事的兩端,聲與色無所謂外,不是絕對的‘對象’。意識的相分本不如五官識的相分為世俗所說的那個外在的對象罷了。”屬于第六識的夢是維度對于個人來說是可以合“物”“我”的狀態(tài).此種向內(nèi)的意識維度使得廢名在個人平淡日常的生活操作中卻依然保持對個體獨特的生命哲學及體驗,即“經(jīng)歷上的平淡只是造成限制作家視野的一種可能性因素,而作家內(nèi)在的豐富則不受限制。”而且內(nèi)向型的生命哲學更使廢名落實到日常生活而且更專注于人的精神的心靈內(nèi)在的超越性,肆于物且超越于物,而表現(xiàn)了夢一般“合內(nèi)外”詩性生存狀態(tài),似乎就用到跟詩歌“對鏡自照”那樣的聚焦于人物的限制性的敘事視角。但是人物的限制性視角所視見的是美麗畫面本身亦是假,是為不可信,所以客觀畫面本身只是物而不是體,雖然廢名試圖將“體物”合一,但其創(chuàng)作中過于迷戀于夢一般美麗的幻想的畫面中往往并無真實感,更多只是夢一般的美感。無論是作者還是故事人物一直處于夢一般的美的畫面之中,小林和細竹在靜默的對視中留下了的淚水,琴子在知道小林和細竹晚上一起到河灘邊玩時心中起的“妒”意……終究是對物及影像的執(zhí),即妄念的一面。雖然作者在后面禪悟到“物不可執(zhí)著,猶如影像不可執(zhí)著,執(zhí)著祂祂沒有,是妄想。”但至少在廢名中期的小說創(chuàng)作中整體的敘事語式上多少不能擺脫“低吟徘徊,顧影自憐”的基調(diào)。但作為以新詩手法做小說的文體形式革新的實踐,視角層面將審美的圖畫的一面融入小說敘事.其意義便易見了。
參考文獻:
[1]王風.廢名集·第四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2]格非.廢名小說[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3.
[3]李筱寅.廢名小說的文體特征和修辭方式對新文學文類的創(chuàng)新[D].南京師范大學,2012.
[4][法]托多羅夫.散文詩學:敘事研究論文選[M].侯應花,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11.
[5]眉睫.廢名先生[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