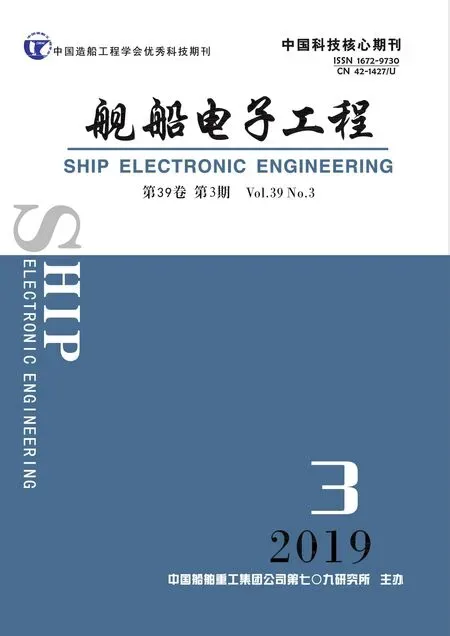基于ADS1258的多通道溫深監測裝置應用研究?
晁大海 范業明
(海軍駐大連地區軍事代表室 大連 116013)
1 引言
隨著人類對深海環境不斷探索,水下探測設備攜帶高性能的探測裝置用于發現更多未知信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而探測裝置采集信號的精確性決定于采集芯片自身的采集精度和采集芯片外圍電路設計[2]。本系統則針對探測裝置水下采集溫深信號實時性要求不高,而對采集精度要求較高實際情況,選取STM32F103處理器和ADS1258模數轉換芯片聯合工作進行溫深數據采集,通過平均處理方法將均值處理之后的數據上傳到海面躉船計算機中,經過電壓信號轉換為物理量信息處理從而實現水下設備位置信息的精確獲取[3]。
2 技術方案
如圖1所示,本次深海探測系統以采集溫深數據為例,主要分為四個部分,具體內容如下:
1)數據采集單元:主要完成溫深模擬量數據采集,并轉換成對應的數字信號。
2)STM32處理器。該裝置主要通過STM32F103處理器,控制數據采集單元并接收該單元傳輸的溫深數據,經過數據處理后通過485控制器傳輸到海面躉船的計算機中[4]。
3)數據收發單元。利用485控制芯片,實現水下溫深探測裝置與躉船監測中心的數據通信[5]。
4)躉船監測中心。利用水面躉船監測中心對水下探測裝置發送來的數據進行接收、解析、顯示處理[6]。
系統工作中,溫深傳感器是集成到水下探測裝置上的,數據采集單元輸出端與STM32處理器連接,采集的數據在經過STM32處理器處理后,通過485控制器傳輸至水面躉船的計算機中進行處理和顯示[7]。圖1為系統工作示意圖。

圖1 系統工作示意圖
系統工作過程中,由于溫深傳感器為4mA~20mA電流信號輸出形式,所以信號采集需要通過串行接入100Ω電阻,轉換為電壓形式輸出[8]。通過數據采集單元和STM32處理器,讀取100Ω電阻兩端的電壓值并轉換為對應的溫度、深度物理量[9]。另外,考慮到實際應用需求,水下探測裝置與水面躉船監測中心進行數據通信主要采用了485通信機制,使其能夠進行長距離的數據傳輸,保證數據傳輸的精確性和穩定性[10~12]。
3 硬件設計
本次系統硬件設計如圖2所示,主要介紹了STM32F103處理器、AD1258芯片電路之間的組成部分。AD1258芯片設計采用兩個通道(AIN10,AIN11)分別采集溫深傳感器輸出在100Ω上的電壓值。AIN10采集的是溫度值,AIN11采集的是深度值,如圖2所示。

圖2 硬件設計方案
由于ADS1258通信方式屬于串行數據輸出工作模式,即所謂的SPI通信模式,基于此,我們根據STM32F103芯片通信接口設置和實際電路板布局需求,選用STM32F103的SPI2口作為與ADS1258進行通信接口,完成命令下達和多通道溫深數據的采集傳輸功能。
4 軟件設計
本次系統軟件設計的整體流程圖如圖3所示。首先,系統上電初始化,實現STM32F103芯片引腳、通信引腳定義初始化,設置ADS1258芯片工作模式、采樣率等參數,如表1所示。之后,進行喂狗操作,實時保證系統程序設計的可靠性。接著,等待ADS1258芯片發出數據準備好中斷。如果沒有中斷,返回上一步急需喂狗,如果發生中斷,則立即讀取通道AIN10,AIN11數據,將采集后的數據分別進行個數和數據值累加。
本次系統對AD1258具體參數設置如下所示:
參數DRATE=00,即ADS1258芯片采樣率1831Hz;參 數 DLY=111,延 遲 后 采 樣 率 變 為1075Hz;參數CHOP=1,即采樣率減半設置;MUXSG1=0x0C,即AIN10,AIN11 2通道采集數據,所以每通道1秒采集點數=1075/2/2Hz,約等于268Hz,即系統每1秒鐘采集268個采樣點數據。基于此,可以得到系統每采集200個采樣點需要時間小于800ms,便可以進行平均處理(<10μs),之后進行均值數據發送(<10μs),使得整個采集、平均處理和發送一次有效時間小于1s,符合系統多通道溫深監測設計要求。另外,由于ADS1258采樣精度為24位,所以在每次每個采樣點存儲時,需要三個8位無符號數據單元進行存儲。如果采集點個數達到200個點時,需要定義600個無符號8位數組進行存儲。當滿足200個采集點時,可進行一次平均處理并將計算的結果發送到上位機進行電壓轉物理量處理。

圖3 系統軟件整體設計流程

表1 ADS1258采集芯片設置參數
系統采集溫深數據后,通過485控制器向水面躉船上計算機發送。系統使用了平均處理后上傳平均值的方法,替代了傳統的即采即發數據傳輸模式。然后即采即發傳輸模式可能會由于整個傳輸通道數據吞吐量增加且STM32控制器采集數據速度高于傳輸通道數據傳輸速度,導致監測裝置數據傳輸可能會出現數據覆蓋、數據丟失或者錯誤的結果。而本文根據實際應用需求,對采集頻率要求不是很高的多通道溫深數據,采取降低采樣率、采集數據后求平均的方法以保證每個通道的高采樣精度。具體平均處理流程圖如4所示。
5 實驗室系統驗證
在實驗室中,將信號源與穩壓電源信號通過線纜連接溫深監測裝置輸入端,輸出端通過485轉USB調試線連接計算機[13~15]。通過上位機軟件對溫深監測裝置發送來的數據進行電壓轉物理量換算,并對每個通道采集所對應的物理量進行顯示。具體系統驗證中監測參數為數據采集點數和數據精確度(有效位)。

圖5 數據傳輸通信驗證
如圖5所示為多通道溫深監測裝置監測軟件設計界面。首先,設置穩壓電源輸出電壓為1.500DCV,信號源輸出信號為正弦波信號40Hz、電壓范圍0~2DCV。測試結果發現前部分穩壓電源輸出電壓值在1.500VDC~1.505VDC之間范圍波動,通過采集的電壓有效值與對應通道溫度、深度之間的物理換算,得到溫度值誤差<0.5°,深度值誤差<0.5m,滿足實際溫深監測裝置應用需求。測試結果后部分顯示的正弦波與信號源輸出信號波形相符合,功率譜顯示40Hz信號,說明采樣點基本不丟失,滿足實際應用需求。
6 結語
本文詳細介紹了基于ADS1258的多通道溫深監測裝置構成、多通道高精度數據采集軟硬件、實驗室驗證過程和結果。其中,根據監測裝置實際應用需求,對采集周期要求不高的數據在監測裝置中累加求平均、傳輸,以保證每個通道的高采樣精度。在不影響整個系統的控制功能前提下,減少了傳輸通道數據吞吐量,保證了數據傳輸的精確性,使得數據傳輸的可靠性、穩定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