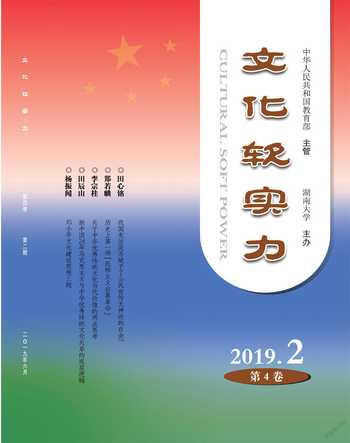歷史上第一場“民粹主義右翼革命”
鄭若麟
法國著名歷史學家、曾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就預言美國將走向衰退的艾瑪紐·托德(Emmanuel Todd)曾就“黃馬甲運動”發出警告:“坦白地說,我懷疑馬克龍在智力上能否理解正在發生的事……”“法國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極端化;所謂精英,即巴黎上層拒絕與人民進行談判。”所以,托德的結論是:“法國的最大的危險不是一場革命,而是一場政變。”轉引自托德2018年12月3日接受法國France culture電臺的采訪.
法國“黃馬甲運動”是一場“政變”?
這到底是一個聳人聽聞的說法,還是對歷史的一種真正客觀的描述?法國的“黃馬甲運動”自去年年底爆發以來,迄今為止仍在繼續;這很可能是一場將引導整個法國(甚至可能影響整個歐盟)走向另外一個歷史方向的“革命性”運動。一個歷史的轉折點可能正呈現在我們眼前。
運動的起源
通常情況下,一次群眾示威往往有著明確的目標,一旦達成,示威就會平息。這一次,法國的“黃馬甲運動”的火星是由政府欲加征燃油稅而引發的。
追根尋源,我們可以發現,這場人數盡管不多、但卻有著“全民性”運動性質的抗議從去年五月份就已經初露端倪。當時一位名叫Priscilla Ludosky的駕車者在“臉書”“推特”和“Youtube”上分別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要求免除新加征的0.76歐元的燃油稅。此信在網絡上征集到23萬個簽名支持。到了去年十月份,網絡上出現一幀短視頻,一位名叫雅克琳娜·莫羅(Jacqueline Mouraud)的女子不僅抗議燃油稅價上漲,而且質疑國家收取的這額外的燃油稅到底用到哪里去了!她直接點名要求馬克龍總統對此做出明確回答。莫羅的視頻在網絡上激發了更為強烈的反響,數周之內這一視頻點擊量超過六百萬,而且幾乎是一邊倒地支持她。而在此之前愛麗舍宮恰好傳出“30萬歐元高價換地毯”的“丑聞”;兩相對比,反差太過強烈。由此,強烈不滿的法國社交網絡開始發出“扎克雷起義”扎克雷起義(Jacques Bonhomme)是法國1358年5月爆發的一場底層農民起義反對上層貴族的起義。雖然最后起義被殘酷鎮壓,但在法國歷史上卻留下了農民起義的濃重的一筆.的呼吁。
真正有組織的“黃馬甲運動”最早是2018年11月誕生于法國北部諾曼底地區的海濱城市迪耶普(Dieppe)。當時在網絡上出現了一個“黃馬甲群”,在推特上呼吁在11月17日進行抗議示威。很快這個群就有了16000名參與者。到了17日周六這一天,小城果然爆發了“黃馬甲示威”,幾乎所有圓形交叉路口都被上千名身著“黃馬甲”的抗議人群所堵塞。“黃馬甲”是當汽車在路上出現問題拋錨時必須穿上的一種背心,目的是讓其他汽車司機遠遠地就能看到他。這種以“醒目”為旨的“黃馬甲”便成為這次運動的強烈象征。很快,這一運動就在全國蔓延開來。在后來的幾周周末,全法國共有數十萬人身穿“黃馬甲”上街抗議。關于其人數,法國主流媒體認為滿打滿算約三十來萬。但“黃馬甲運動”的參與者們則指責媒體“大大壓縮了真正的抗議人群數字”。
運動的轉折點是馬克龍總統的電視講話。
在運動爆發四周后,法國總統馬克龍發表電視演講,宣布放棄預定從2019年開始新加征的燃油稅,而且公布對最低工資收入者(SMIC)發放100歐元的額外補貼。在這種背景下,很多中國專家想當然地認為,運動將趨于平息:既然當局已經做出了完全的讓步,運動當然也就沒有理由再繼續下去。然而,這場“黃馬甲運動”不僅沒有熄火,相反卻愈演愈烈,甚至有向整個歐盟蔓延的趨勢。顯然,燃油稅只是一個導火索。那么這場運動的目標究竟何在?
盡管法國媒體刻意地回避相關畫面和報道,但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黃馬甲運動”遠非近年來其他一些經常出現的抗議活動可以相提并論。這場運動顯然是法國歷史上民眾抗議鏈上的新的一環。種種跡象表明,這次“黃馬甲運動”并非對某項政策、某個政府、某位政治家(總統)的有限不滿而引發的,相反是法國積累多年的對整個左右翼執政體制、法國經濟格局和西方民主的根基——“代議制民主”的強烈抵抗的一次總爆發,因而具有明顯的“革命”的性質。
唯一不同的是,這場“革命”的動因似乎是來自極右翼,但卻得到來自極左翼的有力支持。這既是歷史的荒誕,也是歷史開的一個殘酷的“玩笑”。
反對政權、媒體和資本三大權力
我們知道,真正統治著法國和西方民主國家的三大權力,實際上是政權、媒體和隱身幕后的資本(即財團)。資本通過在金錢上對政客的資助和對媒體的控制(法國95%以上的主流媒體,從電視、電臺到紙質媒體都控制在各大財團手中),實際上操縱著民主選舉的結果,進而使國家運行之軌不會脫離資本利益的大方向。而這次的“黃馬甲運動”的本質特征和真正目標,實際上就是挑戰這三大權力。很多參與“黃馬甲運動”的示威者提出的目標和口號,都是在馬克龍總統的公開講話發布、對運動做出了全面讓步的回應之后,逐漸清晰起來的。其中最著名的一句口號也是在這個時刻響遍法國的:“RIC”(référendum d’initiative citoyenne),意指“人民發起的全民公決”。
為什么要公決?而且要“人民發起”?原因非常明了:就是因為參加運動的法國民眾已經徹底失去了對政府和總統的信任,也失去了對包括左右翼各類傳統政黨的信任。“RIC”直接挑戰的,就是服務于資本利益的代議制本身。因為示威者非常清晰地提出,“我們選出的代表(議會議員)投票做出的是反對我們利益的決策”。比如引起這場運動的導火索就是民選出來的政府所做出的違反民眾利益的一個決策:加征燃油稅。所以,參與“黃馬甲運動”的示威者要求當局進行一系列公民投票;對涉及民眾整體利益的決策都要進行公民投票來決定,而投票的議題也要由公民直接提出。因為過去公決的議題都是由政府提出的。一些重大的、幾乎涉及全體法國人民的議題,當有可能被公決否定的話,法國當局是絕對不會付諸全民公投的。一個鮮明的例子就是同性戀婚姻問題。法國當時爆發了數百萬人的大規模抗議示威游行,要求進行全民公決;但當年執政的奧朗德政府充耳不聞,因為他們非常清楚,全民公決只有一個可能性:被否決。所以奧朗德政府堅持只在議會審議;最終議案在議會被通過。今天的法國同性戀者可以結婚已經是法律。這件事對法國人民政治信心的打擊是非常大的。他們選出的代表做出的是違背他們意志的事。又比如當前法國的一個爭議焦點:要不要脫歐。法國在全民公決是否要批準歐盟憲法草案時,高達55%的人投了反對票。可以想象,今天如果法國舉行全民公決以決定法國是否留在歐盟內部的話,很有可能出現類似英國的事件:法國脫歐。對于歐洲的精英階層來說,這將是不可接受的政治大地震。因而,這樣一個重大議題,法國政府是絕不會讓全民來進行自由裁決的。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RIC”的提出,實際上就是一場革命。
一些運動參與者甚至直接提出要將議會普選制部分地改為抽簽制;以抽簽的形式來選出部分代表人民的議員,以避免選舉出來的議員都是政客的結果。因為抽簽這種形式將給予被選中者絕對的做出任何決策的自由,而不需要顧及黨派利益、選舉利益及其自身利益等。這充分反映出法國民主選舉體制本身在這場運動中遭到幾乎是全面質疑的現象。
甚至為了更明確地表達“黃馬甲運動”的宗旨,示威者還模擬“路易十六上斷頭臺”的歷史,做了一個總統的模型來審判(此舉因違法而正在遭到法國司法當局的追究,已有三名示威者因此被逮捕),這是為了傳遞“與當政者決裂”的強烈信息。也就是說,這次“黃馬甲運動”沒有任何妥協的可能性。
除了反對總統、政府和議會之外,法國主流媒體也正在成為未來最新一幕的“黃馬甲運動”所瞄準的靶心:很多抗議者通過網絡、推特和油管(Youtube)而將矛頭對準法國主流媒體,認為法國主流媒體“都是撒謊者”,強烈抗議主流媒體未能正確地報道這場運動。很多抗議者認為,法國主流媒體過多地將關注點集中在運動中出現的暴力現象,而有意忽略了警察對示威者的暴力行為。我們中國記者作為局外人,也發現一些民間新生的網絡媒體——比如極右翼的AlterInfo、極左翼的Le Vent se lève,包括一些外國媒體如俄羅斯在法國播出的“今日俄羅斯”法語頻道等,均在“黃馬甲運動”期間表現出強大的傳播能力。特別是“今日俄羅斯”法語頻道已經連續幾周在周末運動發生日進行了實況直播,吸引了大量法國觀眾觀看。直播中,“今日俄羅斯”不做任何評論,而只是把話筒和鏡頭直接對準示威者,倒是給人相對更為客觀的感覺。
“黃馬甲運動”另外一個引人關注的地方,是示威者不約而同地對法國的金融體制提出強烈批評。在“今日俄羅斯”法語頻道去年12月30日的一次直播中,一位“黃馬甲”直截了當地說:“我們不愿意繼續生活在金融權力的統治之下。”這句話立即傳了開來。種種跡象充分地展示了這場“黃馬甲運動”針對的恰恰就是目前真正統治著法國的三大權力——政權、媒體和資本。這是“黃馬甲運動”的一個本質性特點。理解了這一點,就會明白這場運動的歷史意義。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這場運動與二戰以后發生在法國乃至整個西方的幾乎所有運動都有著本質上的不同;過去的各種斗爭都有著非常具體的目標,是為了達到某個或某些非常具體的目的而進行的;但這次運動是對西方整個統治結構提出了全面質疑。正是因為如此,這場運動并沒有因為法國總統馬克龍做出了大幅讓步之后而中止。應該承認,“好戲”還在后頭。
焦點之一:對金融資本的強烈質疑
這場“黃馬甲運動”是在法國深陷債務危機的背景下爆發的。這一債務危機正在導致法國中產階級進入“日益貧困”的下行階段。這是二戰以來法國國內發生的最為深刻的歷史性變化。
對法國債務危機之產生、緣由和解決方法的認識和看法,已經將法國分為兩派觀點對立的人群;一部分人認為債務產生的原因是因為法國建立了一個負擔過重的“福利社會”,即對“窮人”的各種額外補貼太多,而導致國家入不敷出;因而改革就是要改掉這一部分福利。也就是說,法國的改革就是要拿窮人開刀。而對于富人則完全是另外一個方案:為了吸引資本前來法國投資,馬克龍總統治下的改革的另外一面,就是要對富人減稅。用“黃馬甲運動”中很多參與者的話來說,這就是一種“劫貧濟富”。
但另一部分法國人——既包括目前參加這場運動的大多數“黃馬甲”們,也包括法國社會“沉默的大多數”——則認為,法國債務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1973年1月3日通過的《銀行法》,是這項被稱為“蓬皮杜羅斯柴爾德銀行法”的法律,對法國中央銀行進行了私有化,使法國中央銀行失去了貨幣發行權,最終導致今天的法國債臺高筑。因此,“黃馬甲運動”的目標直指金融權力。在“黃馬甲”們的眼里,馬克龍的所謂改革,是與底層勞動階級為敵的。
有關法國貨幣發行權已經從國家手里被轉移至私人金融財團的觀點已經出現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特別是在幾本書的出版之后。其中最著名的一本就是經濟與金融學者彼埃爾伊夫·魯杰容(Pierre-Yves Rougeyron)的暢銷書《對1973年1月3日法律的調查》。《LEnquête sur la loi du 3 janvier 1973》由法國Le Jardin des Livres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在這本書中,伊夫·魯杰容試圖證明,法國今天背負的沉重的金融債務,根源就是這條法律。他認為,在這條法律頒布之前,法國中央銀行隸屬于國家,當國家從中央銀行融資時,是不需要支付任何利息的。而在這條法律頒布之后,法國中央銀行的性質就變了。法律規定,國家不再能夠直接從法國中央銀行進行融資,而必須通過向私人銀行借債,并支付4%的利息;再由私人銀行從中央銀行無息借錢。這樣一來,國家便不得不支付給私人銀行4%的利息。而私人銀行則僅僅是將錢轉了一次手。我們千萬不能小覷這4%的利息!事實上正是因為支付了這4%的利息,法國財政預算開始從盈余走向虧損。在通過這項法律之前,法國財政預算還是有盈余的。通過該法后,法國支出開始上漲。1978年至今,法國政府就沒有任何一年的財政預算是盈余的了。而支付這4%的銀行利息,今天已經成為每年法國國家財政預算中最大的一筆開支,超過了高等教育和國防的預算。
之后,隨著歐盟建設的進程,這則《銀行法》后來通過《馬斯特里赫特條約》《里斯本條約》等歐盟建設條約而轉換成歐元體系。但這并沒有改變法國收支從此不再平衡的現象。今天法國的債務已經達到天文數字的22998萬億歐元(法國國家統計局Insee2018年第二季度公布的數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99%。
當然,反對者認為法國債務的根源就是過度的“福利社會”所致。然而令人倍感蹊蹺的是,這筆債務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在法國主流媒體上幾乎是不讓討論的。因此,債務是源于“過度福利”還是源于“銀行法”,在法國形成了兩大觀點潮流;而且始終處于分化、分裂和變化之中。于是,法國債務危機的原因和解決方法,便成為這次“黃馬甲運動”的一個焦點。我們看到,在運動中不斷地有人提出這個問題。每次有“黃馬甲運動”的參與者穿著黃馬甲出現在電視臺屏幕上時,他們幾乎都會提及這個問題;但在法國主流媒體上也幾乎每次都會被電視臺主持人或記者有意識地將話題轉移開去。而在非主流媒體、特別是在這次運動中突然走紅的一些非主流媒體和網絡媒體上,這個問題卻是這次運動的兩大焦點之一。“銀行法”和國家貨幣發行主權問題在這些媒體上、在追蹤觀看這些媒體的法國民眾頭腦里,則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焦點之二:反對全球化
從目前已知或相對比較一致的領域,我們可以認為,“黃馬甲運動”瞄準的另一大焦點是:“全球化”。正是這一大焦點,將法國社會分裂成兩大部分。但這兩大部分不是以傳統的階級成分來劃分的,而是以對這一大焦點的立場來劃分的。
法國有一大特點,就是社會階層涇渭分明,甚至連居住地都有著明確的界線。
法國的上層大資產階級、bobo(小資產階級)和受雇于他們的部分底層階級,主要生活在巴黎及其周邊三十公里左右。他們有一個共同特征,就是他們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法國上層最具代表性的階層主要是金融、房產和跨國大公司等巨頭的擁有者。他們早已突破法國國界而走向全球。甚至包括巴黎的房地產,其最奢華的豪宅已經瞄準國際客戶,因為法國本土已很少有人能買得起了。而居住在巴黎周邊的則主要是為這批巴黎的上層服務的一批人群。正是由于他們與巴黎上層的密切的經濟關系,所以他們盡管從階級劃分上應該歸為中產階層,但由于他們的生活方式追隨上層模式,因而他們的政治特征同樣是支持“全球化”。
而這次參與“黃馬甲運動”的主要成員,則是散布在法國巴黎之外廣大地區的白人中產階級和底層無產階級。他們占到法國總人口的一半以上。他們主要靠打工生活。納稅和交通是他們生活中的重要支出。他們過去的政治面目非常復雜,既有支持法國共產黨、法國社會黨的傳統左翼選民,亦有支持薩科齊等的傳統右翼選民;甚至包括支持國民陣線的極右翼選民和支持另一位著名政治家讓呂克·梅朗松(Jean-Luc Mélanchon)及其領導的“法蘭西不屈服黨”的極左翼選民。但今天可以用一個共同的政治立場將他們統一起來,那就是“反對全球化”。
所有的統計數字都證明,法國中下層的日常收入正在明顯地、史無前例地、迅速地下降。而這種下降在法國被普遍認為是與“全球化”密切相關的: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價格競爭、產品競爭、服務競爭等正在摧垮法國的就業。而所謂針對“地球變暖”的種種措施更是與“全球化”緊密相連。法國本以為可以通過“巴黎氣候協議”贏得碳關稅的好處,沒想到的是最后自己也不得不采取一定的措施來回應自己提出的問題。結果,當生活在巴黎的上層統治階層決定要將燃油稅上調時,立即導致法國50%以上的民眾頓感切膚之痛:汽車和燃油是生活在巴黎以外的法國民眾的支柱。“黃馬甲運動”中最醒目的口號之一是:“馬克龍關心地球末日,我們關心每月的月末日”。
所以,這是一場所謂的在“全球化”競爭中的“受害者”聯合起來的“反全球化”力量掀起的針對“支持全球化”力量的斗爭;就這個意義而言,這是法國歷史上的第一場右翼革命,一場得到同樣“反對全球化”的最左翼民眾的支持的右翼革命。
說這是一場右翼革命,最根本的一點,是“全球化”使西方統治階層內部的三大權力之一的“資本”正在發生利益分化,過去曾經共同在“全球化”中獲利的西方產業資本,與跨國的金融資本開始出現利益對立的局面。
聯系最近的“貿易戰”,我們以美國為例來說明這個情況。
要理解美國產業資本和金融跨國資本的利益是如何分道揚鑣的,我們不僅要認識全球化,同時也要認識全球化的各個不同的階段、全球化對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在不同階段帶來的不同結果;特別需要認識和理解的是從美國國家的角度來看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之間存在著的本質差異。
以軍工聯合體為代表的產業資本基本上以美國國家為主要載體,兩者的強盛或衰落密切相連。盡管產業資本也曾通過全球化而牟取暴利,但隨著全球化進程中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出現和崛起,特別是因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使中國產業從低端開始朝著中、高端發展時,美國產業資本遭到來自中國的強有力的競爭而節節敗退;但他們卻不會閉門反思,相反怪罪于中國和“全球化”。
而以金融資本為首的跨國財團的主要特征則是“跨國”。所謂“跨國”,主要是指國際金融財團通過相互參股、聯姻、建立各類基金會,特別是在金融投機機會來臨時的共同合作買賣、做空做多,使得他們之間的利益已經完全融為一體,形成一股強大的、遠遠超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金融投機資本。索羅斯及其背后的力量就是最典型的代表。金融資本的“跨國”性質,已經使美國國家利益與金融跨國資本自身的利益不再完全吻合。其中最突出之處,就是當美國國家與產業資本因“全球化”而面臨困境時,跨國金融資本卻依然從“全球化”中獲利。因此,在理解美國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之間的關系時,一定要看清,前者與美國息息相關,而后者則早已超越美國,成為一個高踞世界各國包括美國在內的一個龐大的、無形的跨國利益集團。
于是,跨國金融資本繼續支持“全球化”,而產業資本則開始在同樣因“全球化”而失去工作或面臨失業危機的中下層勞動民眾的支持下,開始反對“全球化”。在美國,出現了“特朗普現象”;而在法國則出現了“黃馬甲運動”。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場運動是對1968年“五月風暴”的一次“逆轉”:1968年5月正是法國經濟迅猛發展的上升階段,爆發了左翼民眾要求掙脫工作的束縛,爭取更多自由、更多民主的左翼革命;而這一次則是在經濟急劇衰退中的一場反對進一步開放、反對進一步自由化、要求更多就業、工作和保障的右翼革命。
“黃馬甲運動”正在逼迫我們回答一個問題:歷史正在開“倒車”嗎?還是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有一點是必須指出的,即這場運動并沒有提出一個新的政治模式,用來取代舊模式。更簡單一點說,這場運動僅僅是“破”,而非“立”;更不是對世界上其他統治模式包括中國模式的肯定或贊同。應該特別強調指出的是,西方民眾對中國政治模式的認知是非常膚淺、負面和片面的,因為在他們主流媒體的控制下,中國的現實情況被完全扭曲;中國取得的任何成功都被有意識地忽略掉了。所以中國是不可能成為“黃馬甲運動”的標桿性國家的。但這并非是中國做得不好,而是“中國故事”沒有傳播出去。
“黃馬甲運動”:國際民粹浪潮中的一個巨浪
法國這場得到左翼民眾支持的“右翼革命”與整個西方爆發的反對“全球化”的“民粹主義”浪潮是完全相吻合的。
事實上,在美國選出一位反對“全球化”的特殊總統特朗普時,法國選民也拋棄了傳統左右翼總統候選人,將“不左不右”的馬克龍和極右翼的瑪麗娜·勒龐推進了大選的第二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勒龐本應扮演“法國特朗普”的角色。但法國的傳統主流政治力量(即特朗普口中的establishment——“權勢集團”)比美國更強大,在極右翼的勒龐進入第二輪之后,“反勒龐”便成為一種道義上的“責任”;于是在出現空前棄權、白票和無效票比例(高達25.44%)的情況下,極右翼的勒龐被擊敗,“不左不右”的馬克龍當選。但這一意義非凡的“第二輪”埋下了法國廣大選民在政治上的極端不滿情緒,現在集中在“黃馬甲運動”中爆發出來。
馬克龍上臺后并沒有順從民意在隨后整整一年多的執政中向民眾“讓步”,即為底層勞動力和正在衰退中的中產階級提供更多的“好處”。相反,他在國內實際上繼續推行其多位前任已經失敗了的所謂“變革”(基本上屬于“劫貧濟富”范疇),而在國際上則明確擔任起跨國金融資本的臺前發言人角色。馬克龍是歐盟國家中最明確批評特朗普的“美國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國家領導人。這樣,馬克龍總統便成為國際民粹主義浪潮所瞄準的一個首要目標。
從美國特朗普當選,到英國公投脫歐,從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吹起的這股民粹主義浪潮,早已與法國內部政治朝著極右翼方向演變匯為一體。事實上,特朗普的前顧問史蒂夫·班農已經多次前來法國,與法國極右翼國民陣線的總統候選人瑪麗娜·勒龐有了深入的接觸。早在今年三月份,班農在接受法國《當代價值(Valeurs Actuelles)》雜志采訪時就已經預言:“馬克龍竭盡全力遏制民粹主義浪潮,這將是人們唯一記住的。但他不可能遏制住這股浪潮。馬克龍時代的消失正在大步向我們走來。”
今天發生的這場直接要求“馬克龍下臺”的“黃馬甲運動”是不是這股民粹主義浪潮的一個高峰?班農之流是不是這場運動背后的“黑手”?我們目前尚沒有確鑿的證據。但歷史會將它所知的秘密慢慢告訴我們。
西方政治色譜的歷史性演變
在“黃馬甲運動”中,我們看到法國社會除了左右翼兩大政治流派之外,正在出現越來越多的其他政治組織、黨派和政治思潮。這些政治組織、黨派和思潮正在獲得西方民眾越來越強烈、越來越公開的支持。我們也越來越清晰地看到,這些政治組織、黨派和政治思潮都大大突破了西方傳統左右翼的劃分,而通過另外一些標準而整合到一起。
過去西方的政治色譜是一道橫線:極左—左—中間派—右—極右,一字排開。但今天我們卻發現,法國社會政治色譜正在形成一個光環:中間派在上方、左右翼分列兩邊,而下面卻出現了極右翼選民與極左翼選民正在聯手的情況。比如法國的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即前國民陣線)和極左翼政黨“不屈服黨”的基礎選民都是處于社會最底層的勞動階級,他們卻在“黃馬甲運動”中聯手反對傳統的左右翼。如果我們細究他們的共同點的話,我們就會發現,他們在政治理念上南轅北轍,但在一個共同的目標下聯合成統一戰線:“反全球化”。用傳統的左右翼劃界已經無法劃分的階級,在“支持還是反對全球化”問題上,又重新劃分成陣線分明的兩大陣營。所以,我認為今天的世界已經不再適用于傳統的政治學概念,而應該以“全球化”為核心,重新劃分政治勢力。這樣我們就能清晰地看到,西方世界分裂成支持“全球化”和反對“全球化”的兩大政治力量;這兩大政治力量打破了傳統的左右翼陣營,目前正由反對“全球化”的產業資本聯合同樣反對“全球化”的底層勞動階層,與繼續支持“全球化”的跨國金融資本形成尖銳對立;由于金融資本已經完成了其國際化進程,形成了一個跨國的金融資本集團,因而,這場爭斗也就擴展到了全世界。
從這個角度出發觀察今天的世界,我們可以發現,以特朗普為首的美國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這兩大對立的力量板塊已經完全成形;而他們之間的沖突,也正在日益趨于激烈。
全球化從“幸福”走向“痛苦”
要了解今天西方世界的政治動向,必須首先認識“全球化”的三個階段對西方社會特別是對統治著西方的三大權力之一——資本(財團)形成的巨大沖擊,并最終造成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利益的分裂和對立。世界貿易組織前總干事帕斯卡爾·拉米(Pascal Lamy)在他的一部《世界往何處去?》(Où va le Monde?)的書中曾將全球化從1985年伊始分為“幸福的全球化”、到2001年開始“痛苦的全球化”以及從近幾年最終進入“危機和束手無策的全球化”三個階段。從他的分段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全球化是如何在從“幸福的全球化”走向“痛苦的”甚至是“危機和束手無策”的過程中,將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利益一刀切開,從而形成當今世界格局中產業資本和金融跨國資本分化成兩大對立的力量板塊的。
從1985年開始的“幸福的全球化”階段,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都從全球化中獲利:市場越來越大、勞動力價格越來越低廉、財富迅速積累、貧困現象日漸壓縮、以計算機為核心的技術革命正在爆發、中國轉向市場經濟、網絡使全球化進一步加速發展。
只有擁抱全球化的國家,才能出現經濟奇跡。
當時世界上出現三大趨熱:一是無限繁榮;二是西方“民主”邁向全球;三是由聯合國和美國保證下的全球安全。“市場萬能”的說法就是在這個階段風靡全球的。遺憾的是,如今相當一部分中國學者的思維,始終停留在這個階段。
此時美國的產業資本與跨國的金融資本曾經攜手賺錢。然而很快全球化開始從“幸福”轉向“痛苦”。從我在法國任常駐記者觀察到的現象看,始于2001年的“痛苦的全球化”,主要是指西方廣大的中產階級和底層勞動階層——再具體來說,就是以出賣勞動力來換取工資的階層——從全球化中收獲的已經不再是利潤而是痛苦。與此同時,產業資本也在同來自新興國家的激烈競爭中敗下陣來,也開始失去利潤而僅剩“痛苦”。
我們知道,產業資本的贏利方式主要是通過產品,而金融資本則主要是債務。產品需要勞動力來生產;全球化雖然能夠使產品突破國界,但生產產品的勞動者卻始終是有國界的。
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所出賣的勞動力價格,卻比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要貴得多;再加上匯率的因素,兩者之間的差距足以使發達國家的勞動階層生產的產品賣不出去了,企業于是便將生產從發達國家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勞動階層,因為發展中國家的勞動階層的勞動力價格比他們低,而失去了工作。
從產業鏈的角度而言,近年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之間發生的摩擦,事實上造成了各國工人階層之間的矛盾。因此,當特朗普高呼產業制造回歸美國時,他獲得的正是美國勞動階層的歡呼;而特朗普向包括中國在內的“順差國”發動貿易戰的時候,獲得的也同樣是不明真相的美國勞動階層的歡呼。
特朗普的當選,與過去美國共和、民主兩黨之爭有著相當大的不同。不同就不同在特朗普明確的代表著所謂全球化的“受害者”——產業資本以及中產階級和勞動階層的利益。這就打破了以往“左”“右”之分的局面。國際關系與國內矛盾有著本質上的不同。我們不能機械地來理解社會階級構成和國家關系的演變。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產業資本、國際金融資本、工人階級的矛盾已經變得很復雜,遠不是全球化之前那么簡單。
美國選民中的中下層白人勞動階層普遍支持特朗普的奇特現象,就是一個例證。事實上,他們支持的不是特朗普,而是特朗普的“反全球化”。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勞動階層是有國界的,事實上產業資本也是有國界的。一件商品如果是在美國生產的話,意味著美國企業將重新獲得利潤而勞動階層將重新找到工作。因此,對于美國產業資本和勞動階層,以及部分中產階級來說,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和“制造業回歸美國”是有利的,是對全球化的“逆轉”。
西方內部的這兩大力量板塊不僅僅存在著利益沖突,而且他們對世界未來的走向與構成,也同樣存在著非常尖銳的對立。而中國作為世界上新崛起的一股力量,與西方這兩大力量板塊顯然也都有著明顯的利益沖突。這樣就形成了三方錯綜復雜的利益交錯、斗爭交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這是我們需要深入研究的一個重大戰略性課題。
一場意義非凡的“信息革命”
眾所周知,這次“黃馬甲運動”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沒有明確的領導者。確實,“法蘭西不屈服”黨領袖梅朗松、議員弗朗索瓦·魯凡(Franois Ruffin)等先后被認為是運動的“指導者”;特別是魯凡,在運動開始時非常活躍,是少數議會議員中公開支持“黃馬甲運動”的政治家。只是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事實證明他們不是“黃馬甲運動”的“領導者”,而只是參與者、追隨者。
令人倍感興趣的是,在這場運動中出現的幾位或被法國主流媒體有意屏蔽、或被有意忽略的學者,他們對法國社會、對“黃馬甲運動”所發表的種種講話、文章和觀點,事實上對運動起到了某種深刻的引導作用。而大量報道他們的一些新出現的媒體特別是網絡媒體,則正在以迅猛的勢頭搶走過去傳統的西方主流媒體的觀眾和讀者,正在構成“黃馬甲運動”出現以來的一場新的“信息革命”——非計算機信息,而是新聞意義上的信息——即人們不再相信傳統西方主流媒體上的信息,轉而相信新網絡媒體傳播的信息。
在輿論簇擁下而成為不是代言人的“代言人”,首推埃蒂安·舒阿爾(tienne Chouard)。舒阿爾是巴黎南特大學老師,主流媒體介紹他時總是提及其“左翼激進立場”。舒阿爾成名于2005年歐洲憲法草案公投。反對該草案的舒阿爾發在自己博客上的一篇文章,被主流媒體廣泛引用,最終使歐洲憲法草案公投失敗。在這次“黃馬甲運動”一開始,舒阿爾便受到非主流媒體的追逐采訪。正是他提出了“RIC”——公民自主公決的主張。這已經成為“黃馬甲運動”的一個最具體的政治目標。他對代議制民主一直持否定態度,而主張進行“抽簽民主”;他甚至公開否認法國是“民主”體制;他對法國失去貨幣主導權的批評也是眾所周知的。他的幾乎所有觀點都受到“黃馬甲運動”參與者的高度重視;他從這場運動一開始,就起到了某種“精神領袖”的作用,這是不可否認的一個事實。他最近頻繁出現在各大電視臺,對運動的性質、緣由、未來發展方向等做了大量分析。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似乎在“局外”指導著這場運動。
可以說,埃蒂安·舒阿爾不久前在法國還是一個普通大學老師;但隨著“黃馬甲運動”的深入,舒阿爾必將成為法國當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從某種程度上而言是一位“精神領袖”。
對運動指導性作用同樣非常明顯的,還有另外兩位知識分子,一位是前面提及的經濟學家托德,另一位則是被指為“極右翼”的知識分子阿蘭·索哈爾(Alain Soral)。托德在運動爆發后也幾乎每天都會發表各類評論。這位早在1995年就指出“法國社會處于分裂狀態”的經濟學家曾深刻影響了右翼總統希拉克,“社會分裂”的口號是希拉克能夠當選的一個決定性因素。今天,托德認為,“黃馬甲運動”對法國政治的挑戰是空前的,如果當局不能理解這種挑戰的嚴重性的話,這場運動在他看來甚至有可能成為一場“扎克雷起義”。而索哈爾這位被西方主流媒體描述為“反猶”的政論家也在運動開始后便在他主辦的一個網站“平等與和解”上天天發表對運動的看法和分析。盡管法國主流媒體對索哈爾大力封鎖,但他的影響卻與日俱增。他對金融資本的猛烈抨擊贏得了法國輿論的廣泛共鳴。他的一本《理解帝國》的政論書已經暢銷多年。在示威隊伍中也有相當一部分打出他的旗號。
此外,一些原來影響并不大的網站,在運動中也異軍突起,成為運動的信息傳播者。其影響與日俱增,令人有一種“信息傳播”在法國正面臨著一場深刻的革命的印象。
比如一個建于2017年的名為“起風了”(Le vent se lève)的網站在這次運動中影響大幅增加。網站年輕記者Marion Beauvalet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揭露法國主流媒體是如何抹黑“黃馬甲運動”的,在法國民眾中獲得大量反響。另外一個直接叫做“媒體”(Le Média)的視頻網站也播出了大量法國主流媒體刻意回避的話題討論內容。在“黃馬甲運動”進入高潮前夕,該視頻網站在其欄目“真正的政治”中組織了一場名為“金融資本真的奪走了權力?”的辯論,吸引了大量觀眾。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似乎為“黃馬甲運動”在做輿論準備。
必須提出的另外一個非同一般的媒體,是“今日俄羅斯”法語頻道(RT France)。“今日俄羅斯”雖然是一個外國電視臺,但在報道“黃馬甲運動”中卻起到了類似甚至勝于法國主流媒體的應有作用。“今日俄羅斯”非常聰明地聘用了很多因政治理念不同而被法國媒體排斥的法國名記者,并給他們充分的自由來主持節目,結果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效果。其中有一位原來在法國三臺主持一檔非常受歡迎的節目的記者弗雷德利克·塔德伊(Frédéric Tadde)在“今日俄羅斯”創辦了一檔對話節目《禁止“禁止”》,意為沒有任何話題不能涉及。塔德伊在接受法國記者采訪時說,這是第一次一家電視臺給他“完全的自由”來主持一檔政論節目。這檔節目在“黃馬甲運動”中采訪了很多平時難以在法國主流電視臺看到的專家、學者和運動的參與者,受到法國民眾的大力歡迎。“今日俄羅斯”法語頻道對這場運動的影響,將是未來法國媒體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筆。
未來走向:一個碩大的問號
“黃馬甲運動”還在繼續。盡管法國媒體已經開始“忽略”這場運動。然而事實上法國反對全球化的力量正在動員第32周的“黃馬甲運動”。
由此我們可以非常明確地做出以下幾個判斷:
第一,“黃馬甲運動”不是一個簡單的抗議行為,而是帶有深層次政治目標的群體性運動,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具有某種“革命”的性質;
第二,“黃馬甲運動”與法國近年來的其他抗議示威有著一個根本性的不同之處,即在于其目標的不可妥協性;這一目標用直白的話語來形容,就是要推翻法國現政府、推翻法國現行政治體制;
第三,“黃馬甲運動”必然會遭到法國當局的鎮壓;但在未來幾個月甚至幾年里,“黃馬甲運動”將會不斷地卷土重來;因為這是法國相當一部分中下層民眾面臨自己生活困境時不得不采取和參與的一場運動,是一場具有長期性的運動;
第四,“黃馬甲運動”將會造就一批法國新的思想者,包括舒阿爾、托德、索哈爾等;他們盡管被主流學術界所排斥,但他們對社會的影響將會與日俱增;
第五,“黃馬甲運動”將很難成功;因為西方社會的財權、政權和輿論權都被牢牢地控制在資本、政府和媒體手中;在“黃馬甲運動”面前,事實已經證明這三大權力正在相互聯手,以期維持其統治。兩者相比,力量懸殊;如果沒有外來勢力的支持,“黃馬甲運動”將注定走向失敗。但經過“黃馬甲運動”洗禮的法國和西方,將走向真正意義上的全面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