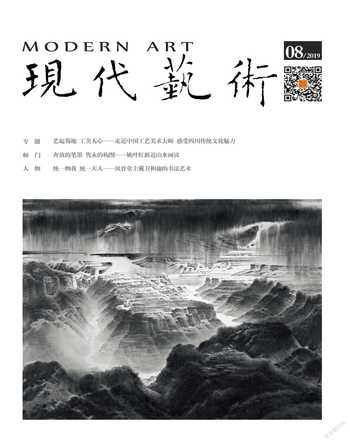矛盾分析法論《清明上河圖》創(chuàng)作背景及當今中國畫發(fā)展
熊小添
《清明上河圖》不僅反應了宋徽宗畫院的水平,同時也為后人研究北宋末年汴京提供了依據(jù),具有高度的歷史文獻價值,且為古代現(xiàn)實主義藝術的典范。該畫作者張擇端生活在北宋末期,作品根據(jù)京城繁華的集市貿(mào)易與街景寫生而創(chuàng)作,滿足了徽宗所提出的“形似”“格法”的標準。
中國畫,可以與世界各國的文明、繪畫并存,卻是獨立且獨一無二的存在。說到它的獨立,首先是其視角不與世界上任何一個畫科相同,而另一方面,古人對線條的執(zhí)著追求,對墨色的運用以及對意境的把握,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早在東晉,畫家謝赫曾對繪畫提出了六個法則,要求我們掌握“骨法用筆”“氣韻生動”等,對線條偏執(zhí),對氣、韻、筆、墨的強調便十分明顯。從最初出現(xiàn)在彩陶上的簡單的線條,到出土的漢朝磚畫與帛畫,再到較為成熟的人物畫,以及再后來山水畫的獨立,與兩宋時期文人畫的興起,使得山水畫成為研究中國文化歷史的一條軌跡。這是一個相當漫長且復雜的蛻變,這個過程用“道阻且長”來形容一點都不夸張。
在十世紀中葉后,宋代統(tǒng)一全國,延續(xù)了五代后蜀的畫院模式,發(fā)展出了規(guī)模龐大的翰林畫院。這種模式持續(xù)了9個世紀,對當時的繪畫藝術發(fā)展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歷代帝王對繪畫極高的興趣,尤其北宋皇帝趙佶,不僅酷愛集畫、作畫,亦廣納書畫之賢才,將院體畫的發(fā)展拉向了高潮。
兩宋時期的人物畫、風俗畫、山水畫、花鳥畫均有里程碑式的成就。馬克思方法論學說中提到,矛盾分析法之所以是認識事物的根本方法,這是由對立統(tǒng)一規(guī)律在客觀世界中的地位以及在辯證法體系中的地位所決定的。矛盾分析方法是“兩點論”與“重點論”相結合的方法。“兩點論”是一種辯證的思維方法。在研究復雜事物矛盾發(fā)展過程中,既要研究主要矛盾,又要研究次要矛盾,既要研究矛盾的主要方面,又要研究矛盾的次要方面,二者不可偏廢。兩宋繪畫發(fā)展的高潮,促進其發(fā)展的主要矛盾是現(xiàn)實因素,包括政治上對繪畫文化的大力推崇、一國之主對繪畫的喜愛等;而次要矛盾是社會現(xiàn)實,包括經(jīng)濟的不斷衰落,北方蠻族侵略導致社會的動蕩不安,使得畫家借助繪畫來聊以自娛,體現(xiàn)繪畫的功能性,達到自我安慰的目的。
以北宋末年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為例,從這幅畫的背后,可以看到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的對立統(tǒng)一、滲透與轉化,在矛盾群中體現(xiàn)了二者的差異、排斥、甚至對立等復雜關系。
中國畫在宋朝可謂是一個發(fā)展的高峰:其主要矛盾是在社會文化背景下,文人畫運動強調了獨立個人的體現(xiàn);其次要矛盾是在宗教背景下,佛教禪宗的影響可謂頗多,也發(fā)展出別具特色的“禪畫”。
在主要矛盾中,從政治的角度看來,皇家對藝術文化頗為重視,花鳥畫也隨之進入歷史中最盛時代。而山水畫也在經(jīng)歷了唐代色彩的興盛與衰敗后,進入了筆墨的黃金時代。在三百余年南北文化發(fā)展中,從文人士大夫、宮廷畫家、明間藝匠以及方外的僧道,共同來表現(xiàn)他們對生活的細心觀察與創(chuàng)作。在這樣“群山競秀,萬壑爭流”的時代背景下,院體畫中的《清明上河圖》不失為中國北宋時期的風俗畫中的代表。
《清明上河圖》不僅反應了宋徽宗畫院的水平,同時也為后人研究北宋末年汴京提供了依據(jù),具有高度的歷史文獻價值,且為古代現(xiàn)實主義藝術的典范。該畫作者張擇端生活在北宋末期,作品根據(jù)京城繁華的集市貿(mào)易與街景寫生而創(chuàng)作,滿足了徽宗所提出的“形似”“格法”的標準。
該畫長525厘米,高25.5厘米,描繪了清明時分京城內外的生活場景以及社會狀態(tài)。畫卷分為三個大段落:開篇是以郊外靜謐的農(nóng)村風光,用三三兩兩的商隊將我們的視線移入城內;中段是以虹橋為中心的卞河以及兩岸的船車運輸以及各種商貿(mào)活動,將整幅畫推向了一個高潮;后段為城門內外,街道縱橫,店鋪櫛比,車水馬龍的繁華景象。它像電影一樣,非常詳盡地記錄了宋朝京城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連每一家商店所賣商品的不同,都可以分辨出來。
整幅畫中共五百五十余人,形態(tài)體貌各不相同,體現(xiàn)出畫家對生活仔細的觀察和精準的刻畫,其對人物、山水、花鳥、騾馬、建筑界畫等亦無不精通,所以到了下筆之時亦展現(xiàn)出其胸有成竹之勢。畫家在創(chuàng)作中用心經(jīng)營,采用中國傳統(tǒng)繪畫的散點透視,整幅長卷中充滿了戲劇性的情節(jié)和引人入勝的細節(jié)描寫,也在畫面布局上頗有考究。
把船通過虹橋的緊張場面安排在全卷近乎中央部分,形成具有藝術效果的最精彩的部分:橋下與湍急的河流搏斗的船工們試圖安全地過橋,有的撐蒿,有的掌舵,有的放下桅桿,有的投擲纜繩,有的呼喊著指揮著,場面十分緊張。與此同時,在路狹人密的橋上,騎馬坐轎的宦官迎面而來,互不相讓地吆喝爭道,還有橋頭負重受驚的驢子等等。工人的艱苦奮斗與官宦權貴之人的無所事事在畫中央也激起了層層波瀾。種種矛盾,畫面的拉扯感,給予人無限的遐想。
雖在北宋以及宋以后對人文畫的追求與偏愛,進而將院畫喻為“匠氣十足”的工匠畫。但從此畫中可深切地感受到畫家對“高雅人士”并不重視的“市井細民”的生活,懷有相當深厚的情感和極為深廣而精道的了解。這不僅僅是畫家對生活的熱愛,從精心的布局到對人與物的刻畫,無不彰顯畫家對美的追求。
而其次要矛盾,亦是北宋王朝沒落的主要原因,便是皇室的昏庸無能。宋朝的第八個皇帝徽宗更是對內貪暴,任用包括蔡京在內的“六賊”,為一己私樂竭力搜刮民間財產(chǎn),人民民不聊生,畫院卻依然為了迎合皇帝的樂趣,將京城的繁華譜寫出來,即安慰了皇帝亦安慰了畫家本人。
現(xiàn)藏于遼寧省博物館的《瑞鶴圖》亦是在這樣的矛盾下產(chǎn)生出的“杰作”。北宋政和二年,汴京上空忽然祥云涌動低映端門,成群的野鶴忽然飛鳴于宮殿上空久久盤旋,當時徽宗治理國家已經(jīng)十分疲乏,加上連年邊塞金兵的進攻,使得宋朝的基業(yè)在其手中搖搖欲墜。這一奇景使得徽宗認為這是祥瑞之兆,興奮不已,于是欣然命筆,將這預示著國家興盛的場景紀錄下來。拋開這幅名作的藝術價值不談,其在當時充當?shù)淖饔帽闶恰皩捨俊弊约海瑫r“寬慰”百姓。
但“祥瑞之兆”卻難以挽回衰敗的國運,此后第十五年,即在靖康二年,金兵攻陷都城汴梁,宋朝軍民紛紛起來抗擊金兵,金人自知無力吞下這個腐朽然而卻十分龐大的帝國,遂盡掠九十二府庫160余年所積藏的金銀財寶、書畫珍玩等,連同徽、欽二帝及皇族、臣僚三千余人席卷北去。北宋王朝走到了盡頭。
時下,中國畫的發(fā)展仍然面臨了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但與兩宋時期卻恰恰相反。
主要矛盾,亦是矛盾的重點,表現(xiàn)在當今中國社會經(jīng)濟的快速發(fā)展所導致的文化相對滯后,嚴重阻礙了中國畫對傳統(tǒng)的繼承以及創(chuàng)新。在中國美術的歷史中,美一直與中國文化息息相關,而現(xiàn)下我們正缺乏的就是宋朝從皇帝到黎民百姓對生活品味質量的追求、對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以及對美的信仰。宋代從皇帝本人的參與到文人士大夫的引導,從宮廷院畫家到民間畫家的競爭,調動起所有藝術創(chuàng)作力量,滿足人們日益提高的精神需求。當今時代,人們沉浸于對物質和金錢的追求,“快餐文化”“庸俗文化”大行其道,書畫美學的發(fā)展氛圍不濃、土壤不厚。
而次要矛盾表現(xiàn)在,與明朝的“文藝復興”不同,現(xiàn)在各個地方的中國畫協(xié)會中,不少“大師”并沒有學習過傳統(tǒng)的技法以及中國畫的思想,缺乏中國畫中浸透的幾千年來文人的精神,不繼承、不創(chuàng)新、不務實,憑借著國泰民安、經(jīng)濟昌盛喊著藝術的口號謀權謀利。這種做法連走火入魔都算不上,走火入魔至少是在功夫練到家時臨門一腳踢錯了方向,而現(xiàn)下各種協(xié)會亂象頻出,打著復古的旗號洋洋自得,作品價值與社會地位結合,藝術市場受官員喜好左右,這樣的風氣勢必會阻礙到當今中國畫的發(fā)展。另外,大多數(shù)充滿人文情懷的忠于傳統(tǒng)的當代畫家卻固步自封,不愿與現(xiàn)實同流合污,潛心研習,僅僅與自己所深交的同道中人溝通,不走到未知的領域去與其他人交換意見,無法在這樣紛亂的藝術“品味”的環(huán)境下為這個時代的中國畫審美提供明確的指向。
因此,人們的審美受到了限制,模糊了美與丑、善與惡的概念。古代繪畫的功能乃是“成教化,助人倫”,當今繪畫也迫切需要發(fā)揮出其應有的功能,故加強我們美育教育力度是刻不容緩的。正如蔣勛在《中國美術史》中寫道“傳統(tǒng)文化是活著的文化,不但活著,而且不能只活在學者專家身上,必須活在眾人百姓之中”, 只有這個種群的人對美的認識達到一定的高度,對自己的文化了解、熱愛、以及弘揚,才能是個真正的中國人,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中國人的精神。我們現(xiàn)下的生活已經(jīng)如《清明上河圖》般的喧鬧,卻又有幾人能夠用善于發(fā)現(xiàn)美的眼睛去體會我們生活中的美好,又有幾人能將爾等美景付之于紙筆,又有幾人能如同張擇端一樣花費畢生的精力去描繪這樣的繁華?“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現(xiàn)下我們缺乏的不是美,而是對美的認識。
而這種對美的認識,不僅僅是強調中國畫,更想強調的是在矛盾分析法下的主要矛盾使得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我們產(chǎn)生的距離感。城市中的大多數(shù)人,在信息高速變化的時代,已經(jīng)模糊了當年在教室里讀“心遠地自偏”時的感悟,更不要說去體會自然中點滴細微的變化了。另一方面也可喜地看到,越來越多的人文情懷逐漸被發(fā)掘,并且影響到社會的各行各業(yè),服飾、家具開始流行復古,中小學教育將書法、四書五經(jīng)、中國畫寫進了教學大綱,向城市蜂涌的人潮漸漸消退,甚至有城市中的人放棄優(yōu)渥的環(huán)境,隱居山林。我記得在高居翰的書中描述范寬的《溪山行旅圖》“未經(jīng)觸及的大自然”,這話讓我感觸頗多。中國畫中不僅僅有山川的雄偉壯麗、自然浩蕩,亦有那樸實的“未知”等待我們去發(fā)覺,“未知”是對世界的探索,也是對自己的深究。而我們身邊那一面墻,一方青磚,抑或一寸不起眼的犄角旮旯說不定亦有山水等待我們去游歷。這些山水其實并不是城市中的山水,中國畫亦不是文人的獨享,而是在塵市中對時光韶華的緬懷,對世界紛擾的敬畏,對自己理想的寄托,以及對自己心目中最為寧靜祥和的凈土的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