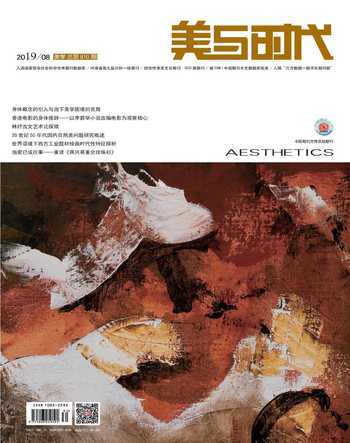20世紀(jì)50年代國內(nèi)自然美問題研究概述
鄒 璐
摘? 要:20世紀(jì)50年代的“美學(xué)大討論”中,自然美問題作為“美學(xué)論爭的第二大問題”出現(xiàn),成為備受關(guān)注的熱點。在“美學(xué)大討論”中主要有以呂熒、高爾泰為代表的“主觀派”,以蔡儀為代表的“客觀派”,以朱光潛為代表的“主客統(tǒng)一派”和以李澤厚為代表的“客觀社會派”。關(guān)于自然美問題的論爭則主要集中在以蔡儀為代表的客觀派和以李澤厚為代表的社會派之間。論爭有兩個方面:自然美的有無問題與自然美的根源問題。朱光潛、蔡儀、李澤厚都有著各自嚴(yán)密的論證,但仍存在著許多不完善之處。
關(guān)鍵詞:美學(xué)大討論;自然美;自然性;社會性
20世紀(jì)初,隨著美學(xué)學(xué)科由西方進(jìn)入中國,自然美作為美學(xué)重要內(nèi)容也進(jìn)入人們的討論視野。20世紀(jì)50年代的“美學(xué)大討論”自1956年開始到1962年結(jié)束,持續(xù)了將近7年的時間,留下了眾多經(jīng)典文章,編纂成六卷本的《美學(xué)問題討論集》。其中,涉及自然美問題的文章就有20余篇。由此可見,“自然美”問題一直是學(xué)界關(guān)注的熱點。
一、“自然美”問題的出現(xiàn)
20世紀(jì)50年代“美學(xué)大討論”的中心問題是“美的本質(zhì)”問題,即美到底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關(guān)于這一本質(zhì)問題的討論涉及到了很多方面,“自然美”問題則是由此中心延伸而來的一個分支問題。杉思認(rèn)為,自然美問題是“美學(xué)論爭的第二大問題”,這一問題是與“美的主客觀”問題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1]。討論“自然美”問題,則先要厘清這一問題為何會在中國當(dāng)代美學(xué)史上出現(xiàn),并成為“美學(xué)大討論”的第二個焦點。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對社會主義新文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為新文化的發(fā)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氛圍。可以說,“美學(xué)大討論”是建國初期思想改造運動與“雙百方針”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那么,在“雙百方針”的大力支持下,為什么出現(xiàn)的不是文學(xué)大討論、藝術(shù)大討論,偏偏是“美學(xué)”大討論呢?
首先是“美學(xué)”學(xué)科從西方的引入。20世紀(jì)初,日本人將“Aesthetic”翻譯為“美學(xué)”,美學(xué)這一學(xué)科也進(jìn)入中國。植根于中國的文化土壤,美學(xué)得以發(fā)展。在經(jīng)歷了20世紀(jì)初以王國維、蔡元培為代表的第一次“美學(xué)熱”后,“美學(xué)”在50年代再一次成為討論熱潮,即第二次“美學(xué)熱”。同時,大量譯介的西方美學(xué)理論在中國出現(xiàn),為“美學(xué)大討論”提供了文本資源。在良好的社會環(huán)境和新興的學(xué)科熱度背景下,20世紀(jì)50年代“美學(xué)大討論”的出現(xiàn)是必然的。而大討論中對“自然美”的關(guān)注則有著深刻的傳統(tǒng)文化根基,“自然美”問題成為討論的第二焦點這一現(xiàn)象具有明顯的“中國特色”。自古以來,中國人對“自然”就有著獨特的看法,傳統(tǒng)詩文與繪畫為討論者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另外,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中國一直進(jìn)行著與“自然”做斗爭的社會實踐,這些征服自然的經(jīng)驗為“自然美”問題的出現(xiàn)提供了語境。
1956年6月,朱光潛的一篇《我的文藝思想的反動性》拉開了大討論的帷幕,在這場關(guān)于“美的本質(zhì)”的討論中,主要分為四派,即以呂熒、高爾泰為代表的“主觀派”,以蔡儀為代表的“客觀派”,以朱光潛為代表的“主客統(tǒng)一派”和以李澤厚為代表的“客觀社會派”。對“自然美”問題的討論則更能凸顯出各位學(xué)者思想的獨特之處。
二、“自然美”的有無與根源之爭
討論“自然美”問題,首先要解決的就是“自然美”的本質(zhì)問題,即自然美的主客觀性問題,也就是說,自然到底存在美嗎?作為“美學(xué)論爭的第二大問題”,“自然美”問題與第一大問題“美的本質(zhì)”問題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對于“自然美”問題,也主要分成了以朱光潛、蔡儀、李澤厚為代表的三種意見,三位學(xué)者主要有兩個分歧點。
分歧一:自然美是否存在
對于“自然美”,三位學(xué)者有著不同的定義。朱光潛認(rèn)為,“‘自然美’三個字,從美學(xué)觀點來看,是自相矛盾的,是‘美’就不‘自然’,只是‘自然’還沒有成為‘美’”[2]。朱光潛認(rèn)為,“自然”與“美”是不相容的,是不可以并提的兩個詞,這是對“自然美”的現(xiàn)實與概念的雙重否定。這種觀點來源于黑格爾的思想,朱光潛認(rèn)為自然無美丑,只有藝術(shù)才有美丑,自然只是美的客觀條件,美的條件并不等于美。因此,自然不存在所謂的“美”,并且所有的美都是具有意識形態(tài)性的。“人不感覺到自然美則已,一旦感覺到自然美,那自然美就已具有意識形態(tài)性或階級性”。那么,“是否還有一種非意識形態(tài)性的、無階級性的,早已存在的純?nèi)豢陀^的不以人的意識為轉(zhuǎn)移的‘自然美’呢?……我說沒有。”[3]
“自然”在朱光潛的眼中,只是人類認(rèn)識和實踐的對象,是美的條件。那么“自然”何以成為“美”?他認(rèn)為,“大地山河以及風(fēng)云星斗原來都是死板的東西,我們往往覺得它們有情感、有生命、有動作,這都是移情作用的結(jié)果。”[4]41朱光潛給出的解釋是:“我們覺得某個自然物美,那個客觀對象必定有某些屬性投合了主觀方面的意識形態(tài)的總和……換句話說,契合了主觀方面的意識形態(tài),由此所得的快感便是美感了。”作為中國第一位奠定了審美心理學(xué)的美學(xué)家,朱光潛認(rèn)為美感是第一性的,美是第二性的,美由美感產(chǎn)生。受克羅齊的影響,朱光潛繼承“快感”論,提出了“美在心在物說”。“美不僅在物,亦不僅在心,它在心與物的關(guān)系上。”[4]153因此,“美就是情趣意象化或意象情趣化時心中所覺到的‘恰好’的快感”[4]153在朱光潛的美學(xué)研究中,自然從來不是他的研究對象,文藝才是,“自然美就是一種雛形的起始階段的藝術(shù)美,也還是自然性與社會性的統(tǒng)一、客觀與主觀的統(tǒng)一”[5]。在《詩論》中朱光潛也曾說過“藝術(shù)返照自然”。自然既然作為藝術(shù)創(chuàng)造出美的條件,那美的條件本身就應(yīng)該包含了美的某些特質(zhì),美的條件并非是無美丑之分的。但朱光潛認(rèn)為自然美是因為作為藝術(shù)的條件才成為美,“自然美”在根本上是一種“藝術(shù)美”。可以看出,朱光潛承認(rèn)自然的客觀性但不承認(rèn)自然美的客觀性[6],自然只是人類心靈的產(chǎn)物。
與朱光潛認(rèn)為自然是美的一種條件不同,蔡儀與李澤厚則肯定了自然美是一種客觀存在。蔡儀的觀點十分明確:“許多客觀事物古代人認(rèn)為美的,而我們現(xiàn)在也認(rèn)為它美,自然事物的美基本上是如此。”[7]對于自然美,蔡儀是堅定的擁護(hù)者。他認(rèn)為美是不依存于人而存在的,“自然事物的美與不美,則是自然事物本身的事,和人對它的認(rèn)識、欣賞與否是無關(guān)系的”[8]9。即使沒有人的存在,“自然美”也是客觀存在于這個世界上的。與朱光潛相反,蔡儀認(rèn)為美是第一性的,美感是第二性的,美決定美感,而不是美感決定美。與朱光潛不同,在藝術(shù)與自然的關(guān)系上,蔡儀認(rèn)為藝術(shù)是為了反映自然,山水畫是為了表現(xiàn)山水的美而存在的。因此,基于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的唯物主義,蔡儀提出了“新美學(xué)”,他認(rèn)為美是客觀存在的,是普遍的、永恒的、絕對的、超歷史的、超階級的,蔡儀將美的研究從概念拉到了現(xiàn)實事物,建立了馬克思主義美學(xué)。
和蔡儀的觀點相同,李澤厚也認(rèn)為美是客觀存在的。盡管李澤厚也同樣認(rèn)為自然美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但這種客觀與蔡儀的客觀不同,李澤厚的客觀是指自然美所具有的社會性是客觀的,而蔡儀的客觀是自然本身客觀存在著美。李澤厚對“自然”的定義是:“我了解的所謂自然是一種‘社會存在’,是指自然在人類產(chǎn)生以后與人類生活所發(fā)生的一定的客觀社會關(guān)系,在人類生活中所占有的一定的客觀社會地位。”[9]164在李澤厚這里,自然美不是朱光潛所說的“藝術(shù)美的雛形”,而是一種客觀的社會存在。
分歧二:自然何以為美
盡管蔡儀、李澤厚二人都認(rèn)為美是客觀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但二人對于“自然美”客觀在何處產(chǎn)生了截然不同的看法。蔡儀認(rèn)為自然美的客觀性在于自然物的自然屬性,李澤厚則認(rèn)為自然美的客觀性在于經(jīng)歷了漫長的人類社會物質(zhì)實踐之后的社會客觀性。
蔡儀認(rèn)為,自然美美在其自然性。蔡儀曾說:“自然美在于自然美本身……自然美是自然事物的個別性顯著地表現(xiàn)一般性。”[10]這里包含了兩個方面,首先,蔡儀肯定自然有美;其次,蔡儀認(rèn)為自然美美在典型。在蔡儀的觀點中,自然美首先是不與人相關(guān),其次是不與社會性相關(guān)。自然美美在它本身所具有的屬性,如花朵美在它的顏色和香氣,即便是金銀,也是因為其獨特的光芒而美。在舉了大量的例子后,蔡儀提出了自己的“美在典型”說。他認(rèn)為“美的本質(zhì)就是事物的典型性,就是事物的個別性顯著地表現(xiàn)著它的本質(zhì)、規(guī)律或一般性”[11]。蔡儀認(rèn)為美的本質(zhì)是典型性,自然美的主要決定條件是它的種屬一般性。蔡儀甚至認(rèn)為,動物比植物高級,因為動物更明顯地表現(xiàn)出了它的種屬一般性。蔡儀從生物發(fā)展的等級來規(guī)定它的美是一種機(jī)械化的分類。這種觀點存在的問題是,自然界中并不存在典型,每一滴水、每一朵花都是美的,并沒有哪一滴水、哪一朵花更美一說。另外,典型并不等于美。正如許多學(xué)者所批評的,蔡儀“把客觀性只理解為純粹自然屬性,它和物質(zhì)本身一樣,可以脫離人類社會而獨立存在。我把自然美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放在與人類生活的客觀關(guān)系上,不僅看到自然美的自然性,而且強(qiáng)調(diào)它的社會性。認(rèn)為自然美必然與人的社會生活分不開”[12]。但蔡儀自始至終都并未像李澤厚那樣幾度修正自己的美學(xué)思想,而是以一種堅定的姿態(tài)捍衛(wèi)著自己的觀點,他所排斥的自然美的社會性則為李澤厚所強(qiáng)調(diào)。
李澤厚認(rèn)為,自然美美在其社會性。這種社會性來源于“自然的人化”“自然的社會性是美的根源”[13]232-233。蔡儀將美分成了自然美和社會美,二者互不相干,李澤厚則將自然美與社會美揉為了一體。李澤厚在《論美感、美和藝術(shù)》中直接下了一個結(jié)論:“美不是物的自然屬性,而是物的社會屬性。美是社會生活中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識的客觀現(xiàn)實的存在。自然美只是這種存在的特殊形式。”[13]237這句話可以看出李澤厚和朱光潛的區(qū)別在于:朱光潛認(rèn)為美產(chǎn)生于美感,而李澤厚認(rèn)為美不依賴于人,否定了朱光潛的移情說;與蔡儀的區(qū)別在于:美在其自然性還是在其社會性。對于蔡儀的典型說,李澤厚給予了猛烈的批判,他認(rèn)為,如果“高級的自然種類屬性比低級的美。那么,蒼蠅、老鼠、蛇就一定要比古松梅花美了……而月亮也一定是最不美的了,因為它只是最低級的物質(zhì)種類(無生物)。”[13]230這段話很直接地指出了蔡儀“典型說”的問題所在。
李澤厚依據(jù)“自然的人化”來解釋美的產(chǎn)生,認(rèn)為自然作為人的對象后才具有了美的屬性。自然之所以美,是因為自然中顯現(xiàn)了“人的本質(zhì)力量”,人類在改造自然、欣賞自然的過程中,看到自己的改變成果,從而產(chǎn)生美感,自然也變成了美的存在。李澤厚的貢獻(xiàn)在于,他認(rèn)為美不是僵死的東西,而是隨著人類社會的發(fā)展不斷變化和豐富的東西,將美放在整個歷史進(jìn)程中進(jìn)行考量,讓美擺脫了朱光潛那種孤立的狀態(tài)和蔡儀那種靜止的狀態(tài)。
但是,李澤厚的觀點也存在著致命的缺陷,即適用范圍問題。對于藝術(shù)作品,我們可以認(rèn)為它們是人類本質(zhì)力量的一種反映,自然物則不同。如果美在于其客觀社會性的話,那么自然物全然都是社會物了嗎?這一觀點顯然很難說服所有人。事實上,大自然中還有很多未經(jīng)人類改造過的自然,其原始屬性仍然是主要屬性,并非所有自然物都具有社會性。“社會屬性”是與“自然屬性”相對的一個概念,如果說自然物完全都是社會性的話,那“自然屬性”去哪了?植物有“社會性”嗎?另外,“社會性”并非是人的專屬屬性,很多自然界中的生物也具有社會性,如螞蟻、蜜蜂等。那美也是它們的社會性與客觀性的統(tǒng)一嗎?“人的本質(zhì)力量”作為一個高度抽象的詞語,如何能定義其好壞?惡的力量是否也是一種“本質(zhì)力量”?這種本質(zhì)力量作用于自然后也是美的嗎?這些問題在李澤厚的觀點中找不到答案。
在蔡儀那里,自然事物是一種最簡單的、最易把握的美,由古到今都具有一種單純的美的力量,美不是什么社會物質(zhì)基礎(chǔ)的反映[8]188,而“社會是自然的延長”。蔡儀說:“自然事物的美即在于自然事物本身,是和自然事物的形狀、顏色或其光澤等分不開的,社會事物的美也在于社會事物本身,是和社會事物的屬性、條件或其形式等分不開的;而藝術(shù)品的美也在于藝術(shù)品本身,也是和藝術(shù)品形成的實際條件及其形象分不開的。”[8]18與蔡儀相比,李澤厚把自然美復(fù)雜化、社會化了。
關(guān)于“自然美”問題的討論,除了上述三位學(xué)者,“大討論”中還出現(xiàn)了一些不同的觀點。比如宗白華肯定自然美的存在,他認(rèn)為自然是一切美的源泉,這是植根于他的生命美學(xué)思想的。“大自然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活力,推動無生界以進(jìn)入有機(jī)界,從有機(jī)界以至于最高的生命、理性、情緒、感覺。這個活力是一切生命的源泉,也是一切‘美’的源泉”。深受《周易》的影響,宗白華認(rèn)為,自然美美在其內(nèi)在的生命律動。
那么自然美究竟美在何處?自然天生具有美,這是不可否認(rèn)的。盡管美并不直接等于自然屬性,但美與自然物本身的自然屬性是分不開的,它可以在各種各樣或精巧或宏壯的形式中找到,并通過這些形式表現(xiàn)出來。在人類出現(xiàn)以前,自然本身就已經(jīng)存在,如今我們看到的山川河流、美麗的風(fēng)景和自然物,我們覺得它美,只是人類的出現(xiàn)讓這種美顯明了出來。自然有美,這種美的前提是其本身的自然屬性。誠然,人類社會的出現(xiàn)對整個自然產(chǎn)生了諸多影響,人類的足跡遍布整個地球。可以說,如今的自然幾乎沒有人類不知道或看不見的地方了。但并不能就此認(rèn)為,人走過的自然、改造過的自然就不是原本的“自然”,而是“人化”的自然了。人只是地球上萬千生物中的一種智慧生命體,并不是什么特殊物種。李澤厚認(rèn)為,自然美美在“自然的人化”、美在其社會性,是人類社會決定了美的產(chǎn)生,本質(zhì)上還是自然本身無美的看法,自然美美在社會性其實是自然美決定于人的另一種說法。自然的美只對人有意義,自然美的客觀性也就隨之消失了。另外,“自然”二字與“社會”二字本就是不能并提的兩個詞語,既然“自然”,如何“社會”?如果“社會”則必定不是“自然”。李澤厚將“自然”與“社會”糅合有其合理之處,但認(rèn)為自然美完全美在社會性是不準(zhǔn)確的。
自然美不是“人化的”對象,如果將自然美作為一個實體,我們將無法探尋出自然美的真諦。如阿多諾所言,“自然中的美,如同音樂中的美一樣,就像轉(zhuǎn)瞬即逝的火花,你剛要捕捉它時,卻一閃眼不見了”[14],人作為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我們的來處,其價值應(yīng)該被予以最高的肯定。
三、“自然美”問題的當(dāng)代意義
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全球化進(jìn)程加快,生態(tài)問題日漸嚴(yán)重,出現(xiàn)了對自然相關(guān)問題的研究熱潮。人們開始反思自然問題,反思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開始重新思考“自然”的意義,自然美在美學(xué)中的地位逐漸上升。生態(tài)美學(xué)的興起,也讓“自然”的意義不再僅限于狹窄的自然物范疇,而是擴(kuò)展到生命整體的高度。在這一高度下,生態(tài)、環(huán)境、景觀都成了自然問題的延伸或展開,自然美的內(nèi)涵也逐漸擴(kuò)大。即便拋開生態(tài)問題的困擾,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問題仍是我們需要思考的永恒話題。因此,考察20世紀(jì)50年代“美學(xué)大討論”中的自然美問題于今有著重要的意義。當(dāng)我們將人看作自然中的一種生命體,“把自然作為自然”而不是“人化的自然”,不再以人為中心審視自然的時候,“自然美”才能成為最高的美。
參考文獻(xiàn):
[1]杉思.幾年來(1956——1961)關(guān)于美學(xué)問題的討論[C]//《文藝報》編輯部,編.美學(xué)問題討論集:第六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1964:416.
[2]朱光潛.談美[M]//朱光潛美學(xué)文集:第一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487.
[3]朱光潛.山水詩與自然美[J].文學(xué)評論,1960(6):56-63.
[4]朱光潛.文藝心理學(xué)[M]//朱光潛美學(xué)文集:第一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41.
[5]朱光潛.論美是客觀與主觀的統(tǒng)一[C]//《文藝報》編輯部,編.美學(xué)問題討論集:第三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40.
[6]朱羽.“社會主義”與“自然”——以1950-60年代中國的文藝實踐和美學(xué)論爭為中心[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2011.
[7]蔡儀.論美學(xué)上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根本分歧[C]//《文藝報》編輯部,編.美學(xué)問題討論集:第二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185.
[8]蔡儀.蔡儀美學(xué)講演集[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85.
[9]李澤厚.關(guān)于當(dāng)前美學(xué)問題的爭論——試再論美的客觀性和社會性[C]//《文藝報》編輯部,編.美學(xué)問題討論集:第三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164.
[10]蔡儀.唯心主義美學(xué)批判集[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58:141.
[11]蔡儀.呂熒對“新美學(xué)”美是典型之說是怎樣批評的?[C]//《文藝報》編輯部,編.美學(xué)問題討論集:第三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108.
[12]任范.論“金銀”的自然美——兼評蔡儀的“美即典型”論[J].復(fù)旦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1980(5):33-37.
[13]李澤厚.論美感、美和藝術(shù)[C]//《文藝報》編輯部,編.美學(xué)問題討論集:第二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14]阿多諾.美學(xué)理論[M].王柯平,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129.
作者簡介:鄒璐,鄭州大學(xué)文學(xué)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環(huán)境美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