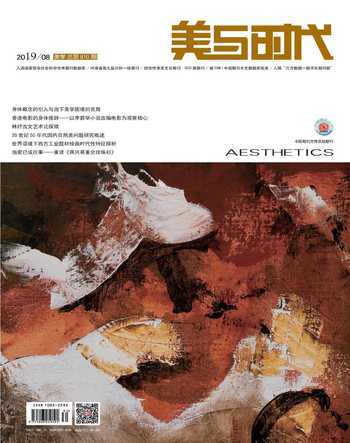多重語境下的知識分子話語
摘? 要:新時期,知識分子反思題材的小說,深受蘇聯文學和“五四”文學傳統的影響,但卻沒有把握其精髓。張賢亮是新時期的重要作家,有22年的勞動改造經歷,小說多以知識分子為主人公,重述他們在政治風暴前后的變化。作家在確認知識分子身份的同時,卻失去了對歷史的真實反思。這背后有著錯綜復雜的原因,從他的兩部作品《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創作的話語環境中我們可以窺探一二。
關鍵詞:知識分子;歷史反思;張賢亮;《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從魯迅開始,現當代文學史上出現了大量的知識分子反思題材的小說。隨著時代語境的變化,反思的側重點也發生了偏離。“文革”結束后出現的一系列的文學作品,或懷想青春歲月,或暴露傷痕,或反思過去,仍是我們記憶歷史的一種方式。其中,一些“右派”復出作家筆下的知識分子在政治運動中成為打壓的對象,恢復政治身份后對歷史發展充滿信心,構成“壞事最終變成好事”[1]167的意義結構。張賢亮的知識分子改造小說《靈與肉》(1979)、《綠化樹》(1984)、《男人的一半是女人》(1985)就是其中的重要作品,發表后曾引起很大的爭議。作家對歷史和知識分子的態度引起了不少評論家的質疑。這幾部作品都發表于20世紀80年代前后,主人公的話語方式顯然與現實的主客觀條件是沒辦法分開的。
一、20世紀80年代前后的話語環境
文學從來都是帶著鐐銬在跳舞,作家們的創作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國人“試圖記憶或忘卻‘文革’的主要方式”[1]154不是通過史料而是作家作品對“文革”的敘述。“‘文革’以后的‘文革故事’,其實已是在重讀‘文革’”,這些故事的敘述方式不僅反映著作家個人的思考也影響著國人的“文革集體記憶”。許子東總結的重讀“文革”的四種方法,可以看到作家們在有意無意地循著一定的規則進行寫作。這些“文革”敘述模式背后是一個時代的政治環境、文化環境、文化心理等。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知識分子們得到了平反。新時期,作家們渴望表達出這些年的壓抑、痛苦,但是在長期的政治壓制之后,他們汲取之前的經驗教訓,仍然小心翼翼地說話。當時的政治環境也并不是完全豁然開朗的,有一個轉變的過程。這也就可以理解“傷痕文學”的發軔之作小說《傷痕》(1978)為什么經歷了許多周折、多次修改才被發表。盧新華本人說:“《傷痕》在發表的過程中也伴隨著‘傷痕’,”之后書寫“文革”的小說也都是在逐漸地沖破以往的思想禁錮。政治氛圍的日漸寬松是作家們敢于吐露心聲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它也沒能提供最充分的條件。20世紀80年代前后的“文革”書寫,如《許茂和他的女兒們》(1980)、《將軍吟》(1980)和《芙蓉鎮》(1981)等獲得茅盾文學獎的小說,寫作的主要目的是迅速療傷,而不是反思歷史和個體。從一些作家個人的創作軌跡中似乎可以看出他們的創作思想也在發生變化。在《靈與肉》中,張賢亮以一個資產階級后代的身份被成功改造的“勞動者”形象擁抱苦盡甘來的偉大成果。幾年后創作的《綠化樹》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章永璘對馬纓花和黃久鄉等勞動者感謝之后是訣別。這并不是說張賢亮對“文革”的認識更加深刻了,而是他開始表現一個知識分子內心的身份認同。顯然,張賢亮創作思想的變化也僅限于對個體的反思,而不包括歷史。
知識分子話語并沒有得到完全解放,它依舊不同程度地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除了要關注作品能否被發表,作家們還要考慮評獎制度以及是否會受到批判,或多或少會受到當時的文化與政治環境的約束。他們不自覺地將這些意識帶入了自己的作品中,所以不能真實客觀地反思“文革”,遮蔽掉了很多真相不說,甚至會使人誤讀“文革”。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發表后引起了許多的社會爭議,評論家王曉明、南帆、黃子平都對章永璘這一知識分子形象產生了質疑。張賢亮為表明政治立場將章永璘與“革命道德”銜接起來不免有些生硬,同時他知識分子的優越感也與他要贊揚的革命力量發生了矛盾。總之,作家在這些因素的權衡中暴露出了一些問題。
已經棄筆多年的作家們并不能確定讀者們的閱讀喜好,從傳統文學中吸取經驗是一個保守的選擇。傳統文學模式已經在讀者群中扎下了根,很容易就能進入文本。知識分子歷史反思題材小說嵌入好看故事的同時,也不忘與各方面的閱讀群體達成和解。不止是張賢亮的作品,這一時期的反思小說如王蒙的《蝴蝶》(1980)、戴厚英的《人啊,人!》(1980)等,都在有意無意地遮蔽傷痛。這些知識分子主人公最終都在“苦盡甘來”的喜悅中迎接光明未來,渴望在新的時代一展身手。無論是主人公還是作家本人都在文本中維護了知識分子的顏面,避重就輕的敘述也能使讀者從中獲得一些寬慰。
可見,以上這些客觀因素都影響了作家如何呈現“文革”。但是,作家在“文革”中的個人經歷無法在他們的心中抹掉,在作品中也會時隱時現。所以,這些主客觀條件會共同作用于作家作品,作家會不自覺地保持距離自己最近的身份介入文本。張賢亮多以知識分子作為小說的主人公,無疑與他的人生經歷有很大的關系。
二、從詩人到小說家
張賢亮曾說:“我的人生就是一部厚厚的小說。”[2]1936年出生的張賢亮和所有同時代的人一樣,見證了政治風暴帶給人們的創傷,22年的勞改經歷讓他對這段歷史更加刻骨銘心。“文革”結束后,張賢亮開始創作小說,成為當代著名作家,從貧瘠的寧夏鎮北堡景觀中汲取靈感,創辦了鎮北堡西部影視城。他既是文人,也是商人。在當代文學史上,張賢亮更多地是以一個反思歷史的小說家的身份被大家熟知。從一個詩人到一個小說家、商人,這種身份的轉換有作家不同的人生追求,也有歷史的推波助瀾。
他的小說其實是帶有自傳色彩的,落難知識分子的形象是他勞動改造經歷的再現。張賢亮出生于南京的一個官宦世家,父母都是名門之后,父親在“西安事變”后棄政從商,后來成為買辦資本家。1954年,高中即將畢業的張賢亮,因歷史問題,與母親、妹妹來到了寧夏落戶。在此之前,憑借少年時期受過的良好的教育及個人天賦,他已經發表了一些詩歌。1956年在毛澤東“雙百方針”的指導下,文化形勢一片大好,張賢亮被當地政府聘任為語文教員。“總之,我的確感受到了‘新時代的來臨’,于是我以全部的真誠唱出了這首《大風歌》。”[3]571957年7月,這首詩發表在了《延河》七月號中,在當時的“反右運動”中被《人民日報》點名批判,隨后他被押送農場勞動改造。這段經歷散見于作家后來創作的作品之中。
1979年被“平反”后,張賢亮發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說《靈與肉》,此后又創作了許多小說、散文、電影劇本等,但是再也不愿寫詩。“人一‘務實’便無詩可言,我已失去了詩的境界和高度”[3]57,多年的“勞改”生活之后,張賢亮失去的不只是青春歲月,也失去了一個詩人的赤子之心。《大風歌》本是張賢亮對時代新發展的激情贊頌,卻被認為是對社會主義發展的詛咒,被扣上了“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帽子。作家認為不公正的對待與自己資產階級家庭出身有關系,這些質疑的聲音在他后來的散文中表述得更為清楚。他在《中國文人的另一種風格》一書中感嘆,僅因一張薄薄的漏洞百出的“雪蓮紙”,自己就受了22年的苦。回望過去自由的21年和接受勞改的22年,張賢亮的寫作顯然無法回避剛剛過去的苦難。一個剛復出的“右派”作家,書寫這段歷史時已經失去了當年的自信和銳氣,其中的妥協成分包裹了真實的委屈。
從詩人到小說家,中間的過渡身份是一個“勞改犯”,在一次次的政治運動中被打壓。隨著身份變化的不只是作家的年齡,更有他的心態。在農村生活20多年,以“老右”的身份與鄉民相處,似乎已經習慣了那里的生活。災荒之年忍受饑餓與寒冷,多次在死亡線上掙扎。面對過去的個人疼痛與歷史疼痛,張賢亮的心情是復雜的。
三、知識分子歷史反思的兩面性
重新回到知識分子的話語體系之內,對于作家們而言是一件值得開心的事。不可否認的是,大多數當代作家的“文革”敘述都表達了每一個自愿或是被迫下鄉勞動改造的知識青年最終試圖融入當地的生產生活。被冠以“右派分子”“反黨反革命壞分子”等罪名的知識分子,這種愿望則比普通人更強烈。所以,新時期的反思小說多少都會流露出對鄉村的眷戀,即使他們曾經在那里吃了數不盡的苦頭。在這一層面上,張賢亮的態度也是明確的。許靈均和章永璘對廣闊的黃土高原、勞動人民有著熱烈的感情,這片美麗又神奇、丑陋又邪惡的土地,吸干了他們的的汗水、淚水、愛情。他們逐漸適應了勞動,成為一個勞動能手,與這片土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靈與肉》中大段地描寫高原上的美景,在平凡的勞動中許靈均的委屈和消沉漸漸變成了對生命和自然的熱愛。許靈均在政治上是被批斗被勞改的“右派分子”、老放牧員、“郭蹁子”,秀芝這些農民把他當做好人。他最終放棄繼承資本家父親的巨額財產,選擇了繼續陪伴他的老鄉們。同時,許靈均作為一個鄉村教師為新時代貢獻力量的決心與理想,也從側面表現出張賢亮重獲自由時的感激、喜悅之情。作品寫于作家離開農場不久,對于“勞改”當地的農村、農民的依戀是真摯的,畢竟他在那里度過了最年富力強的22年。
如果說許靈均是在以感謝苦難的姿態懷念過去,章永璘則開始跳脫出被改造的“勞動者”形象,以知識分子的身份重新審視自己和現實。章永璘在《綠化樹》中對于馬纓花、謝隊長、海喜喜的善良依然抱有感激的態度,他認為是這些勞動者在嚴酷的環境中溫暖著他。到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章永璘眼中對于歷史以及其中的人們有了思考,“文革”期間為何創造了破世界記錄的犯罪率,而這些階級敵人到底是誰的敵人。他和大青馬之間關于“自由”和“閹割”的對話是對歷史發出的又一個追問。這些細節中,他都在以知識分子的眼光探索曾經失衡的歷史關系。
但是,這種知識分子眼光并不是完全精準的,在主客觀條件的制約下發生了變形。章永璘對馬纓花和黃久香的態度受到了許多評論家、女權主義者的批判。章永璘以和馬纓花、黃久香的差距來粉飾自己知識分子的優越感。“文革”結束后,知青與鄉下姑娘的戀愛以結婚或訣別收場,的確是當時的現實情況。為了回到城市,知青們割斷以往的聯系重新尋找自己的生存空間是常見的。章永璘們卻以這些女性勞動者的深情為背景來襯托自己形象的高大。馬纓花無條件地為章永璘提供當時最珍貴的糧食,只因戀著這個男人會“讀書”。章永璘眼中的馬纓花,盡管以前有“美國飯店”的不潔外號,現在卻是一個只忠誠于自己、精明能干的農家女人。在他解決了溫飽問題之后,開始思索愛情,認為“她雖美麗、善良、純真,但終究還是一個未脫粗俗的女人”[4]。這里我們看到章永璘表現出的知識分子的虛偽性,在饑餓難耐時馬纓花的落在饅頭上的指紋都是性感的,一旦解決溫飽就與之劃清界限,他骨子里的清高、自戀可見一斑。
作品沉溺于個體傷痛的表達,對歷史真相呈現和反思都浮于表面。作家沿用傳統小說的“才子佳人”模式,多次制造落難知識分子被風塵女子拯救的橋段,獲得現實利益之后又以兩人的“差距”為借口訣別。章永璘因為新的政治運動和馬纓花永遠地失去了聯系,他們的結局看似是客觀條件造成的,不如說是章永璘或者張賢亮的真實想法。馬纓花不過是普通的體力勞動者中的一員,她的出現似乎只是為了給男性知識分子落難時的物質和精神補給。章永璘受難之時馬纓花是“女人”“女性”,重獲輝煌時她是“勞動者”。章永璘獲得了一個知識分子的體面,也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決心。張賢亮的另一部小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直言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另一半是政治。即使黃久香已經和章永璘結婚,維系他們的,“在根子上恰恰是情欲激起的需求,是肉與肉的接觸”[5]。黃久香只是章永璘知識分子身份確認的一個工具而已。章永璘的“性無能”與知識分子使命之間的隱喻關系,作家強行將政治話語嵌入到了文本的敘事邏輯中。在抗洪救災之后,章永璘恢復了一個男人的特征,作家無形之中又贊揚了革命力量的偉大。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章永璘對過去、未來的思考都沒有談及本質,從歷史的苦難中走出,完成自己的身份確認才是他最渴望的。在身份和解的同時已經失去了知識分子的自我意志。
四、結語
我們可以看到,張賢亮的散文比小說更加客觀地反思了這段歷史,除了文體本身的限制之外當然更多地是外部話語環境的制約。這些小說引起的社會爭議和討論,也反映了20世紀80年代前后的反思小說是在多種話語運作機制下發生的。保守的敘述方式不失為作家們保全自我的好方法,一舉多得的事情何樂而不為呢?可是這些親歷“文革”的作家,他們的敘述不僅影響著讀者,也與我們整個民族的“文革集體記憶”密切相關。如果面對歷史,知識分子的內心是如此脆弱,這就需要思考知識分子的精神獨立性是否仍然存在?
參考文獻:
[1]許子東.重讀“文革”:許子東講稿[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2]張賢亮.我的人生就是一部厚重的小說[J].湖南文學,2009(1):23-26.
[3]張賢亮.今日再說《大風歌》[J].詩刊,2002(11):57.
[4]張賢亮.綠化樹[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4:159.
[5]張賢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13:164.
作者簡介:時雪麗,鄭州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