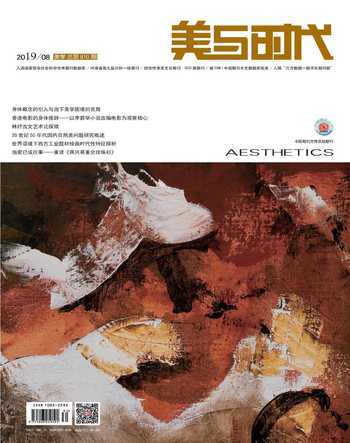《詩學(xué)》悲劇理論視域下的《原野》
摘? 要:亞里士多德《詩學(xué)》中提出的悲劇理論,奠定了西方美學(xué)史上悲劇范疇的理論基礎(chǔ)。以《詩學(xué)》中的悲劇理論為參照,探討《原野》在創(chuàng)作上的結(jié)構(gòu)安排、情節(jié)布局以及隱含在劇作中作者的人性理念,不僅可以更好地從理論上把握《原野》劇中所暗含的普遍悲劇創(chuàng)作理論與文章背后所傳達(dá)的人生價值觀,而且也可以了解西方美學(xué)悲劇理論對于中國現(xiàn)代戲劇產(chǎn)生的影響。
關(guān)鍵詞:悲劇;《詩學(xué)》;《原野》;復(fù)仇正義性
亞里士多德《詩學(xué)》是西方最早一部具有系統(tǒng)美學(xué)理論的重要文獻(xiàn),書中的戲劇理論奠定了西方美學(xué)史上戲劇理論的基礎(chǔ),其中大部分篇章都在對悲劇進(jìn)行探討——悲劇的定義、性質(zhì)、功用等方面。戲劇《原野》作為曹禺經(jīng)典作品之一,單就劇中人物的經(jīng)歷和結(jié)局來看,是歸屬于悲劇的。以《詩學(xué)》中的悲劇理論為參照,探討《原野》在創(chuàng)作上的結(jié)構(gòu)安排、情節(jié)布局以及隱含在劇作中作者的人性理念,不僅可以更好地從理論上把握《原野》劇中所暗含的普遍悲劇創(chuàng)作理論與文章背后所傳達(dá)的人生價值觀,而且也可以了解西方美學(xué)悲劇理論對于中國現(xiàn)代戲劇產(chǎn)生的影響。
一、悲劇定義下《原野》的完整性
“悲劇是對一個嚴(yán)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摹仿。”[1]63亞里士多德十分強調(diào)悲劇作品的完整性,認(rèn)為“因為有的事物雖然可能完整,但卻沒有足夠的長度。一個完整的事物由起始、中段和結(jié)尾組成”[1]74。在現(xiàn)代戲劇的創(chuàng)作中這三者無疑是作品中最基礎(chǔ)的概念與必備要素。起始不必繼承它者,但要接受其他存在或后來者的出于自然承繼的部分。在《原野》的序幕中,作者就借白傻子與仇虎的對話交代了主要人物的現(xiàn)狀——仇虎從囚車出逃回原野,打算回老家找仇人焦閻王報仇,卻發(fā)現(xiàn)仇人已死,心愛的女人(金子)嫁給了自己視如親生兄弟的仇人的兒子(焦大星)。在焦母、焦大星與焦花氏的對話與舉動之間便使觀眾知曉了存在于三者之間的矛盾。序幕的最后,作者又安排了仇虎和金子的碰面,這就為后面情節(jié)的發(fā)展與承繼提供了條件。從一開始,作者就把復(fù)仇這一主題不加鋪墊地直接推到觀眾面前,仇虎一出場就是來復(fù)仇的,其復(fù)仇的對象是自己的干媽、幼時的好友和還在襁褓中的孩子。這樣的起始,簡要交代了時間、地點、主要人物與其中所蘊含的矛盾關(guān)系,清晰明了,矛盾沖突明顯,使文章后續(xù)的承繼發(fā)展顯得順理成章。
而中段是承上啟下的部分,隨著序幕情節(jié)的發(fā)展,《原野》的中段部分主要集中在情節(jié)的具體展開部分(第一幕至第二幕)。承接了起始部分中所交代的各種矛盾關(guān)系,仇虎與焦大星、仇虎與焦母、焦母與金子、金子與焦大星之間的復(fù)雜矛盾通過人物之間復(fù)雜行動與意味深長的對話,情節(jié)逐步推進(jìn),最后仇虎狠心殺死了焦大星,帶著金子逃竄至黑樹林;焦母錯殺自己的親孫子,誓死都要殺了仇虎為自己的兒孫二人報仇。由此,各種情節(jié)承上啟下,自然地引出了整個戲劇的最后部分:夜半時分,仇虎與金子在黑林子里迷路,焦母抱著死去的孫子,帶著白傻子追至黑樹林。再結(jié)合著作者有意安排的各種和現(xiàn)實不符的幻想和各種帶有緊張氛圍的環(huán)境,仇虎變得瘋癲,強勸金子離開,自己選擇自殺,焦母失足掉進(jìn)水塘生死不明。這一悲劇性的結(jié)局就正好符合《詩學(xué)》中說的“結(jié)尾指本身自然地承繼它者,但不再接受承繼的部分,它的承繼或是因為出于必須,或是因為符合多數(shù)的情況”[1]74。仇虎在帶著金子疲憊地逃亡之中看到的各種幻像引發(fā)了他內(nèi)心深處對于人性的思考,他不但意識到了他復(fù)仇的絕路,而且意識到了作為肉身自我的極度的困境和絕望,承繼著他復(fù)仇之路所犯下的各種罪孽,面對偵緝大隊的追捕,他選擇了自殺。而焦家也承繼著之前對仇虎一家所犯下的罪孽,落得個斷子絕孫的下場。整個戲劇從起始矛盾鮮明、人物關(guān)系復(fù)雜到中段承繼各種矛盾作精彩具體的深化發(fā)展,再到最后結(jié)尾矛盾在人物的行動與曲折的情節(jié)之下逐一化解,各個人物都得到了自己看似偶然實則必然的結(jié)局。
“一部悲劇由結(jié)和解組成。所謂‘結(jié)’,始于最初的部分,止于人物即將轉(zhuǎn)入順境或逆境的前一刻;所謂‘解’,始于變化的開始,止于劇終。”[1]13悲劇就是表現(xiàn)人物命運的變化,“結(jié)”與“解”是由起始轉(zhuǎn)向結(jié)局的情勢安排。“結(jié)”是矛盾的出現(xiàn)及其承繼的展開,“解”是劇情發(fā)展的必然結(jié)果。“結(jié)”經(jīng)“解” 轉(zhuǎn)變,改變了順或逆的走向,矛盾繼續(xù)發(fā)展,最終矛盾推至高潮,達(dá)到必然性的結(jié)局。《原野》的“結(jié)”就是由戲劇的起始部分作者制造的仇虎與焦家的殺父辱妹、霸占家產(chǎn)的矛盾與焦母與金子二人婆媳之間的矛盾開始發(fā)展至戲劇的中段部分,焦大星被懷疑金子在家與外人偷情的焦母從鐵路上的崗位召回家為止。而戲劇中的“解”便由此開始,焦大星回家后在與焦母的對話之中得知金子與人偷情,婆媳矛盾與夫妻矛盾進(jìn)一步激化,焦家母子由此發(fā)現(xiàn)仇虎的存在。整部戲劇就在伴隨著仇虎與焦家母子的碰面之下,形勢由起初的焦家母子占主導(dǎo)地位的順勢轉(zhuǎn)向了焦母害怕仇虎逃獄回來復(fù)仇、處處被仇虎牽制、陷入被動局面的逆勢。最后,焦家與仇虎之間的矛盾被推至高潮,仇虎痛心殺害了焦大星,焦母在處心積慮的謀劃后卻陰差陽錯地錯殺了自己的親孫子——小黑子。戲劇便在仇虎帶著金子慌亂逃竄、焦母因自己兒孫的死陷入癲狂、誓死都要跟著仇虎為其報仇之處進(jìn)入了戲劇的結(jié)尾部分,最終達(dá)到了所有主要人物相繼死去,金子不知去向的這一必然性的悲劇結(jié)局。《原野》中的“結(jié)”與“解”密切契合,使得整個戲劇對于觀眾來說,達(dá)到了對于整部戲劇必然性悲劇結(jié)局的理解和對于復(fù)仇道義的正義性的體會。
二、 《原野》情節(jié)的突轉(zhuǎn)與發(fā)現(xiàn)
(一)情節(jié)的“突轉(zhuǎn)”
亞里士多德認(rèn)為悲劇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動,情節(jié)是對行動的摹仿。“情節(jié)”是指事件的組合,它是悲劇的目的、根本、靈魂,一部好的戲劇應(yīng)該是“復(fù)雜的行動”。“復(fù)雜的行動指其中的變化有發(fā)現(xiàn)或突轉(zhuǎn)、或有此二者伴隨的行動。這些應(yīng)出自情節(jié)本身的構(gòu)合,如此方能表明它們是前事的必然或可然的結(jié)果。”[1]88“突轉(zhuǎn)”和“發(fā)現(xiàn)”是情節(jié)的兩個成分,它們對于一部戲劇中情節(jié)的變化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突轉(zhuǎn)”指行動的發(fā)展從一個方向轉(zhuǎn)至相反的方向,這種轉(zhuǎn)變必須符合可然或必然的原則。而《原野》是存在著符合可然或必然原則的“突轉(zhuǎn)”的。在仇虎還未與焦家母子碰面之前,雖然焦家存在著婆媳矛盾,焦大星介于婆媳之間兩面為難,但總的來說,焦母在焦家仍然是居于主導(dǎo)地位的,焦家的生活狀態(tài)還算美滿。可是這一切都在仇虎與金子相遇、二人偷情之事被焦大星驗證之后發(fā)生了轉(zhuǎn)變。焦大星在與仇虎敘舊的飯桌上聽聞仇虎敘述自己的父親不顧兩家人多年的情誼,殺死仇虎的父親,將仇虎的妹妹賣至妓院導(dǎo)致其被折磨致死,仇虎被自己的父親以莫須有的罪名冤入大獄之后,在醉酒的狀態(tài)之下被仇虎用一把匕首結(jié)束了自己的生命。一個擁有自己美好生活軌跡的人就在這突轉(zhuǎn)的情節(jié)之下發(fā)生了轉(zhuǎn)變。在仇虎看來,焦大星的死是父債子償,合情合理,而焦大星自身懦弱的性格也使得這一情節(jié)的突轉(zhuǎn)符合必然原則。在之后的情節(jié)之中,焦母還未知曉自己的兒子已被仇虎殺害,打算在深夜趁仇虎熟睡之時用拐杖打死仇虎,卻不料因自己眼盲,計謀被仇虎識破,陰差陽錯打死了自己的親孫子。這里,情節(jié)隨著焦大星的死發(fā)生突轉(zhuǎn)之后,緊接著又以孫子小黑子的死再次發(fā)生突轉(zhuǎn),劇情的發(fā)展被推向了高潮。此時小黑子的死對于劇中人物來說是太過偶然的,但是對于劇外觀眾來說,又可以理解為是偶然中的必然。焦母從仇虎在她面前現(xiàn)身開始,就沒想過要讓仇虎活著離開,仇虎也心懷復(fù)仇,抱著打算讓焦家斷子絕孫的這一目的。因此在二人如此激烈的矛盾之下,無辜的焦大星與小黑子就必然會成為這一矛盾進(jìn)一步演化的犧牲品,這一點也使劇外的觀眾產(chǎn)生共鳴,感受到因為焦母與仇虎二人人性的泯滅與扭曲,焦大星與小黑子二人看似偶然、實則必然的悲劇命運。
(二)情節(jié)的“發(fā)現(xiàn)”
“發(fā)現(xiàn)指從不知到知的轉(zhuǎn)變,即使置身于順達(dá)之境或敗逆之境中的人物認(rèn)識到對方原來是自己的親人或仇敵。最佳的發(fā)現(xiàn)與突轉(zhuǎn)同時出現(xiàn)。”[1]89“發(fā)現(xiàn)”的類型主要分為兩種:一是一方身份明確,發(fā)現(xiàn)是另一方的事。就如《原野》中對于金子來說,與她私會的男人是仇虎的這一身份是明確的,但這一身份就要順著情節(jié)的設(shè)置、線索的鋪墊,等著焦母與焦大星去發(fā)現(xiàn),繼而焦家母子發(fā)現(xiàn)了仇虎的歸來,使得后面的情節(jié)發(fā)生突轉(zhuǎn)。另一種“發(fā)現(xiàn)”是雙方需互相發(fā)現(xiàn)。但這一種情況在《原野》的創(chuàng)作中沒有涉及。在小黑子被焦母錯殺這一情節(jié)處,仇虎之前早就料到焦母會對他痛下殺手,就將計就計,明知躺在床上的只是一個無辜的小孩,卻因為是焦家的后代,理應(yīng)為焦家犯下的罪孽贖罪,放任小黑子慘死在焦母的拐杖之下。對于床上死者的身份,仇虎與金子是知道的,只是等著焦母去發(fā)現(xiàn)。而當(dāng)雙目失明的焦母發(fā)現(xiàn)時,情節(jié)也被推向了高潮。正是在這一情節(jié)處,整部戲劇發(fā)生了強烈的突轉(zhuǎn),發(fā)現(xiàn)與突轉(zhuǎn)同時發(fā)生,二者產(chǎn)生關(guān)聯(lián),共同推動了情節(jié)的發(fā)展與矛盾的激化,在戲劇所設(shè)置的各種偶然巧合之下使戲外的觀眾知曉了焦家必然的悲劇命運。因此,這一發(fā)現(xiàn),算是《原野》之中最佳的發(fā)現(xiàn)。
三、《原野》中的憐憫與恐懼
(一)情節(jié)構(gòu)合方面
亞里士多德規(guī)定悲劇摹仿的不僅是一個完整的行動,而是能引發(fā)恐懼和悲憫的事件。悲劇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于人的行動,通過引發(fā)憐憫和恐懼使這些情感得到疏泄。“悲劇的功效就是通過能使人驚異的劇情引起讀者或者觀眾憐憫和恐懼并使他們在體驗這些情感中得快感。”[1]71“通過源于自我的情感體驗,使壓抑在內(nèi)心的不利于身心健康的情感通過合適的渠道(如悲劇)進(jìn)行宣泄,將這些不利的情感排逐出去,從而達(dá)到凈化心靈的功效。”[2]可以看出,這與觀眾是有著緊密聯(lián)系的。因為“憐憫”對象是遭受了不該遭受之不幸的“別人”,而“恐懼”的產(chǎn)生是由于遭受不幸的這個“別人”是和我們一樣的人。由此,能夠引發(fā)憐憫與恐懼的事件與觀眾發(fā)生聯(lián)系,觀眾感同身受地被痛苦的情節(jié)所打動,從而產(chǎn)生相同的情感。而在《原野》的創(chuàng)作之中,作者也巧妙地看到了文本與觀眾這一密切關(guān)系,在情節(jié)設(shè)置上,精心編排了能夠引發(fā)觀眾憐憫與恐懼的事件。例如,焦大星與小黑子的死,只是因為上一代人犯下的錯誤就要遭受到本不應(yīng)該降臨在自己身上的禍?zhǔn)拢谇楣?jié)的“突轉(zhuǎn)”與“發(fā)現(xiàn)”結(jié)合之下,打動了觀眾,使觀眾在戲外觀賞的過程中產(chǎn)生憐憫之情,為二人悲慘的身世感到惋惜。同時,觀眾也會因為作者對于情節(jié)精彩的描述,將自己帶入到劇情的發(fā)展之中,感受到當(dāng)時緊張的氣氛,在自己的內(nèi)心產(chǎn)生驚異感與恐懼。在《原野》最后一幕的設(shè)計上,作者選擇了不同于之前作品的傳統(tǒng)寫實手法,而是采用了與尤金·奧尼爾《瓊斯皇》相類似的表現(xiàn)主義手法,設(shè)計了各種伴隨著鼓聲浮現(xiàn)在仇虎面前的各種脫離現(xiàn)實的離奇詭異的的幻像,將仇虎帶回到自己父親、妹妹被洪老、焦閻王殘忍活埋害死的場景之中,帶回到自己當(dāng)時被焦閻王陷害入獄在坐獄時被獄長殘害的場景,帶入到具有神秘及神話色彩的自己的父親與妹妹在牛頭馬面的押送下被真正的閻王爺在地獄審問的場景之中。作者所設(shè)置的這些幻像給觀眾帶來了強烈的驚異感,使觀眾將自己的注意力都轉(zhuǎn)向了作者所設(shè)置的情節(jié)之中,跟隨著主人公在現(xiàn)實與非現(xiàn)實之間來回穿梭,感人物所感。在這些幻境之中,仇虎不得不再次面對自己曾經(jīng)經(jīng)歷過的痛苦場面,看到即便是到了最公正、能夠還人公道的閻王爺?shù)拿媲埃约旱母赣H與妹妹的冤情也被巧舌如簧的仇人給辯駁敷衍過去的場景。這所有痛苦的場景與最后得到的不公的審判結(jié)果都使得仇虎內(nèi)心痛苦不堪,這讓他覺得自己為了復(fù)仇,不惜違背自己的良心,殺死自己的兄弟和對一個無辜的嬰兒見死不救的這一切顯得是那樣蒼白無力。此時仇虎內(nèi)心情感的變化已經(jīng)從一開始的復(fù)仇后的喜悅轉(zhuǎn)變成了對于自我極致的絕望,最終仇虎選擇了以自殺的方式來擺脫現(xiàn)實對于他所帶上的“鐐銬”。就戲外的觀眾而言,觀眾在作者刻意設(shè)置的這些帶有虛幻神秘色彩的情節(jié)里見證了仇虎這一明顯變化,由此也會相繼產(chǎn)生對于仇虎悲劇命運的憐憫之感和對于現(xiàn)實冰冷殘酷之實的恐懼之感。這些被引起的憐憫與恐懼之感繼而使觀眾內(nèi)心不利于身心健康的情感得以疏泄,“堵著”的內(nèi)心由此得到了凈化,達(dá)到了平和的狀態(tài)。
(二)戲景方面
《詩學(xué)》中提到恐懼和憐憫除了可以出自情節(jié)本身的構(gòu)合之外,還可以出自戲景。但亞里士多德認(rèn)為,戲景雖能夠吸引人,卻最缺少藝術(shù)性,是相對次要的部分。與之相反,現(xiàn)代戲劇的創(chuàng)作對于戲景(環(huán)境)的營造卻是十分重視的,并且認(rèn)為好的戲景的創(chuàng)造對于情節(jié)的發(fā)展會起到深化甚至是決定性作用。在《原野》之中,戲景的描述在整部戲劇的創(chuàng)作比例上占了較大比重。作者在每一幕的開頭都會描繪一些代表陰郁孤寂一類的景象來渲染人物所處的具體環(huán)境。“蒼茫的原野上,沒有村落,沒有人煙,只有野風(fēng)的呼嘯和野塘里青蛙的叫聲、樹上的蟬聲,以及火車的鳴叫聲。”[3]在作者描繪的戲景之中,充滿著原始?xì)庀ⅲ褂^眾強烈地感受到在這里,只有仇虎的仇恨,再無其他。因為他內(nèi)心的復(fù)仇已將周遭的一切“燃燒殆盡”。觀眾能夠從描繪的戲景中間接地感受到人物內(nèi)心的痛苦掙扎,繼而產(chǎn)生憐憫與恐懼之情。作者描繪夜半后陰森森的原野和恐怖的黑樹林,使觀眾聯(lián)想到了現(xiàn)實世界的黑暗和殘酷,明白了正是因為當(dāng)時社會的冷漠與不公才會導(dǎo)致原本生性純良的主人公的人性發(fā)生扭曲,產(chǎn)生一心只想要復(fù)仇、與整個世界抗?fàn)幍倪@樣一種怪異的性格。在仇虎的認(rèn)知層面,復(fù)仇是充滿正義性的。并且通過作者一層層對于幻境的描繪剖析,觀眾仿佛如同主人公一般看到了他內(nèi)心痛苦的掙扎:屢遭挫敗,飽受苦難,不公對待,強權(quán)壓制,這使仇虎慢慢變成了一個仇恨的化身。大星、小黑子的死使他內(nèi)疚,仇虎內(nèi)心深處的善良在與他的仇恨發(fā)生博弈,而劇中多次伴隨著幻境出現(xiàn)的鼓聲(后改成木魚聲),更進(jìn)一步渲染了緊張神秘的氣氛,從而從另一個角度揭示了仇虎內(nèi)心的矛盾。曹禺通過表現(xiàn)主義的手法來描寫戲景,創(chuàng)造出一種神秘詭異的美,使觀眾在作者設(shè)計的戲景之中去感受仇虎所經(jīng)歷的痛苦與苦難,從而在自己的觀賞與審美之中產(chǎn)生憐憫與恐懼,體會到復(fù)雜扭曲而又令人驚異的人性力量以及作者對于復(fù)仇這一行為正義性的理解——盡管以人道主義的觀點來看,仇虎從一開始就已然從白傻子的口中得知自己的仇人焦閻王已死,但仍然選擇復(fù)仇是可笑而又錯誤的,但作者的創(chuàng)作意圖顯然已經(jīng)跳過了這一層面,而是想要為復(fù)仇者找到一種突破自己內(nèi)心由復(fù)仇所編織起來的“枷鎖”的方法,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解脫。
以亞里士多德《詩學(xué)》中的悲劇理論來解析曹禺的經(jīng)典戲劇《原野》,不僅可以加深對于其理論的理解,找到二者的共通點即承繼戲劇創(chuàng)作之中經(jīng)典化的部分,而且可以在具體的理解分析中找到現(xiàn)代戲劇在戲劇創(chuàng)作上所做的新突破、新嘗試。
參考文獻(xiàn):
[1]亞里士多德.詩學(xué)[M].陳中梅,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6.
[2]李恒.亞里士多德《詩學(xué)》中的悲劇理論綜述[J].商丘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2016(4):80-82.
[3]呂曉明.論《原野》中人物形象的塑造[J].新鄉(xiāng)教育學(xué)院學(xué)報,2009(3):73-74.
作者簡介:劉婷,西南大學(xué)文學(xué)院美學(xué)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