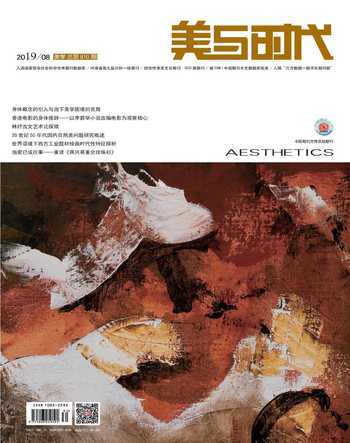愛與美是一對親姊妹
摘? 要:美與愛是一對親姐妹,她們相偎相依、形影不離。正因為“愛得深沉”,才會有藝術美的再現和創造。大愛正是打開大美的萬能鎖,心懷大愛,就會具有“音樂的耳朵和形式美的眼睛”,就會創作出世間最感人動聽的樂章和最美最新的畫卷。美和愛相伴而行,大美吸引和滋潤著大愛,大愛為到達大美的目的地而永不停息地前行!
關鍵詞:愛與美;王學忠;《愛得深沉》
我與河南著名詩人王學忠的相識、相交,算來已有10余年。雖然我們各居安陽、北京兩個城市,見面的機會不多,但交流并不少。一般來說,我對當代作家、作品關注和研讀甚少,尤其是對詩人、詩歌,可王學忠和少數幾位年輕詩人及其詩歌作者卻屬例外。這是因為,他們的創作確實打動了我,他們的追求深深地吸引了我,他們的真誠強烈地感動了我。王學忠的所有作品和關于他的評論,我幾乎全都讀過。因此,不久前收到他發來的即將出版的新作《愛得深沉》的電子版時,我立即放下手頭上的工作,一口氣從頭至尾讀完,并感到由衷的欣喜和興奮。在我的印象中,這似乎是他的第一部多文體的“詩文合集”,是他的創作和人生征途向著新的目標和新的“精神高地”邁出重要的一大步。
《愛得深沉》共分6輯:第一輯收錄《螻蟻之死》和《私有制是萬惡之源》組詩及作者近年新創作的21首“政治詩”“諷刺詩”;第二輯包括《小詩·大詩》和《桂林雜感》兩組組詩,以及其他的詩篇共20余首;第三輯中《我的父親》和《寫給它們中的幾個》(組詩)以及《聽雨》《有一種情愫》《下雪的冬季》等短詩,也可看作“抒情詩”組合;第四輯則為“文論”或雜文;第五輯是一組“散文”,其中既有游記、回憶錄,也有幾篇悼文;最后的第六輯是若干“評論”,包括詩評、劇評、文評以及6封書信。就我個人閱讀后的直觀、直感,應當說,從《愛得深沉》中,不難發現作者在階級自覺意識上體現出明顯的進步和跨越:既有對各種文體駕馭的自覺意識的拓展和提升,對作為新世紀新型先進階級的自覺意識的拓展和提升,更有對努力朝著“新型工人階級文化戰士”的宏遠目標的自覺意識的拓展和提升。
愛與美是一對名副其實的親姊妹。在古代希臘和羅馬的神話中,阿佛洛狄忒和維納斯都同時是集“美”與“愛”于一體的化身。她們是人間愛情和美麗的賜予者,同時也是美與愛的神化的象征。的確,在起起伏伏的愛河中,總是離不開美的倩影;而在對美的渴望和追求里,也就產生出熱烈的、抑止不住的愛。英國偉大作家莎士比亞說:“即使用十二把鎖,把‘美’牢牢地鎖在密室,‘愛’也照舊能把鎖個個打開而斬關直入。”從王學忠《愛得深沉》這部新著來看,正是人類最美的理想境界,才激發和充實著大愛;而愛的偉大和深沉,歸根結底也源自人類社會展現的最崇高的美的景觀。
一
王學忠最初只是寫詩,沒有寫過論文。從20世紀末開始,他才撰寫和發表發言稿、回憶錄、雜文。在2001年出版的《挑戰命運》里,收入了他的幾篇散文。2014年出版的《我知道風兒朝哪個方向吹》(散文、文論卷)是他的第一部文論集;而現在將要出版的《愛得深沉》,則是一部匯集眾多文體的詩文合集。這本新書以《愛得深沉》為名,據作者的解說,這源于艾青的《我愛這土地》中的詩句:“為什么我眼里常含淚水?因為對這土地愛的深沉……”20世紀80年代初,艾青曾為河南安陽的詩刊《詩人》題寫刊名,還親筆題詞:“思想再深、再高,語言要淺顯。”正是在這個刊物上,王學忠發表了他的組詩《春天的早晨》。王學忠在自己的文論中,多次提到“革命詩人”艾青。他不止一次地贊賞艾青的《手推車》形象,認為它“發出了那個時代人民痛苦的悲鳴”“用白描手法寫出了那個時代勞動人民遭受的苦難”。他一再重復艾青《詩論》中的名言:“詩,是最高的理論和宣言”。不難看出,他始終是以艾青等老一輩革命家、文藝家為仰慕的偶像和學習的榜樣的。
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至于所謂‘人類之愛’,自從人類分化成為階級以后,就沒有過這種統一的愛。過去的一切統治階級喜歡提倡這個東西,許多所謂圣人賢人也喜歡提倡這個東西,但是無論誰都沒有真正實行過,因為它在階級社會里是不可能實行的。”“真正的人類之愛是會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滅了階級之后。”由此可見,深沉的愛不是抽象的、超階級的“愛的囈語”,而是一種緊扣時代脈搏的對祖國、對人民、對本階級無私的愛、無限的愛、無邊的愛。這才是神圣的愛、崇高的愛、偉大的愛、廣袤的愛、“真正的人類之愛”,也就是大愛、純愛、真愛和深愛。
從15歲開始就正式成為工人階級一分子的王學忠,深知大愛、純愛、真愛、深愛之要義。他旗幟鮮明、立場堅定,愛憎分明、嫉惡如仇,始終保持著先進階級的革命本色和戰斗精神。他來自社會的底層,親身感受和體驗到勞動人民的勤勞、樸實、勇敢、堅韌,同時也親歷過他們的艱辛和磨難。盡管最初他“不知為何寫詩,也不知寫到何時”(《流韻的土地》),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幾十個春夏秋冬過去,在與繆斯的熱戀中,卻堅持不懈、沒有停筆。隨著他成為下崗工人大軍的一員,隨著他從幼年、青年到中年,隨著他的生兒育女,隨著他本能的、質樸的愛和“一次次咬牙攥拳的不服”和“厭惡的鄙視”(《我嫉妒》),上千首詩歌源源不斷地涌出,10余本詩集陸續問世。不僅如此,他的理念越來越明確,他的視野越來越開闊,他的思考越來越深沉,他的目標也就越來越清晰。他不倦地學習、不停地前行、不斷地跨越,從“工人階級的本能”自發地愛詩、讀詩、寫詩,到自覺地以詩“作槍、作戟/書寫可歌可泣的時代/家國大事”,肩負起新世紀的新使命,實現了人生道路的飛躍和質變,這部《愛得深沉》就是最新的明證。
自發與自覺是一對相互對應的范疇,標志著人類對社會活動的意義是否理解以及理解的程度。列寧曾經多次強調必須反對無產階級的自發性,提倡自覺性,并善于和樂于把自發性提高到自覺性。他告誡:如果僅僅止步于所謂“工人階級的本能”和“對自發性的崇拜”,那就根本無法自動達到對自身與現存秩序之間關系的正確認識。他還進一步指出:“對工人運動自發性的任何崇拜和對‘自覺成分’的作用即社會民主黨的作用的任何輕視,完全不管輕視者自己愿意與否,都是加強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對于工人的影響。”(《列寧選集》第1卷,1972年版,第254頁)21世紀的新型工人階級,從總體上來看,應當是有文化、有知識、有經驗、有覺悟的社會最先進的階級,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的火車頭”。王學忠和以他為代表的這個群體的可貴和可敬之處,就在于不滿足于已有的 “底層詩人”“草根詩人”“地攤詩人”“打工詩人”等一大串的桂冠,而具有“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大胸懷”“大氣魄”“將自己的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安危系在一起”,由個人的“小我”飛越到“大我”的更高境界;而只有無與倫比的“大我”,才會有無私無畏的“大愛”。
《愛得深沉》詩文集是本小書,字數不多、篇幅不大,雖然仍有個別篇章還可加工和修飾,但從總體上來看,內容豐富,有相當濃厚的含金量和正能量。這多少說明,作者已不像少年時一味地去追求產品數量(“只圖多”),而是更加看重作品的質量和能量。更為重要的是,他已不滿足過去以單一的詩歌形式來抒發和表達自己的感情、意愿和所思所想所為,而是試圖駕馭各種不同的文體。在這個最明顯的表象中,卻潛流著作者從單純詩人向多面的新型工人階級文化戰士提升的宏偉抱負。
二
《愛的深沉》前三輯的詩篇,既保留和延續了作者原有的詩風、詩味,又有所延伸和拓展。以《小詩·大詩》的“組詩”為例,他用敏銳的判斷力和真誠直率的語句,歌頌和贊美著“大詩”和“真詩人”,鄙夷和嘲諷一切“小詩”和“偽詩人”。在他的眼里,“大詩寫的是人字/如同攝像機/不作假、不弄虛/真真切切/記錄一個時代/民情、民意//血與火的較量/兩個階級的博弈/是非曲直/呼喚平均、平等/使真善美弘揚/假惡丑止”;而“小詩寫的是自己/私情、私欲/自家灶里的柴/鍋里的米/老婆、孩子身上衣/皆一己私利”。他一再強調:“真詩人/是繆斯與戰士的結合體/用平仄文字/作槍、作戟/書寫可歌可泣的時代/家國大事//真詩人/用真情寫詩/良知寫詩/視金錢如糞土/權力如糞土/充滿正氣、骨氣”//“真詩人/為人民寫詩/為那個創造了/精神與物質財富/卻把權力交給他人管理/憑力氣撈飯吃的群體寫詩“//“真詩人/面對人民的苦難/淚滴、血滴/從不背過臉去/像屈原‘哀民生之多艱’/甚至愧恨而詩//真詩人/也許一生潦倒/顛沛流離/卻精神富有/腰板挺得/比山峰還直//真詩人/站在社會風口寫詩/跳入時代大潮寫詩/披棘斬棘/每一朵浪花/都是鏗鏘的詩句……”連續六個對“什么是真詩人”的回答,鏗鏘有力,響遏行云,是作者發自肺腑的“詩的宣言”,也是對自身忠于神圣使命的誓言。它們與80年前艾青在《我愛這土地》中高喊的那樣:“假如我是一只鳥/我也應該用嘶啞的喉嚨歌唱/這被暴風雨所打擊著的土地/這永遠洶涌著我們悲憤的河流/這永無止息地吹刮著的激怒的風/那來自林間無比溫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連羽毛也腐爛在土地里面”“為什么我眼里常含淚水/因為對這土地愛的深沉……”無論從內在精神還是詩語表達上,都是一脈相承、息息相聯,前后呼應、心有靈犀。
王學忠曾經多次在詩中吟詠過“愛”,例如他在“組詩”《愛的思索》中曾經寫道:“愛是情感、情欲/也是本能/像種子埋進土里/到了春天/便會蓬勃一樹蔥綠”。這樣的描述,固然不失為某種“詩的思索”或“詩的意象”,可多多少少還顯得表層、空泛、一般化。因此,作者自己也認為:它是“需要科學家/認真揭秘的/一個課題”。其實,按照心理學的解說(“揭秘”),“愛”不過是一種復雜的情感活動,是“主體的強烈的、緊張的相對穩定的感情”,以及“情緒洋溢的積極態度的高級階段,這種態度可以使人在其他人當中挑選出他的客體,并把這個客體安放到主體的生活需要和興趣的中心(愛祖國、愛母親、愛兒童、愛音樂等)”“盡管生理的需要也是愛的情感的產生和維持的前提,但由于在人的個性中生物性的東西被取消,并轉變為社會的東西,愛在心理學對自己的親切描述中是受社會歷史制約的感情。”(彼德羅夫斯基、雅羅舍夫斯基主編:《心理學辭典》,東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3頁)因此,盡管中外古今無數的思想家、哲學家、文藝家對這個“永恒的主題”,做過千千萬萬種各自不同的描述和解答,可根據現代科學的剖析,它并非高深莫測和難以揣摩。
還是毛澤東說得好,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存在決定意識,“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的客觀現實決定我們的思想感情”來看,“就說愛吧,在階級社會里,也只有階級的愛,但是這些同志卻要追求什么超階級的愛,抽象的愛,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這是表明這些同志是受了資產階級的很深的影響。應該很徹底地清算這種影響,很虛心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他還說:文藝工作者應該學習文藝創作,這是對的,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切革命者都應該學習的科學,文藝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藝工作者要學習社會,這就是說,要研究社會上的各個階級,研究它們的相互關系和各自狀況,研究它們的面貌和它們的心理。只有把這些弄清楚了,我們的文藝才能有豐富的內容和正確的方向。
我個人認為,目前思想界、理論界、文藝界之所以出現種種的思想混亂和奇談怪論,例如某些人公開地大肆宣揚“一切從愛出發”“追求什么超階級的愛,抽象的愛,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甚至還將它們作為“名正言順”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其根本的原因就是有意無意地忘記和拋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因而導致唯心主義猖獗、形而上學泛濫。70多年前毛澤東在延安號召文藝界和全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知識和學習社會的要求,于今不僅從未過時,反而似乎更具現實性、針對性、必要性。
當然,人類的愛是一個相當復雜的情感和心理活動,提倡“大愛”“深愛”“階級的愛”“同志之愛”,并非反對和否定一切親情之愛、友情之愛、男女之愛。這些現實生活中出現的具體的、身邊的、自然而然的愛,質樸的愛,在尚未受到社會環境的污染和毒化時,無疑是大愛的日常體現和組成部分。“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聲也,有同聽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人的個性中生物性東西”,總是自然而然先天地存在的,不能被抹煞;只是人不同于任何動物的是: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因而人的愛“是受社會歷史制約的感情”。所以,魯迅才說:“自然‘喜怒哀樂,人之情也’,然而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檢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饑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像闊的人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二心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人類之愛的共性和個性是矛盾、對立、轉化的統一體,必須以唯物辯證法的觀點才能正確地認識、辨別和對待。《愛得深沉》中收入的《我的父親》一詩,深深地表達出作者對“一位平凡的父親/老實、本分/用艱辛、苦辛/堅強、堅忍/和母親一起/把他們的眾多兒女/養大成人”的兒女之情。而《藏好》《聽雨》《有一個人》《有一種情愫》《上善若水》《相約》《中秋,月下》《下雪的冬季》,等等,都從不同的視角、以不同的意象,親切、真實、動人地傾訴并感悟著親情、戀情、友情的真誠和純樸。王學忠能夠領會并在創作中實際運用毛澤東所說的:“各個階級有各個階級的美,各個階級也有共同的美。”他在《距離》這首短詩中感嘆:“距離有兩說/可產生朦朧美/亦可造成誤會和隔膜/使愛分離/讓心與心結合”。也許,這就是詩人對愛與美相依相隨理解的哲理。
值得慶幸和欣慰的是,僅上過5年小學的“下崗工人”王學忠,始終在一邊創作一邊努力學習,幾十年如一日地不斷地在學習中創作,在實踐中學習。在一大批老革命家的幫助和鼓勵下,他從閱讀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到進一步努力研讀和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經典著作。正是從這些理論著作中,他才懂得作為工人階級一員的歷史使命,他才從自發的“生命本位主義”者轉變為自覺的新型無產階級的戰士,他才在《不忘初心》中開宗明義地唱出:“水有源/木有本/馬克思主義/是共產黨人的魂”,他才能意識到“初心是一種承諾/也是責任/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無產者做天下的主人/把果實和土地/生產工具和勞動產品/歸還人民//不忘初心/就是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恨/資本主義把人逼成鬼/社會主義使鬼變成人/防止兩極分化/再現白毛女、黃世仁”。他才會“站在左權將軍遺像前”,不能不“心潮逐浪翻/如鋼錐戮心肝”,并自然而然地感嘆:“鋼鐵的炮彈不可怕/糖彈最危險……”
而在《桂林雜感》組詩的《大榕樹》中,我們讀到:“傲然兀立/遮天蔽日/1400多歲高齡/見證了中華民族風雨歷史/天災、人禍/戰爭、瘟疫/倒下的是歲月/鐫刻滄桑年輪的/是堅韌、不屈/你站的正,立的直/身邊的兒女/也站的正,立的直……”以桂林大榕樹的景觀和自然美,蘊含著中華民族非凡的精神氣質和崇高的精神境界。王學忠的大愛、深沉的愛,既是無私的博愛,是對工農兵的摯愛、是對廣大勞動人民的真誠的愛、是“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的光風霽月的愛;又是對自然美、社會美和藝術美的高度再現和審視。
三
“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真、善、美與假、惡、丑總是相互對立并在一定條件下轉化的統一體。有美才有愛,有丑必有恨,有光前裕后的大愛,就會有深惡痛絕、切齒腐心般的恨。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不能愛敵人,不能愛社會的丑惡現象,我們的目的是消滅這些東西。”在王學忠的創作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作品,屬于時事詩、政治詩、諷刺詩,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在他生存和經歷的現實生活中,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出現和泛濫著形形色色、未曾意料的“社會丑惡現象”,引起了他的困惑、質疑和憤懣,不由自主地要用自己的筆,去揭露、批判、驅趕和消滅這些社會的垃圾和毒瘤。在這部《愛的深沉》的新作中,第一輯的20余首詩篇,便大多是這類“時事詩”“新聞詩”或“政治詩”。
對王學忠來說,也許他的愛過于深沉,便對一切假、惡、丑現象恨之入骨、無法容忍。在他的創作中,從一開始寫詩,就出現過少量的時事詩、新聞詩、政治詩。等到他的眼界擴大到社會的更深層面,這類的作品也逐漸增多。在《地火》一書里,就有相當多描繪社會萬象的時事篇章;而在幾年前出版的《我知道風兒朝哪個方向吹》(詩歌卷)中,這類詩則占了絕大部分,全書共3輯,僅第2輯中的部分篇章不屬這種類型。
《愛得深沉》第一輯中除少數幾篇例外,其他都可歸于此類。例如《螻蟻之死》(組詩),是根據媒體報道的一起極為悲慘的事件寫的系列詩章。2016年8月24日下午,甘肅省康樂縣景古鎮阿姑村山老爺彎社28歲村婦楊改蘭,不堪貧困,用農藥殺死了四個親生孩子(其中有一對雙胞胎姐弟)和自己。在鎮上豬場打工的丈夫李克英趕來,將一家五口葬埋后,也喝農藥自殺……王學忠對這個農民6口之家的不幸遭遇和不正常的自盡自戕,表現出強烈的抑制不住的同情和激憤,一口氣寫下《少婦楊改蘭》《丈夫李克英》《大女兒8歲》《雙胞胎姐弟》《3歲小女兒》等五首組詩,悲憤填膺地呼號:“‘虎不食子’/你卻害死四個親生孩子/而后又害了自己/讓人痛心不已/痛恨不已/恨你!用撲簌簌的淚恨你/攥緊的拳恨你/恨你!恨你/痛定思痛/只能用無奈的詩思/探尋你28載/心路軌跡”。再如,作者對吉林省白山市某私企,為殺一儆百,強迫十余名未完成銷售任務的員工,在鬧市區雙膝跪地,沿著人行街道爬行,引來眾多市民圍觀……面對這樣的惡行鬧劇,深感痛心和憤憤不平,他仰天長嘆、痛心疾首:“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不忍目睹呀/一個偉大的階級/才站起來不久/又跪地爬行”(《他們流淚爬行》)。還有類似于“賣妻救女”(《真不知該勸你還是訓你》)、對“惡意討薪”民工的公開審判 (《像是在做夢》和《討薪民工麗麗》) 等社會現象的疑惑和拷問,都在他的詩中屢屢出現。
那么,人們要問,這些本來不該發生在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反常社會異象、怪象,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幾乎成為“新常態”呢?原因當然很多也很復雜,需要具體地、細致地分析和研究,不能只看偶然現象,以個例個案一概而論。王學忠經過長期學習和思考,認真地、嚴肅地回答了這個問題:私有制是萬惡之源!他從長春長生公司生產假狂犬疫苗的個案中,進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審視和剖析,最終得出了這樣一個顛撲不破的普遍性的結論:“謊話說得再美、再多/嘴皮子說破/扮成美女還是蛇/把真理關進黑屋子里/依然光芒四射/‘私有制是萬惡之源’/乃世間真諦/顛撲不破”。在他看來,“紅豆生在南方/胡楊是沙漠的脊梁/蒼蠅不叮無縫的蛋/資本主義社會/是滋生制假、售假的溫床/什么樣的植物/適應什么樣的土壤/芽孢菌在120度高溫下/才會死亡……”作者以詩的語句,從自然界的規律性中,對比和領悟到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不禁使我想到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揭示的原理:“現代資產階級的私有制是建立在階級對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剝削上面的產品生產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備的表現。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無產者只有廢除自己的現存的占有方式,從而廢除全部現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會生產力。無產者沒有什么自己的東西必須加以保護,他們必須摧毀至今保護和保障私有財產的一切。”應當說,王學忠的“大愛”和“大恨”的根基,就在這里。
我在《雜談雜文美學的五性》(《美與時代》2017年第1期)一文中,曾經提出過自己對現代雜文美學的粗淺理解,認為優秀的雜文品性至少具有包容性、幽默性、諷喻性、喜劇性和典型性。其實,我對雜文從來沒有進行過專門研究,至今也未寫過一篇嚴格意義上的雜文。但從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和魯迅的經典范文中,對現代雜文文體產生了鐘愛,感到這樣的“匕首”和“投槍”,實在不可缺少。在我看來,詩人王學忠把筆觸伸向現代雜文領域,也是完全可以理解和自然而然的。一是他早就感到僅僅用詩歌來描繪社會萬象和抒發自己的愛和恨,已經遠遠不夠和難于充分表達;二是他熟悉且能駕馭這種文體,因為諷刺詩和雜文同具某些共性。《愛得深沉》第四輯收入的12篇“文論”,是他初步進行的成功嘗試。
《簡論信仰》這篇短文,是作者在鄭州參加了一個由中國作協和省作協組織為期三天的研討會,兩級協會負責人講到當下國民及作家的信仰缺失,并大聲呼吁信仰。然而,會議的幾個負責人卻輪番宣揚的是孔孟的儒、老莊的道、釋迦牟尼的佛,還有的講了西方國家的耶穌基督。王學忠深有所感,他不免迷惑并提出疑問:“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作家究竟應該信仰什么?把什么樣的信仰寫進自己的作品里?”他的提問是正當的、合理的,而且抓住了目前文藝界、思想界、理論界普遍存在的一種亂象,那就是把信仰抽象化、一般化、非意識形態化,不問它的正確性、合理性、科學性和階級性。因此,社會上迷信成風、邪教屢現,而有的黨員干部公開燒香拜佛,搞祭奠、“埋鎮物”“補風水”,也就見怪不怪、習以為常了。
不得不承認,信仰是多種多樣的,《國際歌》里唱道:“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這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對現實世界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正確的、科學的、深信不疑的堅定信念。一切唯心主義的什么“三世因果,六道輪回,四攝六度,苦集滅道”“善人將進入天國獲得永生,惡人將被拋入地獄受永罪”以及“信安拉、信天使、信經典、信先知、信后世、信前定”等,都不過“從一開始就是產生于實際存在的生產力的超驗的意識”,是顛倒的、歪曲的現實;而在有階級的社會里,它們總是被剝削階級所利用,作為維護自己統治地位的工具,成為欺騙、毒化和麻醉人民群眾的鴉片。共產黨人的信仰只能是科學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徹底的唯物主義的無神論,絕不能在兩種對立的宇宙觀、世界觀、人生觀上搖擺或后退,忘記自己的使命與職責,這與尊重不同的文明和“宗教信仰自由”,完全是兩碼事。
王學忠曾在《永不投降》的詩中寫道:“信仰是漆黑夜皎潔的月亮/茫茫云海噴薄欲出的朝陽/一個民族不能沒有信仰/信仰——/凝聚著‘力拔山兮氣蓋世的力量’//我們的信仰是馬列主義/為了普天下窮苦人翻身解放/幸福可丟棄、生命不懼亡/化作——/巴士底監獄的血與火/南昌城頭的刀和槍”。是的,偉大的蘇聯作家高爾基說:“不能失去信仰,不能因為懷疑而毀滅那偉大的愛。”信仰是“偉大的愛”,有了堅忍不拔的崇高信仰,才有深厚的大愛和疾惡如仇的大恨。
這一輯中的其他幾篇短文,許多都是針對當前詩歌界、文藝界和媒體出現甚至泛濫的奇談怪論、奇形怪狀,提出不同的看法或批評。例如,有人鼓吹“詩歌既不會喪國,更不能興國,從她誕生之日起,就是一種娛樂,一種玩兒。切不可強人所難,讓其纖弱的身子承載太多”(《也說風花雪月》)。有的宣揚“中國文化就是地主文化,而儒家維持的價值觀就是朝廷、地主、農民之間存在的一種契約關系。這種契約關系,維系和穩定了社會的和諧文明。后來,隨著地主階級的消滅,中國文化的內在生命就停止了。”((《精英文人與地主文化》))有的“把詩歌當作謀取個人私利的工具。”(《低俗與馬屁》)有的“人為地搞成一個個小圈子,‘圈外無人賞,圈內自鼓掌’,并自詡某某‘流派’”(《圈子與流派》)。照我看來,這些怪象和亂象,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可以歸結到對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動搖、誤植、異變和缺失中來。不從根本上去正本清源、撥亂反正,這類謬說、謬論、謬誤還會持續不斷地滋生、滋長,成為病毒,污染環境,戕害心靈。
要想寫好雜文,首先必須像毛澤東要求的那樣,運用辯證法,力避片面性,更要在文字上下狠功夫。王學忠的雜文寫作,還剛剛起步。我個人覺得,他在雜文美學的包容性、幽默性、諷喻性、喜劇性和典型性的把握上,都需要更加努力地學習和實踐,繼續不斷地邊學習邊創作,邊創作邊學習。在學習經典和優秀雜文的過程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寫作技巧,竭力避免不必要的各種重復:主題重復、內容重復、語句重復、引文重復;雜文寫作如同其他類型的文藝創作一樣,具有獨特的個性美,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作品,不會贏得讀者的喜愛。
四
《愛得深沉》第五輯收錄的是作者的10余篇“散文”,這里既有游記、悼文,也有對前輩或同輩親朋好友的懷念和答謝文。《閩南采風》記述的就是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邀請作者前往福建參加一次采風活動的前前后后過程,由《與記書兄同行》《鼓浪嶼一日》《登武夷山》《在飛機上》4篇游記組合。王學忠有幸參加這次活動,使他能初次到福建各地參觀、游覽,大大開闊了眼界,增長了見識。更為重要的是,在這次活動中,他結識了許多中外作家、藝術家,都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從河南乘火車啟程初識邯鄲作家張記書,一路交談到廈門,到與采風團團長澳大利亞作家黃心水一行16人,登鼓浪嶼,飛武夷山,直到再飛回廈門,作者感受到“大開眼界,學習了不少知識。這些知識不僅僅是文學、文化、歷史,還有政治、經濟。”因此,他記下的不僅是沿途秀麗的自然美景,更多的是與同行作家的交流。從這組游記中可以發現,王學忠看重的不是游山玩水,而是利用一切難得的機遇,盡可能地學習社會。
另一篇游記《流連忘返京娘湖》,描繪的同樣是這個世界華文作家交流會到太行山脈腹地邯鄲市的京娘湖的集體活動。作者在這篇散文中,雖然為景區的高山流水、碧波浩淼、峭壁懸崖、鳥語花香等景色所陶醉,但更被這里的“趙匡胤千里送京娘”的歷史傳說所感動。由這個見義勇為的故事,使他聯想到當下惡劣的社會風氣,想起一些學術精英的奇談怪論,說什么“‘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是絕無僅有的,是騙人。”“雷鋒是政治家編造出來的政治托兒,真實的雷鋒是大腦炎后遺癥病人。”甚至高調宣揚“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等剝削階級沒落的人生觀。于是,他積極地建議:“如果我們的政府部門、社會團體多組織幾次京娘湖旅游,聽一聽‘趙匡胤千里送京娘的故事’,惡劣的社會風氣一定會得到改觀。”不過,如果沒有從根本上(思想上、理論上、觀念上)去端正并鏟除那些歪風邪氣、荒謬絕倫,單靠多組織旅游來改變惡劣社會風氣,這恐怕只是作者主觀的善意渴求和一廂情愿而已。
《愛得深沉》第五輯里有多篇對革命老前輩的回憶,如《痛心的懊悔與遺憾——深切懷念李成瑞老》一文,詳細記錄和描述了自己與一位德高望重革命家之間的深情厚誼。這位近百歲的老戰士,直到臨終還一如既往地關心和注視著國家和世界的前途和命運,不愧為“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新世紀的楷模。再如《關愛與呼喊》中的一位老編輯、“為他人作嫁衣裳的伯樂”胡德培,在編輯的崗位上辛勤工作40余年如一日,發掘和扶助過許多著名作家和作品,至今仍淡泊寧靜地當一個普普通通的“文學紅娘”。對王學忠這樣素不相識、初出茅廬的作者,進行不斷地鼓勵、指導和支持,無私地奉獻著人格魅力,令人肅然起敬。還有那篇關于一位不幸早逝的同年女詩友畢愛青的回憶,作者似乎是含淚寫出的。他對這位“詩癡命苦”、性格開朗、一見如故、“生活在社會最底層靠辛苦撈飯的打工妹”,充滿了憐憫和同情,表達了深深的階級情誼。(《詩癡命苦的閑云沾衣》)
匯集到《愛得深沉》最后一輯是10余篇評論文章,既有詩評、劇評,也有文評,它們可以看作是作者對革命文藝經典的學習心得和認真解讀。在《工人詩人鮑狄埃與深圳打工詩歌》一文中,作者高度評價《國際歌》作者鮑狄埃作為工人詩人的“主體意識”,認為這種意識“像強勁、猛烈的春潮撞擊著心房,讓人信心滿懷”。而對于某些人竭力推薦和吹噓的深圳“打工詩人”的部分詩作,則感到僅有“嘆息、絕望、倒下”等的情緒,沒有突出工人階級應有的“主體意識”。《踏著時代腳步,抒發人民情感——賞析馬雅可夫斯基長詩〈列寧〉》,用工人階級詩人的眼光,細致地分析了《列寧》這篇長詩的主旨和要義,認為“他的詩有著明確的政治立場,那就是始終站在人民一邊,揭露資產階級的虛偽、奸詐和狠毒,謳歌勞動人民的勤勞與智慧,謳歌一切權力歸人民的社會主義新國家”。《大眾的壯美詩行,堅定的共產信仰——簡論賀敬之的詩》和《永恒的經典,思想的光芒——電影《白毛女》歌詞賞析》兩篇評文,以“寫出了許多經典作品,并影響了幾代人”的賀敬之的創作為例,反思和抨擊了自社會“轉型”以來,某些人大肆宣揚和鼓吹“文藝市場化”“多元化”“娛樂至上”“與世界接軌”等背離和拋棄“二為”“二百”方針帶來的污泥濁水、烏煙瘴氣。在讀過七卷本《志昂存稿選編》后,作者滿懷對革命前輩的仰慕和崇敬,寫下了《赤心如昨,詩心似火 ——簡論陳志昂作品》的書評,深感這“是一次知識和藝術的學習,更是思想的陶冶,對當下每一個沉浸在夢中的人們是一種催醒劑,使其不再懵懵懂懂而猛然警醒。”這些“文論”都貫穿著一條紅線,那就是推崇和高揚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大愛大恨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從2016年開始,王學忠擔任《工農文學》主編,這是份綜合性文學刊物,至今已出版7期。它的內容愈來愈豐富,思想性和藝術性完美結合的作品愈來愈多,讀者的范圍愈來愈廣。這份刊物“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為指導思想,遵循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引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人民大眾服務’的創作道路,堅持用真情實感記錄生活,工農寫、寫工農,寫那些工作在田間、地頭、車間流血淌汗的勞動者,寫他們的生存狀態和精神訴求。”從今年第2期起,它又有了自己的公眾號,跨進了網絡空間,受到廣大工農讀者的好評。有的讀者評說,《工農文學》“思想性戰斗性強,敢于堅持真理,鞭笞反動落后與腐朽,在如林的文學期刊中獨樹一幟、無可取代。中國需要這樣的刊物,人民需要這樣的刊物!”由此可見,王學忠的活動領域,已不局限于個人的寫詩作文,而是擴展到團結和動員所有胸懷大愛的志同道合者,共同為著實現解放全人類的宏偉理想進行“新的長征”。
“世紀巨人”毛澤東主席在《實踐論》中高度概括和總結說:“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人類社會的進步和發展,總是一個從自發到自覺逐步深入的過程,而先進階級的內在自我意識的發現和提升,更是歷史向前邁進和跨越的基本要素和條件。只有自覺地認識和掌握客觀世界的規律性,人們才能在實踐活動中適應、利用和改造自然界和社會,同時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只有具有高度的階級意識,21世紀新型工人階級才能有廣闊的政治眼界、堅韌革命的毅力、遠大宏偉的目標、一往無前的戰斗精神和高超的組織領導才能。我個人覺得,《愛的深沉》的作者和以他為代表的群體,已開始有意識地在朝著這個方向穩步邁進。
《愛得深沉》和《工農文學》標志著王學忠已自覺地勇于擔當新型工人階級文化戰士這一角色,他走上了人生輝煌道路的新臺階。但這條“取經”長途雖活靈活現地呈現在眼前,卻并不筆直和平坦:頭上會有閃電雷鳴、暴風驟雨,腳下說不定荊棘叢生、坎坷曲折,中途難免還有空氣中的“十面霾伏”的迷霧,以及遭遇“現代化”“全球化”“信息化”的妖魔鬼怪、魑魅魍魎,這些都是非常嚴峻的挑戰和考驗。我建議,王學忠們都好好地讀一讀《不怕鬼的故事》那本書,認真學習、領會和運用“不怕鬼”“戰勝鬼”的精神,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努力做一個21世紀“智勇雙全”的開路人、奠基人、掘墓人。因為沒有堅定的信念、堅韌的毅力、敏銳的判斷力、識別力和應變力,就無法識破和消除眼前的重重迷霧和形形色色的現代“白骨精”。因此,我還是再次重復魏巍對王學忠的勉勵:“還要更加提高階級自覺,還要更好地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還要更好地理解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
王學忠朝著大愛無疆的新征途又跨越了一大步,我衷心地祝愿他堅持到底、永不放棄;同時也希望看到有更多的人,與他結伴而行!
美與愛是一對親姐妹,她們相偎相依、形影不離。正因為“愛得深沉”,才會有藝術美的再現和創造。
大愛正是打開大美的萬能鎖,心懷大愛,就會具有“音樂的耳朵和形式美的眼睛”,就會創作出世間最感人動聽的樂章和最美最新的畫卷。
美和愛相伴而行,大美吸引和滋潤著大愛,大愛為到達大美的目的地而永不停息地前行!
作者簡介:涂武生,筆名涂涂,1959年畢業于莫斯科大學哲學系美學專業。歷任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實習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文藝理論與批評》主編,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