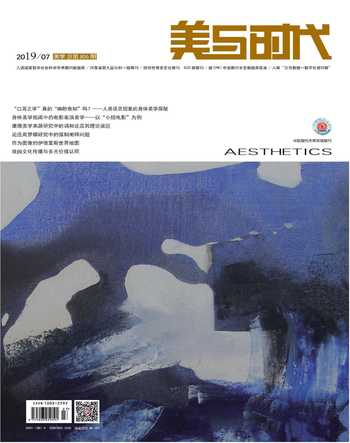身體美學視閾中的電影表演美學
摘? 要:“文”是身體之蹤跡,身體是“文”的作者,身體在創作過程中表現自己。表演是藝術化的身體活動,是以身體為核心的藝術門類。近年大陸上映的“小妞電影”里,女演員發揮自己的身體特性,塑造了眾多形象鮮明的人物形象。從身體美學視閾看“小妞電影”,不但能看到女性身體作為“物”之內涵,更能看到現代社會女性解放的趨勢和目的。
關鍵詞:身體美學;表演;小妞電影;女性
近年來,“小妞電影”異軍突起,形成了一種引人深思的文化現象。那么,它為何會在眾聲喧嘩的時代里脫穎而出?是什么擊中了當代觀眾的神經?從身體美學的角度看,它可能具有審美主體和審美客體的雙重優勢,而這正是它崛起的深層原因。
一、身體與表演:“小妞電影”的美學基礎
進入21世紀以后,世界美學研究出現了明晰的身體轉向。作為對主客二分美學論的反思和超越,身體美學關注個體,關注作為主體的身體。這種變化深刻地影響了電影美學,德勒茲等西方思想家嘗試建立身體電影學。對于電影表演來說,此類嘗試具有重要意義。演員是帶有主觀能動性的身體,表演是身體的實踐。對于表演來講,身體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身體是演員,是演員表演的起點和歸宿,是具有能動性的審美主體;另一方面,身體是角色,是觀眾看到的人物形象,是觀眾眼中的審美客體。在電影表演中,作為演員的主體和作為角色的客體不分彼此,展現為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角色身上灌注了演員的主觀能動性,是演員身體的自我設計和展現。電影表演是審美主體發揮主觀能動性塑造審美客體的過程,是演員之間的身體交互過程,這種交互是在劇本的設定和攝影機的拍攝中進行的。通過劇本設計和鏡頭運動,演員的身體在環境中呈現出獨特的藝術形象,劇本、鏡頭、聲音、背景給演員敞開自己的藝術個性提供場域。演員之間的身體交往彼此成就,表演成為交往中的主體狂歡,無論主角配角,都在與環境及其他身體的交互中展現自己,形成自己獨有的美學特質。
從身體美學的視閾看,電影表演美學的核心在于演員作為主體性身體對自我形象的觀注和設想,表演中的身體是言說的主體,這個主體看起來是滿足劇本設定,但實際上是演員這個審美主體在創造,在按照身體自我設計創造符合其要求的審美形象。“身體在創造世界時也在創造自身,其所有活動都最終落實為身體的自我創造。它內蘊感性和理性、欲望和理想、細小計劃和宏大藍圖,是自我設計著的目的性存在。”[1]77由于每個演員的身體基礎和身體設計不同,造就了每個演員的表演美學風格的相異。明白了這一點以后,我們或許會找到分析“小妞電影”的出發點。
“小妞電影”是一種起源于歐美的電影類型,其特點主要體現為三點:(一)主要觀眾是年輕的都市女性;(二)主要內容是都市女性的情感和人生故事;(三)主要風格體現為輕喜劇的電影類型風格。綜合來講,“小妞電影”“以女性為中心敘述者和主角,以幽默戲謔的方式討論現代年輕女性關注的問題”[2]。近年來,大陸的“小妞電影”發展迅速,不但在數量上,而且在質量上、票房上都呈現增長的趨勢,代表作如《失戀33天》《杜拉拉升職記》《女性公敵》《等風來》《與時尚同居》等。從身體美學的角度來看待“小妞電影”中的表演風格,我們就會發現一個越來越明顯的趨勢——“小妞電影”中的女性表演主體個性鮮明,塑造了杜拉拉、黃小仙等眾多經典人物形象,不但形成了獨特的女性表演美學風格,而且展現了新都市女性的整體風貌,對都市女性觀眾形成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
眾所周知,“小妞電影”的主要角色是都市年輕女性,從身體美學的角度看,電影中的角色的身體首先是審美主體,是演員自身,是具有主觀能動性的身體,是能夠自我設計和表現的主體;其次,這個身體是審美客體,是演員塑造的人物形象,是承擔吸引觀眾目光、滿足觀眾的窺視欲和模仿欲的角色。演員主體和角色客體統一在表演中,展現了電影表演美學的本質。“用現象學的術語來講,身體是世界的樞紐,是所有行動的原點和歸屬,是海德格爾所說的繁忙勞作的此在。沒有身體,就沒有屬人的世界,就沒有詩。離開了身體的行動、感知、思考,世界就無法獲得理解,詩學就不會獲得誕生的機緣。只有進入身體學的層面,詩學的視野才會豁然開朗。”[1]44電影表演美學只有進入到身體學的層面,其隱秘的特質才會被展現,關于身體和表演的一切隱秘才會敞開在觀眾的視野中。所以,對“小妞電影”中的女性身體表演進行分析,有助于我們從美學本質層面來把握電影表演美學的特質。
二、肉身性主體:“小妞電影”中的女性身體
在“小妞電影”中,作為主體的女性身體呈現出與男性身體不同的特質,其最主要的特點就是展現了“肉身性”的豐富內涵。按照列維納斯的觀點,“肉身性”指生存在與他者和世界交互關系中的身體,這個身體不是存在于判斷和概念中的身體,而是活生生的、占據空間和交往的身體[3]。在“小妞電影”中,作為主角,女性身體呈現出豐富的動姿,她們有S型的曲線,有長發、腮紅、眼影,有短裙、低胸裝和高跟鞋,有鎖骨、酒窩和搖曳動人的身姿。這些是她們和男性身體的不同之處,通過這些身體特質,她們牢牢占據“女性”的位置,在男性面前展現了女性“肉身性”特點,并藉此特點反映了身體的自我設計和追求。
以《女性公敵》的主角孫小美為例,她在休閑時段身著休閑裝,除了一頭長發,掩蓋了自己大部分女性特征,這是一種舒適狀態的身體特征,是身體的放松和休閑,展現了自然狀態下的女性身體,這時身體并不刻意展現自己的女性特質;當到了工作場所時,在身體的自我期許下,她將自己包裝成為一個職業女性,眼影、口紅和職業套裙,胸牌、文件夾和高跟鞋,這種身體形象部分掩蓋了女性特質,這是為了職業方便而設計的形象。工作中孫小美精明干練,一切都以工作為重;在被誤解并被指認為“狐貍精”時,孫小美再次改變了自己的形象,短裙、V領、貓步,步步搖曳生姿、臀波乳浪,完全凸顯了其女性特征,表現了身體對自我形象的設計和改變,其內在氣質也變得充滿魅惑,吸引了其他女性和男性的目光,展示了妖媚女性的氣場。這種改變來自于身體的內在需求——既然被認為是“狐貍精”,何不就按照這個標準來樹立形象呢?然而,無論形象如何變化,孫小美精致的容顏、凹凸有致的身材和百折不撓的氣質是其與世界打交道的基礎——正是有這樣的身體特征,她才能發揮所長,展現其肉身性的獨特魅力。
在另外一部“小妞電影”《杜拉拉升職記》里面,杜拉拉呈現了與《女人公敵》不一樣的肉身性特征——如果說孫小美是低胸、翹臀和狐媚的話,杜拉拉則是休閑、消瘦和干練。從身體特征上講,杜拉拉并不是一個前凸后翹、充滿魅惑的性感女子,而是一個氣質安靜、身材苗條的職業女性,其安靜的氣質和謹慎的行動,精確地還原了當下企業的職業女性特征。在家的時候,杜拉拉身著吊帶短褲,生活隨意,愛看書、愛美食,展現了一個放松的女性身體狀態;在職場的時候,杜拉拉則是一身職業套裝,身材修長,行動干練,并且在安靜的外表下隱藏了一個充滿活力的自我。
整部電影中,集中展現杜拉拉肉身性的橋段出現在她跟上司王偉的激情前后。而這次激情的展現是以兩具身體的距離變化為前提的,每具身體在世界中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都占據一定的位置,并且這個位置是獨一的,不能被兩具身體同時占領。從這一點講,身體都是孤獨的,身體可以無限接近,但并不能完全重合,身體之間距離的變化展示了身體之間關系的變化。杜拉拉和王偉只是普通上下級關系,在一次電梯停電的時候,患有幽閉恐懼癥的王偉抱住了杜拉拉的腿,身體的親密接觸為兩人的關系變化打下基礎。公司是不同身體打交道的公開場所,身體和身體之是有一定距離的,王偉和杜拉拉之間的關系和他們兩個人的身體距離一樣,都停留在彼此安全的范圍。但在公司組織的旅游中,由于環境的變化和酒精對身體的刺激,植根于工作場所的距離被消解,兩個人的身體接近,產生了曖昧的情感。最終,兩具身體越過了空間的距離,在臥室碰撞并部分重合在一起,在這個時刻,長期展現為職業形象的杜拉拉,也展示了其不為人知的性感,修長的脖頸、平坦的小腹,向王偉和觀眾闡釋了女性身體的性感側面。之后,兩個人的關系隨著身體的親密無間也呈現出水乳交融的特征。作為主角,杜拉拉的肉身性在工作、旅游、激情的時刻均有展現,把一個外表安靜、內心火熱的職業女性塑造的活靈活現,展示了女性身體豐富的肉身性內涵。
三、跨肉身性交往:女性身體的交互狂歡
在身體美學的視閾中,作為唯一主體的身體并不能自我成就,而需要在眾多身體的交往中成就自我,這種交往不但指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也指人與其他生命的交往,簡而言之,就是有機體與有機體的交往,這種交往是當今世界存在的模式,也是社會發展的需求。在電影表演中,身體之間的交互主要表現為跨肉身性的交往,“在有機體和有機體之間,跨肉身性的互動是生命之源,當然也是文學生產的動力。”[1]266通過主體間的交往,身體才得以呈現自我。從電影學角度來講,角色的塑造主要靠人物的動作、語言來展現,而動作、語言的主體是身體,發生過程是身體與身體的互動。表現在電影中,就是不同演員身體之間的跨肉身性交往,無論是對話、打架、戀愛,身體都在與其他身體打交道,演員的表演風格也在交往中被呈現。
在影片《等風來》中,倪妮扮演的程羽蒙是一個具有豐富肉身性內涵的女性身體,她的人物形象在開頭的三次表演中逐步清晰,這三次表演都是通過與其他身體的打交道完成的。第一個場景中,程羽蒙和一群富二代姑娘在餐廳里品評主廚大餐,她的穿著以休閑風為主,動作優雅,理性而冷靜。她對主廚的點評切中肯綮,展現了其專業性,對富二代保持一定距離而又不失禮貌,展現了風度和優雅,這些身體間的交往,迅速樹立起倪妮高貴而理性的角色形象。在第二個場景里,她拒絕了富二代的豪車相送,但上車后就要求司機開一段就盡快停車,展現了此身體的另外一個側面——貧窮拮據、斤斤計較。這跟第一場中強大的氣場形成鮮明對比,揭示出身體的困窘和對虛榮的期許。在第三個場景里,她不得不委屈自己的意愿而接受主編的安排,再次展示了角色的人生處境,同時也將其內心的矛盾予以展現。這三次表演一環扣一環,通過跟不同主體的交往,塑造了一個理性、優雅、專業,但又愛慕虛榮、生活困窘的角色形象,展現了肉身的豐富性。
在《失戀33天》中,白百合扮演的角色黃小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個體。她在故事的開始被男友拋棄,陷入到悲慘的境遇,在這樣的境遇中,身體展現出其最真實的面貌。黃小仙陷入了生活低潮,她悲傷、貪睡、貪吃、抑郁,身體處在一種無意識夢游狀態,這是真實的黃小仙,是其身體的自我放逐。過了一段時間后,通過與其他身體的交往,身體逐漸恢復了自我控制。跟老板大老王的交往中,黃小仙展現出作為女性下屬的擔憂害怕的特征,但是大老王身上類父的角色特質也給黃小仙展現“厄勒克特拉情結”提供了契機,于是她和大老王形成了亦對抗亦親密的奇怪關系,凸顯了黃小仙能夠隨機應變、順勢而為的性格特征。而和王小賤的交往,則將黃小仙細微的身體狀態完美展現,兩個人既像敵人,又似朋友,最終成為情侶,這是“親密敵人”的最好寫照。這種復雜的主體交往最能展現角色的性格特征,賦予人物形象豐富內涵和獨特魅力。
跨肉身性交往不僅為塑造人物形象提供契機,更主要的是展現了女性演員作為審美主體的特質,“身體這個術語所表達的是一種充滿生命和情感,感覺靈敏的身體,而不是一個缺乏生命和感覺的,單純的物質性肉體;而身體美學中的審美具有雙重功能,一是強調身體的知覺功能,二是強調其審美的各種運用,既用來使個體自我風格化,又用來欣賞其他自我和事物的審美特性。”[4]12相對男性身體來講,女性身體感覺更敏銳,更容易被觸動,也更感性,這是女性先天具有的身體優勢,也是“小妞電影”中完成主體性交往、塑造人物形象的關鍵。此外,特有的身體敏感也為女性角色的情緒展現提供了獨特優勢,“小妞電影”中的情感變化橋段多由女性演員主力完成,如《分手合約》中的幾次痛哭,《杜拉拉升職記》中一夜激情后的微妙心理變化等,女性演員由于天生的身體特點,呈現出細膩、情緒化等特有的女性表演美學風格。
四、身體的解放:“小妞電影”的社會意義
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男權主義的社會,女性身體及其表演往往成為一種文化資本和文化符號,女性的身體普遍被置于男權話語下,被男權社會制定的清規戒律所塑造。“女人,尤其是年輕貌美的女人,通常是藝術家喜愛描繪的對象。藝術家常常把女人描繪為尤物,誘惑著觀賞者的淫欲。藝術總是把身體之美頌揚為令人渴求之物,這種傾向常常導致夸張性的藝術風格,把身體描繪得安閑而優雅,從而傳播了欺騙性的身體意象。”[4]前言2跟男性的身體相比,女性的身體形象在女性人生和職業生涯中具有更重要的價值和作用。男性可以靠權力、財富、智慧等途徑展示自己的魅力,而男權社會中的女性身體卻并不具有這方面的優勢,她們更多依靠身體特征在社會中占據一席之地。在這種情況下,女性身體成為一種資本,是一種重要的社會交往符號。
這種傳統在“小妞電影”中被逐漸打破,在《杜拉拉升職記》《女性公敵》《完美超越》《與時尚同居》等電影中,女性身體超越了之前社會傳統中作為客體欣賞的“物”的位置,不再只是描述和觀賞的對象,更不是男性眼中的風景,而是彰顯了女性的主體意識和獨立思想,是活生生的、感覺靈敏的女性身體。身體是文化塑造的場所,是文化意識的載體,“充滿靈性的身體是我們感性欣賞和創造性自我提升的場所,身體美學關注這種意義的身體,批判性的研究我們體驗身體的方式,探討如何改良和培養我們的身體”[4]11。“小妞電影”反映了女性身體獨有的文化內涵,通過表演,演員不但讓觀眾看到了身體的獨特魅力,而且通過電影的無形傳播效應,角色的特質對受眾也起到了引導的作用。借助這個活生生的、靈敏的身體,“小妞電影”中的女主角發揮主觀能動性,及時接受信息,做出靈敏反映,推動自己的人生和周圍世界的改變。
“小妞電影”的意義,在于引領觀眾回歸身體及身體生存的生活世界,因為,“回到身體及其生活世界,意味著真正的返本歸源:第一、揭示物質、實踐、生產、世界、人、文學等范疇及其所指的原初關系;第二、重新闡釋‘詩模仿行動中的人’‘詩言志’‘文學是人學’等命題的深層內涵;第三、敞開語言游戲、權力、差異之類流行范疇對身體-生活世界的歸屬;第四、以身體的拓撲學消解諸如靈與肉、崇高與卑鄙、理想與欲望之間的虛假對立。”[1]96借助電影中的女性身體表演,“小妞電影”反映并引領了當下社會中女性的反抗和超越趨勢,為打破女性作為“物”“客體”“被看者”提供了轉變的契機,這勢必會為當代社會的身份轉換提供支持和動力。
參考文獻:
[1]王曉華.身體詩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2]鮮佳.“小妞電影”:定義、類型[J].當代電影,2012(5):46-51.
[3]黃瑜.由“隔絕”而“出離”——對列維納斯“肉身性”主體觀念的探討[J].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1):25-29.
[4]舒斯特曼.身體意識和身體美學[M].程相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作者簡介:朱鵬杰,博士、博士后,常州工學院教育與人文學院講師。研究方向:影視美學、生態批評、動畫電影、電影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