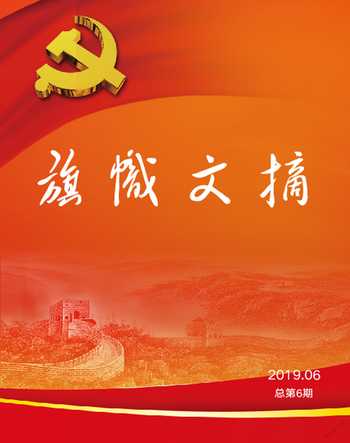不要當熟讀《道德經》的“失敗者”
《道德經》無疑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名著之一,它對中國的傳統哲學、科學、政治、宗教等都產生了深刻影響。同時,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道德經》也是除了《圣經》以外被譯成外國文字發行量最多的文化名著。正因如此,《道德經》早已成為廣受中外讀者推崇與重視的經典文本。那么,老子的《道德經》究竟是一本什么樣的書?而我們今天又應該怎么閱讀與研究老子的《道德經》呢?要回答這一類的問題,離不開對諸如老子哲學之基本定位問題、老子《道德經》一書的核心主題、老子《道德經》中之“自然”的本質內涵以及老子《道德經》研究的出發點與歸結點等一系統相關基本問題所作的理論預設與前提性反思。
其一、關于老子哲學之基本定位問題。關于老子哲學的研究,不同文化或理論背景的研究者當然可以從其各自不同的視角出發作出種種解讀,然而此類關于老子哲學的種種“解讀”,都是與老子哲學的精神方向(即本質特征或曰根本旨趣)相契應的嗎?我們認為,要回答此一問題,首需預先對“老子哲學”自身作一番理論上的考察,方可形成關于老子哲學之基本定位,這大體包含了三個方面的內容:首先,就其對于“世界”之基本態度而言。我們知道,中國傳統文化通常被認為是“儒”“釋”“道”三家之學,而這實際上是指“中國哲學”在經歷“隋唐佛學”,尤其是“宋明新儒學(理學與心學)運動”之再創階段后的理論格局。然而盡管此“三家之學”自魏晉以降即已出現相互借鑒,同時并立之融合會通局面,但就其對于“世界”之基本態度言,三家之學卻仍然各有所側重:一般而言,如果說由孔子所開創的“儒家”側重于“化成”世界,其可謂一種“經世”的哲學;而由釋迦開創的“佛教”側重于“舍離”世界,其可謂一種“出世”的哲學;那么由老子所開創的“道家”則側重于“觀賞”世界,其似可謂一種“忘世”的哲學。其次,就其“自我”境界之預設言。我們知道,若就作為“中國哲學”之原創階段的“先秦哲學”言,則“先秦名家”(知識論)、“先秦儒家”(道德哲學)與“先秦道家”(美學)共同構成了“先秦哲學”之三大基本理論框架。與先秦名家重點強調“認知我”維度以及先秦儒家重點強調“德性我”維度不同,由老子所開創的先秦道家所預設之“自我”境界顯為“情意我”,故其在哲學上之根本理論旨趣,既非“道德”,亦非“知識”,而是“審美”,此為我們理解與把握老子與先秦道家哲學所首需辨析清楚者。再次,就其所關注的“課題”對象言。我們知道,就中國本土傳統主流哲學(儒、道)內部來考察,不同于先秦儒家學派更加關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由老子所開創的先秦道家學派所首要關注的則是人與外部世界(即指作為客觀對象的“自然世界”)之間的關系,而在與外部世界的“對話”中,老子的《道德經》正是以對“道”的探討為邏輯起點展開其關于宇宙與人生問題的全部論述,老子哲學對中國古代純粹藝術精神的建構產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
其二、老子《道德經》一書的核心主題是“道法自然”。《道德經》第二十五章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乃老子哲學的最高范疇,而“道”以“自然”為最高原則或曰最高境界。可見,老子《道德經》一書的核心主題即是“道法自然”,這個表述對于我們把握老子哲學的整體框架相當重要。
其三、老子《道德經》中之“自然”乃指一種否定“人為干預”(即指“有為”與“造作”等“亂作為”)的“思維模式”或曰“人生境界”。關于老子《道德經》中之“自然”本質內涵的理解,我們同樣可以從先秦道家學派的繼承者莊子的相關論述中得到應證。莊子確實是繼承了老子關于“自然”建構的這個思路并將此思想明確表述為“不以人滅天”或“不以人助天”,如《莊子·秋水》有段對話:
(河伯)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不要用人為去毀滅天然,不要用有意的作為去毀滅自然的稟性,不要為獲取虛名而不遺余力。謹慎地持守自然的稟性而不喪失,這就叫返歸本真。老莊此種“自然而然”思想,按我們現在通俗的語言,就是“不折騰”,實乃最具中國本土特色的“自然觀”。與《論語》“倫理觀”主要討論人類社會內部關系問題(如何規范人倫等級與秩序等道德層面問題)相對應,《道德經》“自然觀”同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視角”,它主要討論人類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問題(如何處理人類自身的生存發展與外部環境保護的良性互動關系)。除了上面提到的老子《道德經》第二十五章,關于“自然”概念的其他四處論述,分別見于老子《道德經》的第十七章:“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第二十三章:“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第五十一章:“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第六十四章:“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在此,“自然”在老子《道德經》第十七章、第二十三章、第五十一章、第六十四章中分別表示“自己如此”“少干擾”“少干涉”“自然而然”等大體相近的“含義”,卻沒有我們通常所說的作為自然科學研究之客觀對象的“自然世界”含義,可見,不同于后世流俗意義上的“拉關系”,老子更喜歡與“大自然”打交道。作為哲學家,老子以“大自然”為師,建構出中國傳統文化特有的“自然”概念,此種建構體現出典型的中國特色與中國風格,對后世中國傳統哲學與藝術產生了持續而深遠影響。孔子一生因其主要精力用于教學及奔走于各諸侯國之間游說其政治主張,在政治參與方面耽誤了太多的時間,以至于他接觸《周易》并潛心研究《周易》的“工夫”非常有限,“外王”有余而“內圣”不夠,他的哲學實際上局限于社會政治與倫理層面,先秦儒學“心性論”體系的完成主要是先秦儒家學派繼承者孟子的貢獻。相反,作為當時國家圖書館長的老子,對當時各諸侯國之間的政治缺乏實際參與的熱情,他在《道德經》一書中討論更多的是當時各諸侯國“政道“與“治道”必然失敗的深層根源。如果說孔子愛群居、熱鬧與教導,那么老子則愛獨處、清靜與沉思,他們都是中國歷史上的大哲學家,其哲學理論可以互為補充。
其四、老子《道德經》研究的出發點與歸結點是學會像老子那樣思考問題,提出問題,而不是只是簡單地記住或者糾纏于老子已經完成的不同年代版本具體說了些什么。老子的《道德經》一書,雖說成于春秋戰國時期具體的“時空”語境,但即便是在兩千多年后的今天,它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舉個例子來說,早在17世紀的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18世紀的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孟德斯鳩等人都對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贊嘆不已,并自覺地從中國的《道德經》得到思想資源。。老子是西方人最感興趣的哲學家之一,從16世紀開始,西方人把《道德經》翻譯成了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等。據西方學者統計,從1816年至今,各種西文版本的《道德經》已有近700種,如今幾乎每年都有一到兩種新的譯本問世。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被譯成外國文字發行量最多的世界文化名著,除了《圣經》以外就是《道德經》。這個例子充分說明老子《道德經》的哲學建構有許多重要內容具有超越時空的永恒價值。那么我們今天應該怎么閱讀與研究《道德經》呢?最重要的當然是需要將老子《道德經》蘊含的哲學思想與哲學智慧進行創造性轉換與創新性發展。學會像老子那樣“思考”與“提問”,比只是簡單地記住或者糾纏于老子已經完成的不同年代版本的具體內容要重要得多。我們首要的是要傳承老子《道德經》作哲學思考與提問的“精神”或“智慧”,而不是僅僅傳承一套關于此種哲學的某種自以為是的固定知識。任何一套關于“哲學”的“知識”都是死的,而唯有傳承其哲學“精神”或“智慧”才能真正將一個國家與民族的傳統文化弘揚光大。我們今天閱讀與研究老子的《道德經》一書,就是要設想,如果老子活在今天,針對當代中國與人類社會所面臨的環境危機與生存困境以及人們對于“審美”維度遺忘,以他的哲學智慧與哲學思維,他會怎么改寫《道德經》?作為一種哲學視角,《道德經》在春秋戰國時期或許是夠用的,但放到當今時代,則它所涉及的許多理論問題尚需作更具針對性的專題論述。實際上,我們自己就是當代的老子,因為我們傳承了老子的哲學“精神”與“智慧”,我們不會拘泥于老子《道德經》具體說過一些什么。老子《道德經》早已經說過的話,有什么好研究的?再怎么研究,都不過是老子哲學的“派生物”。更重要的是“接著”老子往下說,要說當代人自己的話。什么是中國哲學精神?就是在“照著講”的基礎上還有能力“接著講”,“接著講”的當然不是那套有限的“哲學知識”,而必須是“哲學精神”或者“哲學智慧”的傳承。不能將“精神”或者“智慧”傳承下去,那么我們雖說在學術與知識積累上已經是個不錯的專家,但我們在哲學理論研究與實踐智慧方面卻很可能早已經迷失方向,早已誤入歧途。我們對于老子《道德經》的閱讀與研究,要么“死”在“句下”,要么誤以為“智慧”就是“知識”,則我們本質上仍然只不過是熟讀了老子《道德經》的“失敗者”。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這是老子關于“為學”(“學術知識”)與“為道”(“哲學智慧”)之良性互動關系的精辟論述,要避免成為只是熟讀了老子《道德經》的“失敗者”,我們必須學會像老子那樣“思考”并“提問”。
(作者簡介:江向東,哲學博士,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思想史研究室副研究員。)
(:博覽群書 2019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