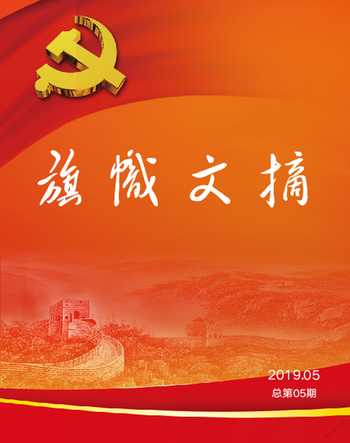令人警醒的歷史反思與人性考量(評論)
李掖平
中篇小說《遺忘》的作者尤鳳偉,是1980年代即蜚聲文壇的“文學魯軍”中一位實力派作家,從1977年發表作品至今已有四十余年。在這近半個世紀的風云流轉中,其創作一直秉持魯迅先生倡導的直面人生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的現實主義立場, 沿著歷史重述和現實關照兩條主線展開。歷史重述類小說,注重在縱向性時空坐標中解剖特定年代的歷史現象,通過還原重大場景重要事件,重塑身處社會轉型風雷激蕩大節點處的人物群像,還原其蕪雜微妙的心靈圖像,對過往歷史經驗及教訓進行尋根溯源的深刻反思。代表作有《石門夜話》 《鬼子來了》《中國一九五七》等。現實關照類小說,則注重在橫向性時空格局里向社會日常生活內部深辟,扣住矛盾沖突和人的心靈創傷及精神痼疾,聚焦時代癥候、關注民生熱點、書寫底層苦難、考量人性沉浮,代表作有《泥鰍》《中山裝》 《金山寺》《命懸一絲》《水墨》等。
《遺忘》以冷峻的反思意識和沉厚的悲憫情懷,將歷史與現實相勾連,由一個五十年前的刑事案件引入了對當下官場現狀以及貪污腐敗問題的描寫揭示。通過尋訪打撈這樁歷史命案的種種蛛絲馬跡,在既是舊案嫌疑人又是當下貪腐高官初永新的生活歷程中,剝離出一個個令人震驚的歷史和現實秘密。不僅展示了糾結于歷史/現實、忠誠/背叛、正義/邪惡、真相/假面、驚恐/沉痛等巨大漩渦里的隱秘復雜的心靈暗影與人性脈動,進而尋根索源其歷史、政治、哲學、經濟和民族心理等多元傳統基因,標示出一種清晰可見的現實主義高度與深度。
小說的故事情節在一個過去與現在的時空并置框架中展開和推進:刑警范強受命組隊偵破“無名白骨案”,幾經走訪調查,鎖定了這是一起發生在五十年前“文革”時期的歷史舊案,犯罪嫌疑人初永新也露出水面。但這個初永新卻是一名以常務副市長身份退休多年的高官,范強數次問詢查證都被他以年代太過久遠記不清了予以抵賴,案情調查一時受困。受富有偵破經驗的老干警點撥,范強轉而調查初永新的現實經濟犯罪案,經過數次精彩緊張的心理對峙和情感博弈之后,最終迫使初永新承認了自己五十年前犯下的罪孽,命案水落石出。刑警范強破案立功之過程,既是探尋人性罪惡之源、體制漏洞之殤的過程,亦是警醒讀者對抗習以為常的可怖性遺忘,復蘇小到個人大到民族國家必須留存的歷史記憶的過程。
小說的敘事空間在歷史與現實的回環對照中不停轉換,“文革”初期初永新以非法手段綁架常宗寶企圖奪權之時,漫天的落霞已然見證了他盛滿罪惡的潘多拉魔盒的開啟。而經過五十年的兜轉后,他起高樓,宴賓客,不斷放縱貪婪的欲望,于貪腐道路上愈走愈遠。這背后利欲熏心的人性之惡不禁讓人唏噓,理想信念的拋棄與崇高信仰的缺失引人沉思。由此看來,小說的命名確實別有一番深意。作者將這樁刑事案發生的時段設置在五十年前的“文革”背景之下,并且圍繞被害人常宗寶設置了犯罪嫌疑人、“文革”時代和現今時代的三重“遺忘”。不僅時空背景得以有效延伸,文本內涵也更加豐富深邃,一個蘊含著雙重警醒之意的巨大時代隱喻浮出水面:一是初永新對常宗寶的殺害,隱喻著當年的文革悲劇,隱喻著在那個特定時代背景下人性良知與理性的扭曲破碎;二是初永新連環套式的系列“遺忘”,擰成了一條清晰的因果鏈,隱喻著“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這一富含哲理性的精神命題。在過去與現在的時空穿梭中,初永新可憎面目有源可溯,當下的貪污腐敗、為官不正的作為,正是其“文革”時不惜殺人爭權這一狂妄行為的再次上演。由五十年前對自己非法綁人行為的遺忘,到后來對“文革”歷史之痛的遺忘,再到對人民干部應有的初心與良知的遺忘,小罪終于積成大惡。由此,尤鳳偉以過人的膽識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在“文革”背景下發生的不論有意或無意的傷害,遺忘固然不行,但今天的我們又該怎樣從歷史劫難中吸取教訓,如何將深刻的反思精神融匯于民族的血液中?
《遺忘》的敘事形式亦可圈可點。從結構上看,情節的鋪衍并非捋著一條反腐線索貫穿到底,而是將范強受命破案、日常工作、生活情感三條線索擰在一起有主有次交叉推進,情節生動豐富但絕不散漫,敘述節奏緩急相間張弛有度,人物性格得以多側面多角度豐滿。與此同時,刑偵、懸疑、反腐、官場、愛情等多種元素雜糅一體,滿足了讀者的多種閱讀需求。案情偵破過程一波三折而又環環相扣,針對破案遇到的難題逐個擊破,無論是刑警現場勘查還是多方調查走訪,無論是警察內部人員的邏輯推理還是外部人事因素的干預,抑或是讓人疑竇叢生的各個環節安排以及縝密精細的細節設置,都顯現出令人信服的邏輯力量。小說以初永新承認五十年前的過失致人死亡案作為結局,但文本依然留白出一個巨大的可言說空間,由“范強的心不由得勁跳了一下”這句話作為收束,意味深長,讓人突然察覺其實事情也許并非如此簡單,也許比我們了解的更加不堪。仿佛逐漸緩慢下來的曲調突然高揚而后戛然而止,留下耐人尋味的余韻。真相與謊言的迷霧之中,事情的本質和真相究竟如何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它引起了令人警醒的歷史反思與人性考量。
責任編輯 師力斌
(:北京文學2019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