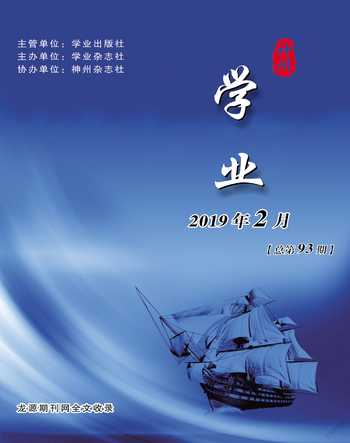論明永樂年間庶吉士王英及其詩文風格
李華
摘要:王英是明前期庶吉士的代表人物,他在明代歷任四朝,身居高位,頗受統治者信賴。但由于個性真率、放達,最終未能進入內閣成為大學士,晚年還受到排擠,外放南京。與其身世、性格相關,王英的散文既像一般的庶吉士群體那樣重視倫理教化,行文結構上有一定的模式化傾向,又有豪宕灑落,才氣橫溢的獨特風貌。其詩歌大多用語雄健遒勁,風格豪壯蒼涼,更具特色。
關鍵詞:庶吉士;王英;詩文
庶吉士制度是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根本目的在于選拔、培養高級官員,并因此被明清兩代統治者所重視。翰林院庶吉士制度確立于明永樂二年,當年曾先后三次考選庶吉士,從新科進士中選拔德行、文才出眾者124名,其中王英堪稱卓異。本文主要對王英的生平、仕宦經歷與詩文風格加以考辨和分析。
一、王英的生平與仕宦經歷
王英(1378-1450),字時彥,號泉坡,江西金溪人。永樂二年甲申科進士,被選擢為庶吉士。他出身于儒學世家,曾祖王頤貞元朝時鄉試中魁,祖父王子岱、父親王修本均以儒行稱世。但父親早逝,年少失怙,全憑母親曾氏撫養成人。王英從小刻苦嗜學,永樂元年鄉試中舉,永樂二年登進士第,選授庶吉士,科舉之途較為順遂。
永樂五年,王英結束了三年的庶吉士學習,并因處事慎密得到明成祖的器重,進入內閣撰寫機密文字。其后,參與了《太祖實錄》的編纂工作,授翰林院修撰,進侍讀。永樂二十年,隨明成祖北征。王師凱旋時,經過李陵城,皇帝聽聞城中有塊石碑,叫王英去察看。王英發現是元時李陵臺驛令謝某的德政碑,永樂帝怕碑上的蒙古名會引起爭地事端,叫王英將石碑擊碎。王英將碑沉入河中后還奏。永樂帝因其行事詳審,贊許道:“你是二十八人中讀書者,我將要重用你。”因向王英詢問對北伐戰事的意見。王英答道:“您御駕親征,對方一定會遠逃,請不要再窮追不舍了。”永樂帝笑道:“你認為我是窮兵黷武嗎?”便對王英說:“聽到軍中動靜后立刻向我稟報。”并告諭宦官不要阻攔。永樂帝下令不要給立功而有過失的官軍糧食,官軍相聚哭泣。王英將此事上奏后,才恢復了官軍的糧食供給。可見,王直為人耿直不阿,行事又周密詳審,頗得永樂帝信賴。
明成祖病逝時,王英與尚書蹇義、夏元吉,學士楊榮、楊士奇,侍讀王直等人商定喪禮,為了處理國政,在內閣住了七天之久。明仁宗繼位后,加恩賜白金、彩段。當年八月進秩侍講學士,不久升任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講學士。明宣宗時,天下承平,宣宗對文學創作很感興趣,總是與大學士談論文藝,賞花賦詩,對他們非常禮遇。宣宗曾勸勉王英:“洪武朝中的學士有宋濂、吳沉、朱善、劉三吾等人,永樂初則有解縉、胡廣。你要勤勉,不要讓前人獨專其美。”此后,王英參與修纂的《太宗實錄》《仁宗實錄》成書,遷任少詹事,賜麒麟帶。正統元年,命王英侍經筵,擔任《宣宗實錄》總裁,進禮部侍郎。正統八年,命王英管理禮部事物。浙江的老百姓遭受了嚴重的疫情,王英被派去祭雨。當時已大旱很久,王英一到便下大雨,百姓稱為“侍郎雨”。正統十二年(1448),王英的兒子按察副使王裕坐事下獄,王英上疏待罪,明宣宗寬宥不問。正統十三年(1449),擔任閑職南京禮部尚書。景泰元年(1450)五月庚申卒,年七十五。賜祭葬,謚文安,后改謚文忠。
王英一生的仕宦經歷總體較為平順,這與他的性格、才干息息相關,同為永樂二年庶吉士的陳敬宗曾這樣評價王英:“江右撫州多出名儒顯官,若宋之晏殊、王安國,元之吳澄、虞伯生諸君子,其文章、名位、功業皆炳然當世而垂耀竹帛者,豈偶然哉?玉笥、寶蓋諸名山秀氣所鐘也。公亦撫之人也,其文章、名位、功業莫不相似然。自入仕,歷官通顯,不離朝廷四十五年,而列圣眷遇久益不衰,似又過之矣。天之生賢,何私于撫之人哉!抑孰知公之才德自足致身于青云之上也?”后世對王英的功績、為人也評價頗高。《明史》本紀稱其“端凝持重,歷仕四朝”。《今獻備遺》說他“歷事三朝,完其勛名,其亦吳、胡之侶耶?”廖道南則稱:“予觀陳敬宗所撰《文安傳》,以為撫州多名儒,若宋之晏殊、元之吳澄,蓋玉笥、寶蓋諸山之靈所鐘也。及讀《國史》,謂文安樂易善書,跌宕不拘小節,固有征哉!贊曰:漢有二王,咸負芳名。宋有二王,并登宰衡。文端曰直,文英曰英。勛如其名,永世有征。”
但是,王英的個性不像很多高官那樣持重,而有魏晉名士般的放達之風,《明英宗實錄》稱其“豪縱跌宕,不拘小節,頗有晉人風度云”,“性直諒,好規人過”。也正是由于這種直率、外露,不善迂回的性格,他雖官居高位,但始終未能成為內閣大學士,“三楊皆不喜,故不得柄用”,“早結主知,雖陟清華,未及柄用”。晚年更被排擠出了權力中心,放逐到了南京。這對他的打擊很大,兩年后便抑郁而亡。
二、王英的散文風格
王英有《泉坡集》,今存《王文安公詩文集》,其中詩五卷,文六卷,數量并不是太多。但他在翰林四十余年,數次出任會試考官,朝廷制作多出其手,四方求銘志碑記者不絕,詩文廣受好評。《明英宗實錄》稱:“其文章典贍,一時重之。尤善草書,解縉以后,一人而已。”《靜志居詩話》評其詩曰:“西王密切謹嚴,句無浮響,如‘別路斜陽京口樹,他鄉明月洞庭船。挽得雕弓射飛虎,賜將宮錦繡盤螭。舊館空余秦地月,古壇猶似漢宮秋。’皆瑯然清圓可誦也。”陳田也在《明詩紀事》中說:“余觀東王《祭泉坡文》云:出入朝廷,敬恭將事,不翕而同,不矯而異。可以知其旨矣。詩五言如良玉縝栗,迥異當時臺閣之體。”可見王英之詩文因較為豪宕灑落,才氣橫溢,而區別于當時主流的臺閣文風,并因此受到當時和后世的激賞。
就文體而言,序、記、碑銘是王英散文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序又多為贈序、詩文序、族譜序三類,如贈序《送金少卿還姑蘇序》,詩文序《棠陰八景詩序》,族譜序《吉水錢氏族譜序》等。記雖數量較少但內容豐富,關涉儒學、祠堂、廟宇等文化設施,與私人的堂、屋、齋、亭、軒等建筑,如《崇德重修儒學記》《雷公廟禱雨記》《大明重建南岳廟記》《龍池書館記》《翠微樓記》等。這些散文均具有一定的文學、文獻價值。
王英的序、記類散文在行文結構上并無太多出色之處,其獨特性主要在于論述立場上,一般序、記文多頌美、夸贊之詞,王英的卻以訓誡為主。當然,他的訓誡并非一味刻板的說教,而是在闡發古人的思想理念時,增添自己獨特的人生體悟和為政思考。如《送黃知縣赴任詩序》說:“會朝廷無事,萬方清寧,云夢之野固無苦楚子之畋獵者,民可以樂其生矣。吾豈務為游觀乎?又必告之曰:民之樂其生,當習詩書俎豆以厚其俗。(民)出貢賦以時供于上,吾豈厲民以自奉,有負于令乎?”這段論述提出為政應以民為本,而不應刻薄百姓,要將傳統的民本理念融入到縣令的從政原則之中。《送陳知縣之任常山序》中云:“人之立身,能致其謹而不自流蕩,為物所溺而虧其守者,必能企仰古之君子,循其道,不以窮達顯晦而易其操,則庶幾其可矣。”平實的文句中闡明了不隨世俗流蕩,不為外物所溺,不以窮達易操,謹慎守真的為人準則。《送陳用謙還鄉序》說:“夫人之為學,無汩沒于淺近,必至其遠者、大者。非有他也,求其聞廣見多,以盡乎天下之大觀而奮發其心氣,以期于有為者也。”這雖然是從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中生發的觀點,卻也融入了作者真實的體驗與追求。
《環碧樓記》則顯示了王英獨特的山水觀。他認為山水兼具修養德行之效與山水游觀之樂,不應排斥后者。可見,較之王直等人一味強調“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將山水倫理化的傾向,王英的態度要通脫得多。或許由于倍感仕宦之繁難與遭受排擠之苦,王英晚年時常有歸歟之感,多篇記中均提到“老矣”、“乞身南山”。但總體而言,他的散文較少抒寫個體情感,尤其是愛情、夫妻之情,關于家庭生活的記敘也多上升至倫理道德的層面。
三、王英的詩歌風格
相較而言,王英在詩歌上的特色更為鮮明。不少詩歌的內容有一定深度,藝術上也造詣較高,文體則以五言古體為優。如五古《雜詩》其三:
清晨登高丘,迢遙望郊郭。連山起層甍,焜燿皆丹臒。歌吹一何繁,車馬日聯絡。翩翩游俠兒,姿態紛婥約。輕裘巧妝束,珠貝相間錯。侈心儷金張,壯志凌衛霍。豈知幽閨中,居者恒寂寞。掩形無完衣,充饑有藜藿。貞心益自厲,容色日銷落。塊然獨囂囂,甘為所眾薄。
此詩對比了游俠兒與居者(隱士)的生活和心境,寫出了隱者情愿獨守貧窶,也不愿與世同其波流而自守寂寞的孤傲態度。寫法上頗受阮籍《詠懷》、郭璞《游仙》的影響。
此外《登北門外古城》、《夢游華蓋山》三首、《游翠微山圓通寺》五首、《六賢詠》六首等詩,也驚挺俊爽,各有可讀之處。如《登北門外古城》:
朝出北門道,下馬登古城。循步歷幽險,墉堞半欹傾。其陰何蒙密,蔓草與榛荊。野鼠時出沒,狐貍亦悲鳴。聘懷忽悽惻,游目極窈冥。群山東際海,遠勢與天平。夐絕孤云浮,渺漠終古情。慨茲乃故跡,昔者勞經營。形勢猶突兀,從事嘆凋零。孰云金湯固,慎守須兢兢。憑高一長嘯,壯心徒自驚。
此詩前半部分描寫古城的毀圯破敗情景,顯然了吸納了鮑照《蕪城賦》的寫法。但后半部分歸于慎守,有警誡邊將之意,又與《蕪城賦》的立意大不相同。
《六賢詠》所詠黃冔、劉杰、陳介、葛元喆、王彰、朱夏皆元代金谿人,有表彰鄉賢之意。其序曰:“六賢皆金谿人,元時金谿多文雅之士,能謹行誼、保名節者,六君為最。若待制黃公,已載《元史》,馀皆闕焉,乃為之詠。”六首皆用語精警挺拔,饒有風骨。如詠黃冔:“待制本儒生,素心亦何烈。臨危仗孤劍,誓死以殉國。奮軀入重泉,正氣浩充塞。蛟龍為悲吟,天地慘無色。殺身良獨難,求仁義斯得。”雖然人物形象流于概念化,但下語雄健遒勁,風格之豪壯蒼涼,在其他庶吉士當中是不多見的。
王英還有不少題畫詩,如《題周懷中家景圖》《畫虎歌》《題韓滉畫田家移居圖》《溪山秋意圖》等等,展現了他較高的藝術鑒賞能力,從后兩首詩中還可看出他有清新淡遠、受陶詩影響較深的一面。
參考文獻:
[1]張廷玉.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
[2]周駿富.明代傳記叢刊[M].臺北:臺灣明文書局,1991.
[3]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明實錄.[M]中華書局,2015.
[4]王英.王文安公詩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基金項目:本文為湖南省教育廳社科項目“明前期庶吉士詩文與明前期社會”(項目編號:13C566)的階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