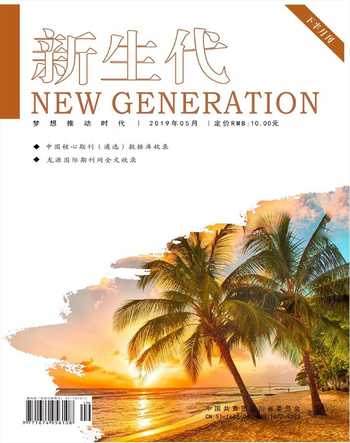唐代閨怨詩之“代言體”的研究
【摘要】:唐代閨情宮怨詩的創作有一個很奇特的現象,就是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由男子代女子抒情表意的,即運用了代言體。“代言”作為唐代閨怨詩重要特征,展現了唐代閨怨詩的獨特魅力和廣闊的審美空間。男性詩人借女子的身份言志抒情,帶有委婉的功利性目的。唐前閨怨詩的作者幾乎都是男性,女性則寥寥無幾。由于二者生活經歷、寫作視角、社會地位等方面的差異,作品在審美取向、思想深度上有著明顯的不同,但都形象地展示了當時女性的生活情態。
【關鍵詞】:唐代閨怨詩 代言 言志 蘊藉
閨怨詩是唐代眾多詩歌題材中一個很獨特的門類,這類詩歌,有的是女子自己寫的,還有一些是男詩人模擬女人的口氣寫的,主要書寫古代民間棄婦和思婦的憂傷,或者少女懷春、思念情人的感情。其語言大多幽怨深情,委婉含蓄,其作品豐厚的情感內蘊和藝術成就值得后人學習和借鑒。閨怨詩源于先秦,發展于漢魏晉及隋朝,在唐代發展到頂峰。唐王朝戰火連綿,商業經濟繁榮、科舉制興盛,導致大量的夫妻分離,再加上更為開放的市民意識和婦女觀,所以表現閨怨的詩人、題材大量涌現。唐代閨怨詩有相當一部分是男子而作閨音,即運用了代言體,深入探究唐代閨怨詩代言體創作的研究,我們能發現其中的復雜性
一、“代言”與“審美”
唐代閨怨詩以“男子而作閨音”的代言體和以悲為美的基調聞名于世,“代言”體作為言志的一種方式,在大部分閨怨詩中展現的淋漓盡致。代言就是借他人的身份、心理、口吻進行構思創作,即代詩中主人公言志抒情,詩人以閨婦的情感遭遇隱喻自己的政治遭遇,帶有委婉的功利性目的。“詩言志”之說源出于《尚書堯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這是中國儒家詩歌理論的“開山綱領”,是中國古代文論的母題,它來自對《詩經》創作經驗的總結,是對作品表現作者情感這一特征最早的理論概括。由于敘述者與隱含作者的不一致,而產生了“代言”的特殊語言效果,他們以女性化的敘述語言曲折地表達出自己細膩而感性的聲音,又借由。敘述者的女性身份,隱藏自己的潛在想法,實現了語言真實性。唐代“代言體”詩在整體風格上不同于山水田園詩的清新自然,也不同于三水田園詩的豪邁奔放,而是具有一種委婉曲折、意猶未盡的美感效果。比如說唐代閨怨詩中男子而作閨音在遣詞上,無論是描寫景物還是人物感情,多用一些具有凄清蕭條意味的詞語和意象:柳、寒砧、西風淚、思、燕等,這些詞的大量運用能夠營造一種寂寞悲涼的環境氛圍,反襯人物的心境,使詩歌表現出纏綿悱惻、寂靜冷清的意境,具有含蓄蘊藉的特點。
二、代言與蘊藉
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中,有很多男性文人擬作閨音,這是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造成的。封建統治者為女性提供了一套所謂“三從四德”的禮教制度,使女性被籠罩在男性權威之下。在這樣的背景下,女子幾乎不能從事什么社會活動。同時,由于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荒謬言論,女性的文學創作道路在一定程度上也遭到了堵塞。因此反映女性情感的詩歌大多是男性代言之作,女性留下來的作品較少。到了唐代盡管女性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封建禮教的束縛還是存在的,因而唐代閨怨詩的作者仍大都是男性。與早期男子而作閨音不同的是,唐代閨怨詩的“代言”寄托了豐富社會內容和作者的某種情志,展現了更加豐富的審美空間。從蘊含主題上看,唐代閨怨詩中男性文人之寫女性,大體有這樣幾種情況:
(一) 對處于水深火熱生活中的人民的同情
唐代征伐相當頻繁,初期主要是解決反唐勢力和周邊少數民族政權。除此之外,為了鞏固政權并防止有可能出現的叛亂,唐朝還大量囤積兵力,再加上安史之亂的動蕩,導致征婦的數量大大增加。戰爭不僅跟國家安危有關,也與千家萬戶的生活密切相關,由此產生了許多夫妻常年離別的悲劇,有的甚至剛剛新婚,丈夫就被拉上戰場。唐代就有很多閨怨詩展現了戰爭給下層人民帶來的苦難。比如裴說的《聞砧》“愁捻銀針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寬窄。時時舉袖勻紅淚,紅箋謾有千行字。”在秋天的夜晚,征婦在昏暗的燈光下寫著給征戍邊關的丈夫的信,心中有萬般的苦楚和思念想要對丈夫傾訴。擔心邊關寒冷,捻著銀針縫了一件衣裳,卻不知丈夫穿上是否合身,心中愁緒漸起。這首詩體現了夫妻由于戰爭被迫分離的悲涼場景,展現了唐代頻繁的戰爭給下層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其它如杜甫的《新婚別》、張籍的《征婦怨》等均不只是寫閨婦的不幸命運,而是把她們作為一面鏡子,反映戰爭給下層人民帶來的災難和不幸,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
(二)寄托君臣關系、抒發懷才不遇之感
中國的“三綱五常”強調君為臣綱,夫為妻綱,從這個角度來看君臣關系和夫妻關系確乎有些相似。中國自古就有借男女關系象征君臣關系的傳統,比如屈原的《離騷》。漢王逸就已經指出:“《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讬君子;飄風云霓以為小人。”屈原的這一創作方法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唐代閨怨詩中亦有這樣的作品。唐代閨怨詩中的《太行路》便是借夫婦以諷刺君臣不終。《太行路》先以“古稱色衰相棄背,當時美人猶怨悔。何況如今鸞鏡中,妾顏未改君心改。”寫女子色衰愛弛的悲劇,后以此比喻君臣關系,“不獨人間夫與妻,近代君臣亦如此。君不見左納言,右納史,朝承恩,暮賜死。”。這既是對當下生活在重重特權壓力下處于水深火熱情況下女性的悲慘遭遇的呼喊,也是對君臣關系不終的慨嘆與無奈。
三、男士所寫閨怨女子形象是否符合現實
誠如一些學者所說:“中國歷代有許多男性文人曾經擬作閨音,他們將自己的文學觸角伸向女性生活、女性情感,一些作品相對‘女性化’,幾乎達到以假亂真的境地”。那么唐代閨怨詩“男子而作閨音”到底是否能夠真實反映唐代女性的面貌,他們所反映的女子形象又跟女性筆下的形象又有什么不同,我們可以通過比較兩類作品來分析這些問題。
唐代由于文化的繁榮、政策的開放,促使女性意識覺醒從而產生了許多女性作家。她們的詩歌多以怨愁為基調,多些閨中思念之情。由于大多是她們的親身經歷,所以表現了真實質樸的特點。如出自女詩人陳玉蘭之手的《寄夫》:
夫戍邊關妾在吳,西風吹妾妾憂夫。一行書信千行淚,寒到君邊衣到無?
這首《寄夫》用質樸而又真實的語言表達了女詩人對丈夫的思念,“夫戍邊關妾在吳,西風吹妾妾憂夫”,直接點出夫妻分離,當西風吹起時妻子開始擔憂遠在邊關的丈夫。詩的后兩句,寫閨婦寄衣附信,“一行書信千行淚”,女詩人每寫一行書信便有一行清淚從眼眶流下,凝聚著思婦對丈夫的無限思念、憂慮。“寒到君邊衣到無”,流露出思婦對丈夫冷暖的關心,害怕邊關天氣突然轉涼而自己親手縫制的棉衣卻還沒有寄到丈夫身邊。體現了思婦對丈夫的愛憐之深,可謂句句含情。正如黃叔燦在《唐詩箋注》中所評:“情道真處,不假雕琢,自成至文,且無一字可易,幾欲天籟矣。” 女詩人以樸實的語言,真實地表達了自己的心聲。一些商人婦也用詩歌真實地表達了自己的離別之怨與相思之情。丈夫長期在外經商,妻子只得在家中日夜期待丈夫的歸來,年華老去,只能在江口獨守著空船,期盼丈夫早日歸來。如郭紹蘭的“我婿去重湖,臨窗泣血書。殷勤憑燕翼,寄與薄情夫。”“臨窗泣血書”運用浪漫主義的手法,表現了女詩人對丈夫的一片深情。
如果將二者的閨怨詩進行比較,毫無疑問,他們的基調都是以悲為美。從思想內涵上來看,女性詩人的視角比較狹隘,僅從個人角度抒發情感,而男性詩人則關注到了社會問題。如閨怨詩中對征婦的大量描寫,就是突出了邊塞戰爭的頻繁。更進一步,從女性形象來說,總體來講男性詩人筆下的女性形象大致上是符合唐代女子的總體特征的。比如裴說的《聞砧》中的“愁捻銀針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寬窄。時時舉袖勻紅淚,紅箋謾有千行字”這樣微小的細節,仿佛就是征婦的真實心理,如果不是經過了細心的觀察,一般的男性詩人是寫不出這樣細膩真實的畫面的。這類詩雖出自男性詩人之手,但感情的抒發和形象的展現相當的真實。從現實來看,唐代法律中規定:“若夫妻不相安協而和離者,不坐”,這無疑是對妻權的一種保護。《太平廣記》中也有諸多記載與丈夫抗爭、勇敢追求幸福與自由的女性事跡的記載,可見當時的女性地位和女性反抗意識都得到可一定程度上的提升。從女性形象的塑造來看,男性作家塑造了一批敢于反抗的女性,如于濆的“知子從軍去,何處無良人”(《古別離》);曹鄴的“貧賤又相負,封侯意如何”(《怨歌行》);李益的“早知潮有信,嫁于弄潮兒”(《江南曲》)這些詩中的女性大膽斥責丈夫的行為正展現了這一現實轉變。然而唐代女性詩人文學創作仍是作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自己的意識并沒有完全滲透到文學作品中,真正的女性意識尚未覺醒。
【參考文獻】:
【1】劉紅旗.論唐代閨怨詩不同創作主體的審美取向[J].漳州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25(01):36-40.
【2】陳葉.唐代閨怨詩之“代言”的豐富開放性空間[J].包頭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3,14(03):28-30.
【3】孫世家.論唐代邊塞閨怨詩中的女性形象[J].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2015(01):5-6.
【4】李紅. 唐代閨怨詩研究[D].暨南大學,2002.
【5】王淑梅,楊柳,蘇虹.唐代“代言體”詩歌創作動因和藝術特征研究[J].名作欣賞,2012(12):83-84.
【6】胡海桃.近十年唐代女性研究綜述[J].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16(06):101-106.
作者簡介:姓名:譚添 ?出生年月:1998年7月22日 ?性別:女 ?民族:漢 ?籍貫:湖北省武漢市 ?學歷:大學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