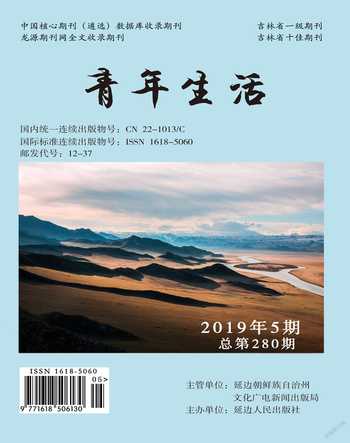中國近代文化的轉型及其原因
金璐璐
摘 要: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我國古代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清政府時期封建權力達到頂峰,受外國勢力影響,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知識分子們從曾經的鉆研國內儒學漸漸轉向探求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積極投身于國內的救亡圖存運動中來。
關鍵詞:變革;內因;外力
近代新學是中國學術文化的近代形態,也是中國傳統學術的時化轉型。由于中國近代新學是在西學東漸的直接影響下發展起來的,以至近代新學從內容到形式都深受西學的熏染,不少新學家亦當必稱西學;這樣,人們往往把近代新學全然看成“外鑠”的文化形態,看成西學的東方翻版。此類見解顯然失之偏頗。顧頡剛早在1919年論及中國近代學術變遷時就曾提出:“吾從前以為近三十年的中國學術思想是由易舊為新的時期,是用歐變華的時期;但現在看來,實不盡然。”1“在三十年內,新有的東西固然是對了外國來的文化比較吸引而后成的,但是在中國原有學問上一樸學、史學、經濟、今文派的趨勢看來,也是向這方面走去,所以容易感受新來的文化。”近代新學在中國的發生發展,固然深受西學的刺激與影響,但它畢竟不是西學的簡單位移,多種文化創造,中國傳統學術文化本身就蘊含著由在動因一經世實學。龔自珍“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學”的提出及躬身實踐,魏源《海國圖志》的橫空出世都是學術經世并付諸實踐的范例,而且,魏源的經世思想以實利為標準,講求功利價值,為經世思潮的致用找到了生命的支點,使之得以蓬勃發展。以后“求諸實用”的治學原則成為近代學術的發展趨勢與時代要求。梁啟超對龔魏對中國近代學術轉型的影響多次給予很高的評價:“自珍、源皆好作經濟談,最注意邊事”,2“故后之治今文今學者,喜以經術作政論,則龔魏之遺風也。”“數新思想之蔭蘗,其因緣固不遠溯乎龔魏。”《清代學術概論》又稱:“光緒間所謂新學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3并說:“語近世思想之向導,必屬定庵。吾見并世諸賢,其能為今之思想界放光芒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當其始讀《定庵集》,其腦際未有不受其刺激者。”極言龔對人們思想影響之大。曾樸也說龔自珍與魏源“兩人崛起,孜孜創新”。自此經世之學中,學術多元和西學的大量引進成為學術近代化的標志。其重要特點在于西方的自然科學,特別是軍事技術、工藝制造等利于經世濟國之術成為時人注目的焦點和重點學習的對象。從此,圍繞不斷引入的西學與中學的交融、沖突引起的“體用之爭”以及關于傳統文化出路的思考與論戰成為近代學術的主流。
雖然在經世實學中已經孕育看中國學術近代轉型的內在動因,但是促成舊學解體并導致其發展方向變革的因素卻來源于近代西學。加王先明所指出的:“西學的沖擊,一方面激活了傳統中學中的文化因素,使之與時代的變動相結合,形成主動追隨時代進步的學術風尚;另一方面,西學本身的科學和民主因素,也逐步納人中學之內,構成了中國舊學向“新學’變革的基質。”4從近代學術文化發展的歷史進程來看,新學的形成確乎得力于西學的推動。
傳統觀念的轉變,即人與人之間以社會契約型的權利義務觀念,取代傳統的倫理化的道德觀念。近代中國文化轉型方面一個極其嚴重的社會問題,恐怕就是道德問題。傳統道德中既有陳腐的成份,也有有益的東西。繼承和發揚這些有益的東西是我們的歷史責任。但是,任何優秀的傳統都不會直接導致現代化。僅僅靠宣揚傳統,或者莫名其妙地一味迷信“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那么,就無法避免道德的無序性變動,傳統也會失去應有的張力而不斷萎縮,從而使我們沉淪為一個無道德的時代。傳統生活方式的改變。它包括人們生活范圍的擴大,謀生手段的改變,社會流動的加快和生活質量的提高等項內容。傳統語言文字的轉變.這是文化的信息符號的改變,它包括兩個內容,第一傳統民族語言文字的進化,例如文字的語體化,文字的簡化,標點符號的采用等等;第二,外來語言文字的引進,乃至外來語言文字的日益普及。
西學東漸是近代中國社會變動的重要歷史因素。在西學流布的過程中,曾經有多種西方近代社會"政治學說傳入中國,并在相當廣泛的范圍內發生影響。近代中國的政治變革運動也往往與這種影響的規模和力度有關。但是,如果細心考察下來就會發現,這種規模和力度一般都僅僅限于宏觀性質的。近代西方社會政治學說遠未普遍地滲透和溶合到社會各階層的深層心理素質中去。甚至在知識分予群體中這個過程也沒有完成。在近代中國人,包括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中,許多西方社會政治學說的基本范疇、概念都表現為一種浮光掠影的游離狀態。它們或者嫁接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根基上,或者為傳統政治道德改造。政治資源的分配,限定著知識精英參與政治的道路和方式。就整體而言,知識精英是官僚隊伍的后備軍,只有通過科舉考試的渠道才能參與政治,否則的話只能一輩子以“候補”的身份存在。雖然歷史上不乏知識分子拒絕為當世朝廷服務而深隱簡居的例子,但他們要么是留戀舊主,要么是期盼新圣。他們只有選擇為這個朝廷或為那個朝廷服務的自由,而沒有選擇是否依賴于封建政治發揮其作用的自由。甲午戰爭之后,由于危機的刺激,更重要的是由于政治價值觀的轉換,知識精英開始沖破封建科舉的渠道,以新的方式和新的取向作用于政治生活,開始了其政治人格的近代轉型。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對于傳統參政方式的超越。鴉片戰爭以來,一方面知識精英參與政治的需求日漸增長,另一方面,參與政治的渠道卻日益狹窄和擁擠。
甲午慘禍的刺激和求變理念的激勵,終于為知識精英沖決幾千年來的參政渠道造成了突破口。以康有為為代表的一部分人,通過上書的方式,以在野知識分子的身份,評點時政、呼吁變法、指陳時局危艱、要求皇帝下“罪己詔”,處分腐朽無能大臣;而另一部分人則放棄了科舉之途,走上實業救國、教育救國之道;更有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一部分人徹底判離了封建政治,走上了武裝推翻帝制的道路。這種轉變標志著中國的知識精英已不再僅僅是封建官僚的候補,開始擺脫對封建政治的依附。
注文:
1 顧頡剛:《中國近代學術思想的變遷觀》,《中國哲學》第11輯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 梁啟超:《清學術概論》中華書局 2010年版
3 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復旦大學出版社 1985年版
4 王先明:《近代新學—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嬗變與重構》,商務印書館2000版
參考文獻:
[1]崔志海《近代中國文化轉型研究導論》近代史研究2009年02期
[2]陳于武《探究中國近代文化轉型的軌跡及其機制》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8年07月
[3]徐瑛《探討中國近代文化轉型的軌跡》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5年03月